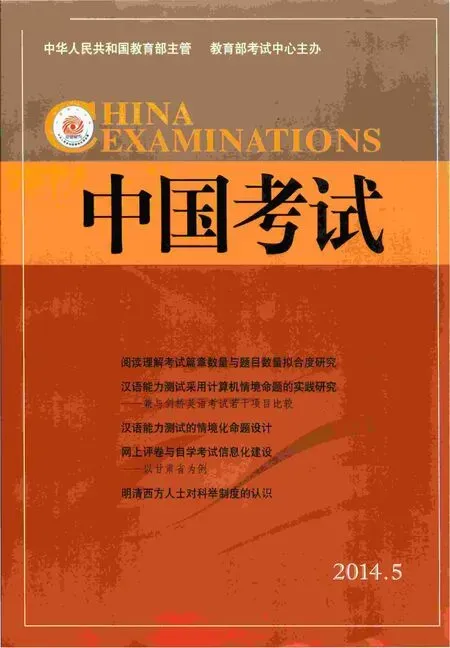明清西方人士对科举制度的认识
吴四伍
明清西方人士对科举制度的认识
吴四伍
近代西方人士基于西方视角或自身经历,对中国科举制度的考试功能、考试体系、传统教育等进行独特分析。他们肯定科举制度的选拔功能,却对其阻碍教育、耽误人才发展的消极方面深为叹息。他们欣赏科举制度设计的周密,但同时以西方人的身份指责科举考试内容的落后。这些论断和认识对于今天人们研究科举、反思教育,意义尤其深远。
科举制度;传统教育;西方视角
明清以降,中西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一些西方有识之士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不断加深。科举制度在传统社会中举足轻重,自然受到西方人士的关注。他们根据亲身经历,或凭借自身判断,对中国社会诸多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留下了众多珍贵的历史记录,其中利玛窦、丁韪良,卫三畏等是杰出的代表。他们以西方人独特的视角,对官吏人才选拔、社会等级形成、传统教育发展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这些认识,对于今天人们理解科举、反思教育提供了难得的素材,值得人们重视。
近百年来,海内外科举研究取得诸多重要成果,形成了重内轻外的畸形格局,即学人多重视科举制度沿革、演变、功能的梳理,而有关西方与科举关系的研究却寥寥无几。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当数1937年邓嗣禹所撰《中国考试制度西传考》,该文虽意在阐述中国科举制度在欧美传播的具体历程及其对欧美文官制度的深刻影响;但有关16世纪至20世纪西方人士如克罗兹、特利高特、孟德斯鸠、狄德罗、摩里逊、麦杜思等对科举制度的认识也有所论述[1]。60余年后,刘海峰《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一文对科举制度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进一步丰富,搜集更多的史料,注重从文明传播的角度倡导科举制度对欧美文明的影响[2]。该文同样重视欧美知识界对科举制度的认识,也对此进行了相关阐述。然而,两文都重在阐述中国科举制度的海外传播及深远影响,对于西方人士观察科举制度的独特之处,缺乏具体分析。事实上,近代以来西方人士对科举制度优劣的详细分析,对科举制度举行的具体观察,对科举与传统社会关系的洞察,以及独特的西方视角,与同时代的国人分析科举制度大相径庭,为人们了解和分析传统社会科举制度运行提供难得史料与见识,本文对此试做一简要论述,祈请大家指正。
1 测量目标与官吏选拔
近日科举研究,正呈现多学科、多领域拓展的良好发展趋势,从历史学科以外的学科领域深层发掘科举制度的各种社会影响,成为人们努力的重要路径。但是,科举制度的自身研究同样值得重视,特别是从科举的本质属性出发,从教育测量的视角探索科举的发展,显得更为紧迫。研究科举,首先必须承认科举是一种旨在人才选拔的测量工作。换句话,科举制度的本质是一项教育测量工作,其核心是测量目标的确定。对官吏的选拔是科举制的主要测量目标。这一测量目标本身也决定科举制度的工具属性所在。来华的西方人士,对于科举制度的选拔人才功能是赞赏有加。
明清之际,利玛窦作为最早来华传教士之一,他观察到:中西社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管理阶级的不同。在他看来,中国政府的治理是受到知识阶级的巨大影响,而这一知识阶级正是由科举制度塑造的。“只有取得博士或硕士学位的人才能参与国家的政府工作;由于大臣们和皇帝本人的关怀,这类的候选人并不缺乏。”[3]同时,科举制还影响了中国人学习和创造重点的转移,即中国对学问的偏好胜过对战争的爱好。正是这种偏好,导致了中国倡导四千多年的和平主义传统。换句话,科举制度为中国政府官员的较高文化素质把关。它确保将最优秀的中国人才送到官吏队伍之中,保证了中国社会的内部稳定,也成就了中国对外和平的优良传统。
科举制度的选拔功能也得到卫三畏的认可。鸦片战争前夕卫三畏向美国民众介绍中国,科举制度作为首选课题。“中国教育的透彻性,考试的纯正、有效,文学的精确、优美,……完全超过了同一时期的犹太、波斯、叙利亚所能达到的。”[4]科举制吸引优秀人才的重视,它向“这个国家最有志向、最有才能的或激烈的人物提出一个崇高的使命,需要他们贡献全部力量”。科举制能选出高效的官吏队伍,“这样的考试所充分发挥的思想和记忆力的训练,造就了一个层次的知识界,只需要公共生活的磨练和经验,就可以从读书人中产生政治家,使中国在亚洲的影响远大。”[5]科举制度效能的发挥,使得人们“不可能设计出更好的方案来保证政府的永久性,或是使人民在政府的管理之下心满意足。”[6]科举制体现了平等的精神,“这一制度将一切人置于平等的基础上,据我们所知,人类本质还没有这样的平等”。科举制度在维护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社会起到良好的作用。“科举考试制度以经典及其注解所教导的政治权利义务作为绝对的力量,使中国免于再次分裂成许多王国。”[7]
卫三畏同时指出科举制的一些缺点。如晚清政府的捐纳功名过多,使得“考中的人凭真才实学进入官府有个很大的为难,就是出钱买到虚衔和实缺的人更占便宜”。卖官的后果,使得5 000名进士和27 000名举人等待任用。[8]基于宗教立场的考虑,卫三畏认为基督教国家没有必要实施这种制度,因为人们为其自身而学习,不必如此劝诱,就有能力、有意愿成为统治者所期望的博学之士。他们不会听任网罗和圈套的摆布,汲汲于官职,而且最能干的政治家不必从最渊博的学者中寻求。[9]
与卫三畏不同的是,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传教士丁韪良博士积极主张美国学习科举制度。19世纪70年代,美国国内酝酿文官制度改革,是否学习科举制,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丁韪良对科举制的理解有着某种现实的意图。他写道,“正是在中国,科举考试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经受了考验。假如我们想在这一点上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这将不会是我们从中国人那儿学到的第一门课,也不会是他们所能教给我们的最后一门课。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受惠于中国人,如罗盘和火药,也许还有印刷术带给我们的一点启示。”,并且强调“假如我们采取中国选拔人才的方法来为我们的国家政府选择最优秀的人才,那么它对于我们的政府管理机构所带来的有益影响绝不会小于上面提到过的那些技艺。”[10]因为“科举考试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国家政府选拔人才,无论它在哪个方面有失败的地方,都不可否认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它的特定目标。中国的官吏几乎无一例外是受教育阶层的优秀人才,无论是京师,还是在各个行省,在每一个文学领域拔尖的都是官吏。皇帝正是借助了他们来教化和统治中国的百姓。”并且,科举制体现了真正的民主精神,“在随从簇拥下大摇大摆从街上经过的威严官员其实并没有什么世袭的爵位,也不是因为皇帝宠幸而做官,更不是由臣民们善选出来的。他们是自选的,并因此获得人民更深的崇敬,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是靠自己的学识和能力获得官职的。还有什么能比给所有人‘机会均等的激励灵感’更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民主?中国就是以这种真正的民主而傲视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因为无论它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有何种缺陷,人们必须承认,中国在鼓励人们发奋努力和奖赏学业成就上设计了最佳的方法。”[11]
1909年,尽管科举制废除,传教士麦高温在游览贡院后仍不禁感慨,科举制曾经在中国社会塑造何等强大的文人阶层。“国家的行政人员必须从文人中选出,如果我们认识到对这个地域辽阔的国家进行管理需要多少行政官员,那么这个阶层在国家中是多么强大和有影响力也就不难想象了。[12]近代西方学者费正清认为科举考试制度自汉代开始,以文章为选拔标准,官员“以彻底服膺于官场的正统思想来确立他们居官任职的资格,这肯定又是另一种伟大的政治发明。”[13]
从测量目标的完成角度来看,科举制度在选拔优秀人才担任官吏方面,得到西方人士的长期赞扬,也是西方人士肯定科举制度的最大之处。从利玛窦直至费正清,不管时代如何不同,立场如何差异,他们均承认科举制在选拔官吏方面的积极作用。人们立场不同,往往判断科举制度的价值差异很大,如像卫三畏基于基督教徒的立场认为科举制无需借鉴,而丁韪良基于现实需要强调科举制的优越性,但两者均无法否认科举制在塑造中国社会特性方面的巨大效应,他们恰好从正反方面论证了科举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工具价值所在。诚如费正清所说,科举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所扮演的角色,远远没有为人们所重视。
2 考试体系与身份等级
从测量的附加效果来看,科举考试制度对传统社会的影响是任何现代考试所难以比拟的。科举考试从县级到全国,形成了各级相通的严密考试体系。这种体系能够确保动员所有知识分子参加考试,从乡试到殿试,使得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置身争取权力与功名的统一测试之中。更重要的是,伴随考试的结果,使得人们分处秀才、举人、进士等不同功名,进而在社会上形成不同层次的文人体系,造成不同士人身份等级的不同。来华西方人士往往将科举的功名与西方社会的学位制度比较,得出很多独特的认识。
利玛窦认为科举制度是一种人文教育的方式,科举应试人士存在三个明显的等级,即身份。中国的秀才类似于西方的学士学位。举人则相对于西方的硕士学位,必须由秀才为基点考试晋升,不过,“硕士学位要比学士高出很多,随之也就更加尊贵而且有更引人注目的特权”。[14]进士则相当于西方的博士。中国进士的获得难度更大,但是回报也更大。进士“属于取代硕士地位的另一个社会阶层,并被算作是全国高等公民之列。”并且进士和举人之间的差别很难让西方人理解。在他看来,“一个外人很难体会他们的地位比他们昨天的同事们高出多少,而那些人却总是让他们上座并以最奉承的称呼和礼貌来款待他们。”[15]对于中国的科举功名,利玛窦坚持以西方的学位制度为参考坐标进行理解,认为中国科举考试体系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强调科举功名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强化有着特别的作用,远比西方的学位证书更有社会影响力。
卫三畏认为科举考试体系分为四级,认为科举功名分为秀才、举人、进士和翰林。他比较深入分析各级考试的不同,秀才“第一级资格可以靠势力和金钱来获得,而第二级(举人)则全凭考试”,至于第四级,即翰林,“宁可说是官职而非考试级别,因为得到这一地位的人列入翰林院的名单,而且领薪金”。[16]卫三畏更关注科举考试体系中各级考试竞争的残酷。“官职的荣誉和权力是多年坚韧学习的激励和报偿。二十名中举者之中得到官职的不及一人,百名应试者之中考取的不及一人。”在科举考试体系影响社会分层的方面,卫氏更强调秀才考试的作用。“受教育的人形成了这个国家的唯一特权阶级;有了第一级学位,就使自己进入士绅阶级之列,被认为苦读付出的一切代价得到足够的补偿。”秀才本身拥有一定的社会和经济特权,“中国教育和考试制度的实际好处,在授予举人之前已大部分做到了。”因为科举考试培养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阶层,卫氏认为中国科举制度有利于维护传统官僚社会的长期存在,“这样的考试比其他任何单一的原因在维护中国政府的稳定并说明其连续性之上已经作出更大的贡献。”[17]
丁韪良延续了利玛窦的看法,认为科举考试体系分为三级,即乡试、会试和殿试,对应的科举名分为“秀才”、“举人”和“进士”。“秀才”的称号相当于学院或者大学授予的学士学位,“举人”称号相当于硕士学位,“进士”称号相当于民法博士或法学博士。不过,对于科举功名的特殊性丁韪良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中国的学位代表的是才能,而非学识;它们是由国家授予的,没有经过学校或学院的干预;它们还带有官衔的特权;而且他们只授予考生中比例很小的一部分。西方的学位正好相反,它们与做官无关,它们所证明的——假如能证明的话——是学识的长进,而非能力”。
至于“翰林”,丁氏认为其与皇家学院院士对等,因为两者都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但两者跟政治的疏密关系不同,“欧洲的学术院是在贵族或皇家赞助下自发成立的组织,但翰林院却是一个文官团体和政府组织,也是整个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翰林们并不是为了热爱学问而试图参加这个组织,而是为了这个职位所能带来的荣耀,尤其是把它作为获得肥缺的跳板。[18]两者对具体知识的掌握也有着很大的差异。“从科学的观点来看,把中国的翰林与法兰西学院院士(或甚至西方的普通平民)来作比较是不公正的。因为自然科学正好是翰林们不擅长的知识门类”。在丁韪良看来,尽管翰林们对中国历史熟练掌握,但是对于西欧历史一无所知,对于近代地理学,动植物学、日心说等近代科学知识所知甚少。他们的精神和目标和法兰西的院训“创造与完善”是格格不入的。[19]显然,在细致比较中西考试的差异方面,丁氏认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与政府管理更加紧密,得到的回报也与权力和社会威望更为密切,而西方的教育考试更多注重知识与学术,而不仅仅聚焦于官吏选拔。
由于经历与知识不同,来华的西方人士有关科举考试体系的认识存在分歧,如麦高温坚持科举考试“四级说”,即科举功名分别是秀才、举人、进士和翰林。他承认科举功名与西方学位制度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两者所教育和掌握的知识明显不同,“用西方的观点来看,获得以上学位所需要的知识是贫乏而有限的,在我们英国学生的眼里简直少得可笑。中国学生们所需要的所有知识就是对儒家经典深刻而又透彻的理解。他们对英国学生在中学里所学的基础课程尚且知之甚少,更不用说大学中那些高级课程了。数学、天文学、几何学、地质学等,这些名词对中国学生几乎是完全陌生的,至少英国青年人必须学习的一些纯科学的课程更是中国文人闻所未闻的。”
尽管西方人士对科举考试体系的层级认识存在一定的分歧,但他们都看到科举考试与文人集团的特殊关系,看到科举制度对传统士人身份的塑造,看到了科举制度对传统社会的特殊影响。他们注意到科举考试与社会阶层形成的密切关系,特别是教育权成为中国管理层与精英层入门的重要砝码,科举制度成为中国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他们清醒地指出科举制与西方学位制之间的本质区别,如双方所有的知识不同。立足当时西方人士的立场,中国的科举制度及其塑造的士人,无疑是有着明显的落后标志。尽管,这种判断本身也展示出近代科学革命以来西方士人的殖民心态和心理优势。
3 应试科举与传统教育
从科举考试的准备来看,应试教育占有非常明显的位置。教育与考试始终互为矛盾、互相影响,科举制度与传统教育亦不例外。虽然科举制度在动员人们投资教育、读书识字方面功不可没,但是其浪费士人精力,扭曲教育方面同样也是罪孽深重。在西方人士看来,科举制度在促进教育发展方面,似乎弊多于利。
首先,科举制度影响中国学科知识和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即人文学科发达,而医学、数学等科学相对落后,进而影响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利玛窦观察到,“在这里每个人都很清楚,凡有希望在哲学领域成名的(按:通过科举做官),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其原因是“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象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希望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20]科举制度给中国传统教育所造成的重文轻武的现象,深刻的影响中国的民族性格,“凡希望成为有教养的人都不赞成战争,他们宁愿做最低等的哲学家,也不愿做最高的武官,他们知道在博得人民的好意和尊重以及在发财致富方面,文官要远远优于武官。”这样,中华民族也形成了爱好和平的民族性格,因为“从帝国建立开始以来,人们就更愿意学习文科而不愿从事武职,这对于一个很少或没有兴趣扩张版图的民族是更合适的。”[21]有关科举制度对民族性格的形塑,丁韪良也有类似的观点,“我们亲眼目睹这种力量强大得足以将满族这么一个勇敢的游牧民族改变成为中华民族中最中国化的民族。正是教育给生活在各种不同自然环境下的中国人身上打下了一个统一的烙印。”[22]
其次,科举制度的成功使得传统教育发展出现不健康的状态,成为一种目标教育和短视教育。丁韪良认为科举制使得中国传统教育并未得到政府的资金投入,而是依赖私人的投资。“实际上,教育一贯是通过私人集资和公共募捐的方式来办的,而政府则满足于摘取最好的果实和采用适当的激励措施来促进人才的培养。一个这样做的政府不能被指控为忽视教育的权益,尽管这种赞助的有益影响很少能渗透到社会的底层。”[23]政府关心的只是官吏培养,而不是教育的本身发展。“政府并没有看到教育本身的价值,而是把它当做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教育的伟大目标就是保证国家安定;保证国家安定靠的就是能干的官吏,而教育就是使官吏们为了履行职责而作准备的一种手段。这个目标一旦实现,政府一旦获得了这种能干官吏的适当来源,民众的教育不再是一个目标。”[24]以科举考试为目标的传统教育显得发展缓慢且误入歧途,“把参加科举考试定为学习的永久目标必然会使教育的影响变得肤浅。……这种作文耗费紧张而无用的大量精力,这就好比是西方人对于拉丁语诗歌的热忱,后者曾经统治了教育机构,直到现代科学的兴起推翻了这种统治。”[25]
再次,科举制度的残酷竞争与恶性发展是传统教育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卫三畏看来,由于科举制度的影响,中国教育的目标发生扭曲,中国古代教育的大目标,并不在乎学习知识,而在于训练心灵,纯洁情感。“读书仅仅被看作获取一定目的的手段,很自然的结局是,当一个受教育的人达到了目标,他不会怎么乐意将这些谋求职业的手段转变为人生指南或欢乐。”[26]中国教育制度的真正价值在于通过考试和授予的学位,可以成为学生进入官府的通行证。美国传教士何天爵批评尤为犀利。“在中国,读书求学的一切动机和最高期望,就是要步入仕途。当每一名孩子由懵懂无知到渐谙人事而进入学堂时,他首先被灌输和想到的,便是读书做官,而所有父母在为孩子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时,他们念兹在兹的,也不过如此[27](第191页)”跟西方人比较,“西方读书人不一定是为了做官,而所有那些东方的莘莘学子们孜孜矻矻、皓首穷经追求学问的明确目的,就是为了做官。他们视做官为梦寐以求的终身职业。”[28]
同样,卫三畏看来,科举考试伴随而来的是特定的科举式教学,带给孩子更多的是痛苦。背诵是科举教学的特色,但是背诵不能解决孩子的学习问题。“他们并不设法便利学生认字,不按字的组成部分来安排;而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认,就像教孩子从标本组中识别矿物的名称和形状一样。像这样的学习程序所取得的结果,必然使幼稚心灵的力量没有得到正确知识的滋养而发展,只能是天赋受到遏制,在脑力功能中灌输奴隶式地顺从于金科玉律,塑造中国学生的智力就像经过园丁辛苦地劳作,被扭曲成盆景的小树一般,这样违反自然的栽培法只能长出不像样的果实。”[29]
丁韪良认为“中国人在智力上并不逊于所谓的‘最优等民族’”,尽管“一个欧洲的五岁儿童能比十岁的中国儿童表达更多的思想”。[30]在他看来,造成中西知识教育差异的更大原因来源于科举制的导向作用和教育方法的落后。科举制倡导的是“纯粹是智力文化”,且用“最坚决和有效的方式”推行,其规模“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与中国相匹敌。”[31]科举教育方法落后,缺乏创新的空间,“在其他国家,哪怕是一个启蒙课程的教师,也会给随机应变和原创新留出空间。……在中国却没有任何这样的情况。”原因是,“在这个以整齐划一而著称的国度里,艺术和文学的所有过程都采取固定的模式,就像他们的衣服样式和梳头的方式那样。学生们全都沿着他们的祖先在一千年前所走过的道路,而这条路也并没有因为有这么多人曾经走过而变得更为平坦。”[32]更为根本的是,科举制度在中国遭到滥用。因为“科举考试的竞争制度似乎注定要在推动思想运动中扮演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而这个思想运动的起始阶段已经清晰可见。”,尽管过去科举制度“迫使中国人的心智在过去长时期内部都像碾磨一样在原地打转的话”,但“那并非该制度本身的错,而是人们滥用了这个制度。”[33]
最后,科举考试及其配套的教育制度存在致命缺陷。科举考试的内容存在知识上的天然不足,在卫三畏看来,科举制度的过度发展与膨胀,加之中国语言的复杂、难学,使得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对其他人种、年代和土地全然不知,这就是他们的不幸,远非他们的过错,他们因孤立而遭遇灾难。他们完全不懂,学习外界的道德、科学、政治观念将会带来持久的利益。既没有地理、博物、数学,也不将别国的历史和语言作为课程的组成部分,只是一味地读经典著作,自然在他们的国家培育出扭曲的观点。”因为知识的缺陷,使得官员的性格也发生扭曲,形成自负无知的性格。“官员一说到自己的力量、资源和相对影响,脑中充满了自负、无知和傲慢,一遇到更有技巧或更强大得对手,就陷入无助的地位。”[34]何天爵也认为科举制度不能胜任时代的发展,“一位头脑敏锐和智慧在某些方面不逊于任何欧美人的中国政治家对于最基本的科学原理却一无所知,他相信地球是方的,坚持认为日食、月食是由企图吞吃太阳或月亮的天狗造成的,他确信狐狸会随意变成人形。”[35]
总之,对于科举时代的教育体制,西方人士普遍持一种批评的立场,特别是立足现代自然知识的基础上,批评科举考试内容的狭窄,教育方式的呆板,教育内容的单一等。倪维思的论断有着很大的普遍性,“中国的教育体制虽然能使人的记忆潜力和储量发展到一种绝无仅有的程度,但它却打击和阻碍了思想的自由表达和创新能力”。[36]
4 西方视角与历史路径
西方始终是一个变动的西方,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停滞的中国。大约从16世纪到20世纪,西方对中国的整体认识历经一个从崇拜、仰慕到蔑视和不屑的过程。同样,西方人士对科举制度的认识,也历经从浅到深,从局部到整体,从感性到理性的复杂过程。明清之际,利玛窦最先认识到科举制度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殊作用;晚清之时,卫三畏、丁韪良则站在一个欣赏和借鉴解读,理解和夸赞科举制度在官吏选拔方面的优秀作用;而到民末清初,麦高温等看到是没落的科举制度、废弃的科举遗迹;到费正清时,科举制度已经更多的是一个纸面上的研究对象,科举开始走入历史的博物馆。
西方人士对科举认识的变化,固然与观察对象(中国科举制度)的兴衰紧密相连,但同时也与观察者(西方国家)实力的快速发展不无关系。历经工业革命的西方世界,大大领先于同时代的中国,他们站在近代科技的高峰,对科举制度的评价,有着几分特定的历史意蕴。
首先,他们承认科举制度的本身优越,却不屑向当时落后的中国学习,处于一种向落后者学习的尴尬心态。如1885年美国政府文治机构委员会宣称:“如果不带有任何主观故意宣扬中国的宗教或帝国主义,我们将能看到世界上最闻名的和最古老的东方世界的政府为什么一直要求采用考试的方式录用政府官员这一事实;如果这种方式还有一点可取之处的话,难道还能不让美国人民享受它的好处;孔夫子已经交给中国人政治道德,中国人已经能够阅读书籍,使用罗盘针、火药、乘法表,而那个时候,我们这块大陆还是一片荒凉,难道还让我们的人民不再使用这些东西不成?”[37]这一宣言本身就宣告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尴尬地位。科举制度成为西方唯一可以借鉴的地方,似乎也越来越为人们所遗弃。
其次,他们更多陶醉于自我的西方中心观念,认为自身代表进步的现代思想,科举制度的发展不适合时代的发展。何天爵尽管承认科举制度“比其建立时期以及以后许多世纪中在世界其他地方所发现的任何制度都要好的多”,但是科举制度“与现代的知识发生接触和产生对比时,它就变得相当怪异了,再也不能胜任其依然为之服务的目的。”[38]1897年,德国人骆博恺认为科举考试作用有限,“按照欧洲的概念,这次考试的结果是相当可悲的。这种国家考试,严格按照以往的传统,只考文章的写作,只要求考生以学得的中国文学知识和写作技巧表达中国风格的复杂思想。国家官员都是文人,并无任何治理国家的专业知识,按照我们的概念,是无法将国家领导和治理好的。”科举考试成为中国政府因循守旧的代表。“1897年的国家考试清楚地表明,中国并未认真采用西方文化,依然要按照它的惯例行事,世界强国似乎终于看清了这点。”[39]
再次,他们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源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何天爵曾与当年多位举人讨论考试的不公正问题,大家控诉的是满汉的不平等,满人更容易获得功名。他描叙以为候补举人的日常生活“他知道一长串省府官职序列的每一处空缺,也知道每一个职位的特点和薪水,他对于官场的每一丝丑闻都津津乐道……他穷困潦倒,住在一家简陋的客栈中一间正对马厩的房间里,每天晚上悄悄地洗衣服,每个月靠不足两个银元的微薄收入生活。”[40]麦高温在1909年所写《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谈到科举制度废除后的某种凄凉:“在中国,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开始了。那些曾容纳一万考生的巨型大厅现在已被遗弃,孤零零地呆在一旁。它们的辉煌已经过去,大门在风中时开时关,巨大的蜘蛛已在房梁上安家织网了。”[41]显然,西方人士对科举的认识尽管有着视角的差异,但是更多的是依据自身判断,或亲身经历,为人们了解科举制度提供难得的史料与记录。
[1]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西传考.邓嗣禹先生学术论文集[M].台北:食货出版社,1980:103-118.
[2]刘海峰.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J].中国社会科学,2001(5):187-202.
[3][14][15][21][22][意]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48,40,42,34,60.
[4][5][6][7][8][9][16][17][27][30][35][美]卫三畏.中国总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60,385,361,390,389,390,387,392,378,375,393-394.
[10][11][18][19][23][24][25][26][31][32][33][34][美]丁韪良.汉学菁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影响力[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207,208,231,240,188,198,201,198,189,202,192,206.
[12][20][42][英]麦高温.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M].北京:中华书局,2006:36,37,45.
[13][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60.
[28][29][美]何天爵.真正的中国佬[M].北京:中华书局,2006:189,183.
[36][39][41][美]何天爵.真实的中国问题[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29,29,33.
[37][美]倪维思.中国和中国人[M].北京:中华书局,2011:39.
[38][美]Mary Gertrude Mason.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M].北京:中华书局,2006:195.
[40][德]骆博凯.十九世纪末南京风情录——一个德国人在南京的亲身经历[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8:215-217.
Westerners’Perspective about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U Siwu
Modern westerners give a unique analysis about the function,system and traditional education of Chines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based on their own experience or western perspective.They give a positive attitude about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selecting talents,but have a deep sigh for the negative effects such as hindering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alents.They appreciate the thorough design of the system,but at the same time,they criticize backwardness of the examination content as westerners.These statements have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for studying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reflecting education for us today.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Traditional Education;Western Perspective
G405
A
1005-8427(2014)05-0057-8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近代中学历史教育与考试互动研究”(项目编号:13CZS07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吴四伍,男,《中国考试》杂志社,助理研究员,博士(北京 10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