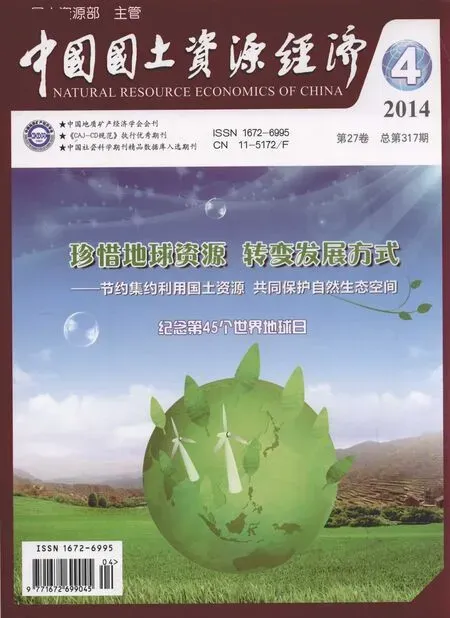生态环境问题三思
■ 姚 霖
(1.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北京 101149;2.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世界地球日”是传播环保理念,唤醒公众环保意识,激发公民环保行为的重要路径。2014年我国纪念“世界地球日”以“珍惜地球资源,转变发展方式—节约集约利用国土资源,共同保护自然生态空间”为主题,其理念实质是通过建构“自然生态空间”与“国土资源利用”之间的关联,倡导转变资源利用的非可持续性方式,以实现“美丽中国”的旨愿。当前,从方法论与技术层面讨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研究,已然获得了丰硕成果。但知识积累与技术更新并不一定能扭转现实的困境。究其原因,皆在于理念的滞后。观念先行于实践,思想虽无形,但其影响却最为深邃。人类在遭遇生存环境每况愈下的形势前,不仅需要思考解决燃眉之急的有效路径,还需展开积极反思,为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思想参照。基于此,笔者尝试提出一隅之见,以期方家指正。
1 生态环境问题的内涵
近30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外汇储备第一,制造业产值第一,经济总量第二的国家。因国情使然,国家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森林破坏、植被退化、湿地减缩、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地质灾害、大气污染、地下水污染、生物种类锐减等诸多生态环境问题,并已然影响到了国民的健康与生活。“问题”是内在矛盾的外在表征。欲了解生态环境究竟是如何一个问题,还需着眼其内涵。
“生态”是“生态学”的核心概念,即海克尔(E.Haeckel)为克服启蒙运动天人两分的弊端,在1866年根据造词法造出来的ecology。其词根“eco”,指“house”,词缀logy意指在打破“混乱”后步入了“逻辑”的“秩序”。“house”作为人的居所(区域),需具备满足人类生存与生活的功能——它能够遵循秩序(logos)来调适包含水、土、气候、生物等外部自然环境与人类之间关系的系统(ecosystem)。“生态学就是通过研究这个系统来理解家乡的家园学。”[1]在以人为利益中轴的家园中,自然环境被赋予了价值的意义。与此同时,自然环境还禀赋了自然的“物属”。自然资源作为生态环境的重要内容,是生态系统调适的参与主体。一方面,自然资源在生态承载力内充当生境的角色,滋养着万物的生息与繁衍;另一方面,当生物对资源的需求越过生态承载极限,将会导致生物无法获得能量输入而致使生命数量与结构发生变化,以实现新的资源供需平衡。可见,仅就自然生态而言,生态系统在满足“尊重自然生态承载力”与“生态系统调适自在发挥”的 条件时,就会呈现良性状态。然而,在石圈、土圈、水圈、大气圈以及生物圈组成的生态系统中,因人的“不当干预”导致生态系统调适条件的改变,进而造成了不利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
2 生态环境问题的成因
探寻问题的肇始,对深入了解问题是大有裨益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成因甚为复杂,表现形式也多样[2],但人为因素却始终无可遁形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存在。
2.1“工具理性”1“工具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渊源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提出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工具理性强调通过工具的确认,达到对效率最大化的追求。这种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的价值观背离了对生态环境运行规律的尊重与理解。的张扬
人类最直接最有效地干预自然界便是使用工具,因而对存在于“工具”背后的思想进行探讨也显得尤其重要。工具理性的偏颇,实质源于高效率地追求短浅利益而致人文理性丧失,使得人们无法正确看待“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体自我”之间的关系,进而衍生出诸多环境问题、社会问题以及个体心理问题。纵观人类与自然交互的历程,人类在经历“‘自然中心主义’的原始文明,‘亚人类中心主义’的农业文明,‘人类中心主义’的工业文明”[3]期间,其知识与技术不断获得更新,“驾驭自然”的能力也日渐增强。这种在原始文明与农业文明时代因“工具”的功能有限,暂未表现出严重破坏力的能力于工业革命后冲破了以往技术的桎梏而愈加强大。在效率的刺激下,人类贪婪地向大自然摄取资源,无限制地接近或超过自然生态承载阈值。在人类短暂盈利不断得到实现时,“工具理性”也由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席位。更为担忧的是,工具理性还搭乘了“现代化”的话语体系,获得了“普世文明”的支撑。随之,标榜“科学”、“中立”、“价值无涉”的“科学技术”(工具),在全球范围内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嵌入各地人民的日常经济文化生活之中,促使他们用“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去改变着他们熟悉生活方式。“技术的可能性和后果是如此无所不及,一切事物如今是如此地打上了技术的烙印,而技术的发展速度又是如此令人咂舌,以至于使人感到,在技术许诺的本身也同时出现了对人类及其未来的可怕的威胁。技术正在变成全球性的力量。它开始染指人类历史的根基,而且正在向人类历史注入极不稳定的因素。”[4]其结果是,人们为“眼前利益”而放弃了长时段内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位育2“位育”源于《中庸》:“致中和,天下位焉,万物育焉”。该词作为一个概念,最早由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提出,主要是指生物个体或群体如何在历史时空中与环境取得和谐关系。智慧”,在“工具理性”的模式下,肆意破坏着自然生态空间,使致生态环境岌岌可危。
2.2 经济活动的失位
联接自然与社会的经济活动,因创造人类福利而促进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也因其运行失位而致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经济学英文名economics,词源为经济economy,源自古希腊语οικονομια(家政术)。Οικο意为家庭,νομοδζ为方法或习惯”。[5]最早使用经济概念的色诺芬(Xenophon)在他的《经济论》中将经济理解为“家庭”与“管理”。在中国,“经济”取自商朝《礼记》中的“经世济民”,至东晋时代“经济”才得以正式使用。清末,严复将economy翻译成“生计”,随后孙中山从日本引进“经济”一词,“经济”正式成为economy的翻译用语。依词源可见,不论是满足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西方经济学初衷,还是以先国家而后侧重生计的中国经济思维,皆关怀个人与社会的福利。从理论上来看,经济活动以“改善人民的日常生活条件”[6]为宗旨,遵循通过“生产、交换、消费与分配”的过程,最大效率地调配有限或者稀缺资源的轨道。然而,不论是在市场经济、指令经济或混合经济模式下,因经济活动参与主体的多样,利益需求的各异,导致了经济主体会以“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使用“净化污染的私人边际收益等于净化污染的私人边际成本的方法,来决定利润最大化条件下的污染水平”的思维,去权衡是否减少生产的负外部性,其结果必然会出现经济的无效率。经济无效率与负外部效益,又势必会损害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在缺乏政府有效监管的情况下,经济失位带来的结果则表现得更为严重。允许出现且事实存在的经济活动失位,使得在“经济人”(Economic man)得以能够在自然资源的“公共经济属性”上大做文章,从而为自然资源非可持续性开采与利用埋下了隐患。
2.3 公共物品属性作祟
市场经济时代,作为稀缺性公共物品的自然资源,无可规避地要参与至经济活动之中。按保罗·萨缪尔森(Paul Anthony Samuelson)的界定,“公共物品(public goods)是不论个人是否愿意消费,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个成员获益的物品”。[7]其特征之一是公共物品不属于私人所有,虚化的所有权导致难以计量公共物品利用的成本与收益,其效用最大化也很难通过市场来实现。其特征二是社会效益的整体性,公共物品的使用与消费都会产生外部性效应。自然资源作为稀缺性公共物品,不仅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特征,还具有环境意义:其一,自然资源作为环境的有机部分,服从自然生态规律,并参与生态环境的调适。自然资源的开采与破坏并非简单地物理切割。自然资源从“地下”转至“人手”的结果,必会导致整体环境功能的受损与丧失;其二,自然资源的公共产权属性,为满足“经济人”(Economic man)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创造了条件。赋理性思维的“经济人”(Economic man)会因自然资源的公共产权性质,而不顾资源开采与利用可能产生的负外部性与公众福利。偏离追求公众与个人福利的经济活动,产生了经济无效率。经济活动的失位,衍生了稀缺性自然资源的浪费,违背了经济活动原有的初衷。如此为“经济人”(Economic man)利用自然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谋取私人利润最大化提供了机会,由此在非可持续性的资源利用中造成了很强的自然环境负外部性。其结果是,有限的国土资源日渐枯竭,其原本依附和参与的生态环境被破坏,公地悲剧与资源魔咒不断上演,生态环境危机频频出现。
2.4 政府环境管制有待完善
矫正生态环境的外部性问题,需政府实施有效的环境管制。正如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所说,“政府应当为人民做那些他们想做,但仅凭个人力量无法做到或做好的事情”。就中国自然资源的市场配置情况来看,当前已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权益,建立了诸如配置矿业权、农地承包经营权、城市用地权、海域使用的出让与转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源的有效利用。另外,各级政府已开始探索运用行政工具与市场办法(如,排污费与可交易的排放许可证),来杜绝企业发生污染行为。现行环保政策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仍存有待完善之处。
从目前还未建立配套的环境市场与环境权益保障体系来看,我国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制度设计仍以保障自然资源的高效开发与利用为重心,而未给予生态环境保护以重视。故而,我们看到具体涉及自然资源开采与使用权的出让与转让的法律法规中,没有清晰与详实的环保责任与追究制度。环境保护权益体系和政府监管体系的建设滞后,为生态环境遭受经济性破坏提供了制度性漏洞。于是,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权的拥有人,在开采与利用自然资源时会忽视其环保责任与义务,而不顾其开采行为可能引发或诱发的地貌破坏、生态系统失衡、地质灾害、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
3 生态环境问题的解题路径
如何破解生态环境问题是必须思量的问题。一般来说,研究者多聚焦于具体的实施办法,例如,地质灾害防治、土地复垦、三废治理、封山育林,关停并转污染企业等等。事实上,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同人类发生能量交换的多生态系统。因此,环境工程的具体操作技术也决非一言能够概括,但其建设最为核心的“路径”却是能够探讨的。基于上文讨论,本文试从“消解工具理性、政府环境有效管制与环境教育”三个方面来展开。
3.1 以“位育智慧”消解工具理性
“工业文明以降,‘技术’已成为维系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但人类作为大自然的有机部分能够存活并繁衍至今,最为关键的原因是依靠人民在长时段历史空间中凝练而成的‘智慧’”。[3]这笔财富蕴含于不同自然环境的经济文化类型、维系社会和谐的道德要求与保护自然环境的信仰之中。不论其智慧载体如何多样,其本质是强调人如若要在长时段的空间中获得生存与发展,则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去实现“致中和,安其所也,遂其生”[8]的“和境”。正如《国语·郑语》载:“夫和 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9]“多种因素通过相互配合、协调来组成新的事物或达到理想的效果,相反则损。”[10]“和”的解释魅力涵盖了人与物、人与人以及人与己的范畴。“‘和’是旨在促进参与体优化组合而达成和谐共处”。[10]承上意,“和境”是对“人与自然”和谐状况的一种描述,其中“共生”的内容与自然环境保护理念相切合。这恰为解决因“工具理性张扬”而不断出现的“资源诅咒”、“发展悖论”等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思路。思想的历史资源并非因已发生而失去现时的意义。相反,开展生态文明建设需采撷历史智慧。保护地球资源,建设人地和谐的生态文明要回归于人的本身,消解导致自然资源过度无序开采利用的工具理性,需要从中华民族传统智慧中摄取营养,并将其付诸实践。
3.2 衔接政府管制与市场办法
自然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与政府管制的局限是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原因。如何在现有市场与政府管制下,探索保护生态环境的路径亟待解决。萨缪尔森认为,“对付由外部性造成的无效率的武器是什么呢?最常见的方法是政府的反污染计划,即通过直接控制或经济激励来引导企业矫正外部性。更细致的办法是明确并加强管理,以促成私人部门之间通过协商达成更加有效的解决办法”。[11]如“制定环境标准、发放许可证、公布禁令、进行配额管制、收费、保证金制度、负外部性权利交易”等政策,皆为政府应对不完全竞争、外部性和信息失灵等市场形势,凭借行政权力直接或间接干预市场配置的努力。然而,如若完全倚重于政府管制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却又很难成功。因为,政府管制虽然能够消除“部分”的市场失灵,但却不能干涉其市场配置的全部过程,有时甚至会因政策失真而导致市场的“不效率”,进而影响社会的整体福利。故而,我们认识到要解决自然资源的外部性问题,政府管制不可或缺,但又不能完全倚重。
自然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离不开市场发挥自身的调节功能。所以,除需要建立健全政府管制外,还应尊重市场自身的机制。例如,实施自然资源确权便是积极尝试市场办法之一。自然资源确权是现行规避公共物品属性所导致负外部效应的主要办法,它通过明确自然资源使用人的权利与义务,使其在经历市场“讨价还价”后,实现高效配置,进而将自然资源外部性内化。自然资源确权不仅促进了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而且为环境治理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主体,保护了公共利益。不可忽视的是,资源权益要发挥良好的作用离不开健全的市场机制和有效的政府管制。这其中,政府实现了市场无法涉及的社会尺度,市场满足了政府管制无法触及的高效配置。因而,在现行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需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间实现衔接并用。
3.3 环境教育
生态危机不仅是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从深层次考察,它还是个文化问题。人生存于特定的文化模式之下,受其所处文化的濡化(enculturation),完成着代际间的涵化(acculturation)。生态意识与生态行为也随文化的横向与纵向流动,参与了人的塑造。因此,承当文化传承之责的教育自然不能缺位于生态文明时代的历史呼唤,开展环境教育,培育公民环境意识,规范公民环境行为,对于美丽中国的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开展环境教育绝非为“喊口号”式的“大肆宣传”。笔者认为,教育是影响人身心健康向上的社会活动,受制于社会大环境、学校中环境以及家庭小环境。如要实现教育目的,需把握“一个尊重,二个层面,三个落脚点”。“一个尊重”,即教育活动要尊重人的身心发展规律。例如,在环境行为培育上,就应当考虑到教育对象的性别、年龄、民族等因素,制定合乎个体与群体特征的教育方案。“二个层面”是环境教育的开展需从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两个方面入手,在培育个体环境意识的同时,要鼓励开展环境保护实践,并帮助他们在实践中提升环境意识。“三个落脚点”,则要求教育着眼于受教育者的生存空间。其一,在学校教育中可通过环境课程,积极开展环境户外活动,培育个体积极的环境态度与环保能力。其二,在家庭教育场域中,鼓励家长以言传身教促进儿童环境素养的提高。其三,开展多样的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社区活动,以增进社区居民的环保意识,承接家庭与学校的环境教育。总之,良好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培育,虽不可一蹴而就,但其意义却是久远的,也是值得为之付出的。
[1]张海洋,包智明.生态文明建设与民族关系和谐:兼论中华民族到了培元固本的时候[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3(7):1-5.
[2]陈泉生.论环境问题的分类[J].亚太经济,1997(6):56-57.
[3]姚霖.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管窥[J].青海民族研究,2014(1):56-60.
[4][荷]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M].李小兵,谢京生,张锋,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5]陆谷孙,等.英文大字典(第二版)[G].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587.
[6][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9版)[M].萧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6.
[7][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9版)[M].萧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49.
[8]汉语大字典(第一卷)[Z].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成都:四川省新华书店,1987:183.
[9]左丘明.国语[M].尚学锋,夏德靠,注.北京:商务出版社,2005:250.
[10]姚霖.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教育的现实境遇与价值选择[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1(6):64-68.
[11][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9版)[M].萧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