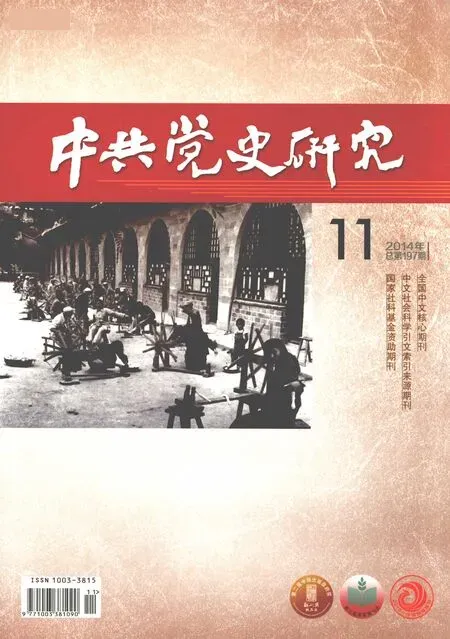政权初建背景下的政府与乡村*——山东省郯城县一九五三年“毛人”谣言的传播与平息
侯松涛
(本文作者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北京 100088)
学者李若建在他关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的研究中,集中关注了“毛人水怪”谣言。如李若建所言,“毛人水怪”谣言从传播的范围、影响和持续的时间来说,当为20世纪中国最大的谣言,1953年的“毛人水怪”谣言则是最集中的一次爆发。①李若建:《虚实之间: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页。笔者近年来在对山东省郯城县50年代档案的整理中,对此有所关注并搜集到较为完整的相关史料。总体而言,李若建的研究思路主要是以公开出版的地方志等资料为基础而形成的解释性框架,亦典型地体现了其学科背景特点。与之不同,本文的研究则是以档案史料与口述访谈资料为基础,将1953年“毛人水怪”谣言传播与平息的纵向脉络置于中共政权初建的背景下,观察与提炼其中所蕴含的新生政权在基层乡村初步巩固的内在逻辑,虽不敢说可与已有研究相得益彰,但仍不失为值得深入的尝试。
一、拉锯—解放: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革命政权建设的区域性轨迹
关于1953年“毛人水怪”谣言,笔者关注的个案模型是山东省郯城县。该县位于山东省最南端,恰为山东、江苏两省交界之地,亦可谓中国南北文化交界之地。西方学者史景迁曾以此地为个案进行过清代乡村社会的研究。①参见〔美〕史景迁著,李璧玉译:《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在历史上,郯城县是中国无数个极为贫瘠的地区之一,境内几无任何自然资源。与此相伴随的,是境域内的土匪猖獗,1924年“县境匪大小杆股不下三、四十起,绑票、撕票举不胜数,商号、平民无不遭劫”。②《郯城县志》,深圳特区出版社,2001年,第11页。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下,当地百姓在灾难降临时只好求助于神佛,对各种“鬼怪”则充满畏惧。但客观而言,郯城的境遇与宏观上中国近代以来的乡村命运并无太大差异。更值得关注的,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革命政权建设在郯城县所体现的区域性轨迹。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之后,郯城一直处于国、共、日三方势力并存拉锯的状态。在此过程中,中共革命力量与日伪、国民党经历了多次互有进退的战斗。1940年1月,八路军东进支队攻克郯城,给郯城带来了第一次中共革命的解放,但11月即被迫退出,日伪占郯城。1943年1月,八路军115师攻克郯城,此为中共革命给郯城带来的第二次解放,但2月份郯城又被日伪侵占,成为“拉锯式游击区”。1945年7月,八路军再克郯城,给郯城带来第三次解放,此后至1947年,中共革命政权在当地展开了规模较大的土改运动。但1947年1月国民党进攻,中共政权又一次撤离。此次撤离给当地留下的是一些经历者至今记忆犹新的惨烈与血腥:土改运动中的受冲击者——地主富农等组织还乡团“卷土重来”,又开始“倒果实”,全县被倒回土地25万亩,房屋2.4万间,大牲畜7780头,粮食594万斤,银圆31.827万元。另外,干部家属及群众被枪杀、活埋2124人 (其中活埋250人),全县活埋人坑145个。③《郯城县政权志》,1993年讨论稿,第197—198页;《郯城县志》,第21页,直至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初起,位于战役重要区域的郯城才第四次获得最终解放。
新中国成立之前,在各股势力的时进时退中,在各类土匪的袭掠中,乡村的生存环境极为恶劣。虽然现在已经很难清楚近代之前百姓的“跑反”历史(“跑反”指为躲避兵乱或匪患而逃往别处),但在一些尚未故去的老人的回忆中,“跑反”是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时期的拉锯历史留给他们最深的记忆。日本人来了跑,国民党来了跑,土匪来了跑,共产党来了开始时也跑,早已难以记清楚哪一次跑的是谁的反。④笔者在山东省郯城县红花乡黄庄村 (当时属郯七区)采访何氏的记录 (2012年5月26日)。何氏,女,1924年生,当时为中农成分。就中共革命而言,虽然1927前后在当地即有活动与影响⑤《郯城县志》,第12页。,但在郯城动荡不安的历史中,尤其是中共革命在拉锯中的几番进退,所谓的“解放”给普通百姓带来的不是中共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而是一种迷茫感和不稳定感。虽有1949年中共革命的胜利,可谁又知道共产党政权此次给郯城带来的“解放”能持续多久?乡村百姓的这种心态不可能在中共革命刚刚胜利不久的1953年即全然消失。
二、毛人—干部:乡村基层政权初建时遭遇的尴尬
根据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基层政权的建立健全是整个政权巩固的基础,故此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共非常重视基层政权的建设。1950年12月8日,政务院第62次会议通过《乡 (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及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为基层政权的建构提供了指导,此后,基层建政运动在全国已解放地区次第展开。于此过程中,到1952年底,郯城县共建立了136个乡,共配备乡政委员1108名,乡政府下属的各种委员会亦在各乡开始逐步建立。⑥《郯城县人民政府关于民主建乡情况总结报告》(1952年11月22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县政府永久卷11-1-6。但整体而言,这只是初步构建了基层政权的构架,健全与巩固政权的相关工作才刚刚开始。
据李若建的考证,“水鬼毛人”谣言最早出现于1946年,此后多次爆发。⑦李若建:《虚实之间:20世纪50年代大陆谣言研究》,第14页。“水鬼毛人”谣言在郯城当地亦几度流传,文字资料显示,自1949年起此谣言“连年发生”①《地委关于东海县委的工作情况与今后工作的指示》(1949年12月10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6。,几与中共革命的走向胜利同步并趋。1953年6月25日,正值当地高粱长成、青纱帐起时,在紧邻江苏的郯城县八区白岭乡徐塘东村,村民陈士爱夜晚发觉有两个穿白衣服的人进宅子,第二天对亲戚说这两个穿白衣服的头上有火等,当晚即有一片群众集体睡觉,引起全村恐慌。②《郯城县委关于八区发现“水鬼毛人”谣言情况的通报》(1953年7月13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长期卷1-2-34。此为档案记录的谣言之肇始。自此,谣言在当地逐渐流传开来,形成1953年夏天的集中性爆发。在谣言的流传中, “毛人”的形象是“红鼻子,绿眼睛,夜里能从门缝里钻进去”,“专抓妇女来扒人心”③《郯城县委关于八区发现“水鬼毛人”谣言情况的通报》(1953年7月13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长期卷1-2-34。,等等,从而引发百姓的极度恐慌。
(一)恐慌者
谣言引发的是集体性恐慌。在谣言最为严重的阶段,百姓“挤门塞窗”,有的打鱼叉、买手电筒,闹“毛人”地区煤油、电灯供不应求。白天则许多人不敢下湖 (当地土语,湖即田地)生产,致土地荒芜。一些百姓赶集也扛着铁杈、大刀。④《关于发生“毛人”谣言骚乱情况的专题报告》(1953年7月),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30。夜间则各村不分男女老幼,在政府介入之前亦不分所谓“地主反革命分子与群众”⑤《关于郯城县平息地主、反革命制造“毛人”骚动事件的报告》(1953年8月4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30。,皆分片集体睡觉,“男劳力站岗住在外面,妇女小孩住在里面”。⑥笔者在山东省郯城县徐庄村 (当时属郯七区)采访王元德的记录 (2009年1月6日)。王元德,男,1935年生,当时为贫农成分。竟夜高悬灯火,站岗守卫。并持有枪、刀、棍、杈等利器,一处喊叫全村响应。人心惶惶,自相惊扰,风吹草动,疑为“毛人”。⑦《关于郯城县七区捕灭“水鬼毛人”谣言斗争情况的通报》(1953年7月25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长期卷1-2-29。在此过程中,由于百姓“自相惊疑互相殴打,有的鸣枪放炮”,造成了许多误伤事件。⑧《关于发生“毛人”谣言骚乱情况的专题报告》(1953年7月),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30。据县委7月29日的统计,全县由于骚动群众互相殴打误伤者66名 (其中有因被打过重而死者)。⑨《关于郯城县平息地主、反革命制造“毛人”骚动事件的报告》(1953年8月4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30。
在这种集体性恐慌中,恐慌者包括了所有阶层人群。中共革命的受冲击者亦是如此。如有的地主“夜间自己搞破脸说是毛人抓的”。⑩《关于发生“毛人”谣言骚乱情况的专题报告》(1953年7月),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30。八区一个叫邱如早的地主,半夜睡梦中叫了一声,其妻以为有“毛人”,吓得即用“扫帚乱捕”,结果一家几口人都被搞伤。⑪《邱如早材料》(1953年8月5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八区委永久卷66-1-001。
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基层政权中的许多人也成为谣言的恐慌者,一些干部亦与村民一样,赶紧购买手电筒、火柴等照明物,与村民一起“参加集体睡觉,点长夜灯,一夜不睡”。⑫《一区委关于反水鬼毛人的情况简结》(1953年7月31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一区委李庄公社永久卷63-1-8。有的干部听说“毛人”后吓得起不来,有的区干部晚上吓得不敢出门。⑬《关于发生“毛人”谣言骚乱情况的专题报告》(1953年7月),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30。
还有的基层干部“亲自造谣,吓唬群众”,“领头闹‘毛人’”。如七区一村主任陈士祥拿广播筒广播说: “毛人变狗啦,又变火球啦。”并“假借政府名义”下令砍伐村周围树木、苘麻,以便预防“毛人”。⑭《关于郯城县平息地主、反革命制造“毛人”骚动事件的报告》(1953年8月4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30;《郯城七区平息毛人骚乱的初步总结》(1953年7月),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30。有村干部公开地说县委下派去该乡工作的工作人员是“毛人”。⑮《关于郯城县平息地主、反革命制造“毛人”骚动事件的报告》(1953年8月4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30。有的民兵乱打枪,并“吆呼毛人来了”,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村民的恐慌。①《我区谣言传播情况》(1953年7月23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塂上区委永久卷57-1-2。有的乡干部 (一武装委员)夜间乱打枪,结果误伤了一名村民,将其腿打断,等等。②《七区委当前谣言情况报告》 (1953年7月22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七区委永久卷53-1-7。
在谣言闹得最严重的数月,全县各区乡村皆笼罩于一片恐怖恐慌之中,百姓的日常生活几近于半瘫痪状态。
(二)乘机活动者
在谣言传播带来的恐慌与混乱中,亦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乘机活动者”。
首先是中共革命的受冲击者,即当时所谓的地主、富农等“反革命分子”。有的地主“围着草苫子扮作毛人威胁群众”。③《关于郯城县平息地主、反革命制造“毛人”骚动事件的报告》(1953年8月4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30。有的地主“装毛人”想吓跑军属好扒他的粮食。④《郯七区平息毛人骚乱的初步总结》(1953年7月30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七区委永久卷53-1-7。有一地主的老婆下湖乘机偷玉米。⑤《七区委最近三天的情况报告》(1953年8月1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七区委永久卷53-1-7。有的则乘机“倒果实”,如有地主乘机造谣吓唬分到自己财产的村民,将其吓跑后重新收回自己土改中被分掉的房产。⑥《郯城县委对地主反革命装“毛人”吓唬群众,进行反攻复辟活动的几个具体实例的通报》 (1953年8月8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30;《关于郯城县平息地主、反革命制造“毛人”骚动事件的报告》(1953年8月4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30。有的地方亦发现有乘机进行破坏活动的武装特务,有逃亡的原国民党时期的保长造假证件,并乘机“大肆活动威吓群众”,等等。⑦《关于发生“毛人”谣言骚乱情况的专题报告》(1953年7月),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30。
但是,谣言的“乘机活动者”不是只有中共革命的受冲击者,而是形形色色的各类人等,包括许多中共革命的利益获得者。七区一邮局干部半夜里与老婆吵架,其妻极彪悍,该干部几乎光着身子就跑到了大街上,其妻在后拿着扁担追撵出来,大概为顾及自己面子,便吆喝着叫毛人抓着了。⑧《关于发生“毛人”谣言骚乱情况的专题报告》(1953年7月),县委永久卷1-1-30;《郯城七区平息毛人骚乱的初步总结》(1953年7月),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30。七区阴村乡阴南村民兵马保坤“以谣言吓唬看瓜的群众杨生清,夜间集伙五个民兵偷瓜吃”。⑨《七区委最近三天的情况报告》(1953年8月1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七区委永久卷53-1-7。某村贫农李德林因孩子多、家里穷,晚上披蓑衣出来偷玉米给小孩吃,被戳伤 (后因伤重死去)。⑩笔者在山东省郯城县高峰头镇蔺庄村 (当时属郯七区)采访徐祇刚的记录 (2009年1月8日)。徐祇刚,男,1933年生,当时为贫农成分;笔者在山东省郯城县高峰头镇前高峰头村 (当时属郯七区)采访侯大江的记录 (2012年6月3日)。侯大江,男,1927年生,当时为贫农成分。八区的一个贫农李记学,在村民正恐慌不已集体睡觉的时候,带着四个民兵“扎了一个草人,给穿上褂子,用手巾包上头,腰中拴上个长绳子,一夜往集体睡觉的群众中扔了三次,每次扔后将绳子一抽,抱草人即跑,每次均引起群众害怕,齐声呐喊”。⑪《郯城县委对地主反革命装“毛人”吓唬群众,进行反攻复辟活动的几个具体实例的通报》 (1953年8月8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30。郯城七区有个胡木匠,贫农,村民给他起的外号是“胡小鬼” (由其外号即可知其爱恶作剧的性格,最多算是个农村“二流子”)。一次胡小鬼白天在湖里 (即田地里)看瓜,百无聊赖中便恶作剧式地蹲在谷地里装鬼叫,几个正在附近割草的小孩以为是“毛人”,吓得撒腿就跑,搞得村民几天不敢下地劳动,最后才发现是他装的。⑫《郯城县委对地主反革命装“毛人”吓唬群众,进行反攻复辟活动的几个具体实例的通报》 (1953年8月8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30;《中共七区委两天谣言情况报告》 (1953年7月26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七区委永久卷53-1-7。有的村民不小心刨伤了邻居老太太,为推卸责任,就一口咬定是毛人干的。⑬《郯七区平息毛人骚乱的初步总结》(1953年7月30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七区委永久卷53-1-7。有的村民不小心把自己小孩头刨破了,也说是毛人干的。⑭《中共七区委当前工作报告》 (1953年8月11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七区委永久卷53-1-7。
谣言传播最为严重之际,也成了各地的偷盗事件发生最多之时。这对于乡村而言,比所谓“反革命分子”活动影响更大。据郯城县委1953年8月初的不完全统计,谣言传播期间,5个区发生地主倒算者17起,但发生的偷盗事件亦有16起。①《关于郯城县平息地主、反革命制造“毛人”骚动事件的报告》(1953年8月4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30。许多村庄连续发生偷盗事件。由于谣言恐慌中村民集中睡觉,家中无人,结果小偷乘机偷去许多东西。有的村民六亩多玉米地被“一次性盗净光”。②《关于郯城县平息地主、反革命制造“毛人”骚动事件的报告》(1953年8月4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30。有的一块瓜地被偷光。当地做煎饼 (当地主食)用的鏊子面积一般较大难以搬运,有的村竟也被小偷偷了去。③《我区谣言传播情况》(1953年7月23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塂上区委永久卷57-1-2。以至七区在8月1日给县委的报告反映:“目前群众最迫切的要求是秋收和捉拿小偷保护秋收。”④《最近三天的情况报告》 (1953年8月1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七区委永久卷53-1-7。
因此可见,谣言的“乘机活动者”包括了形形色色的各类人等,不仅有中共革命的受冲击者,亦包括许多中共革命的利益获得者。
(三)谁是“毛人”
虽然“水鬼毛人”谣言在当地连年发生,但1953年的谣言“大多数说是人装的”,“不承认是什么鬼怪,所以只提毛人没提水鬼之事”。⑤《第七区发生毛人情况与今后反谣言斗争意见》(1953年7月21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七区委永久卷53-1-7。因此,当地将此次谣言事件直接称为“毛人”事件。那么,谁是“毛人”?在政府介入处置之前,谣言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共干部。
在谣言的传播中,有说法是:“毛人”“是苏联毛主席分下来的,李庄下了两汽车,都是工作人打扮,专扒人心”。“带着枪奉毛主席命令扒双身妇女小孩配药,好治朝鲜战场受伤的人。”⑥《一区委关于反水鬼毛人的情况简结》(1953年7月31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一区委李庄公社永久卷63-1-8。“白天当工作人员、夜晚当毛人,区里有廿多个,每乡有三、四个。”⑦《郯城县委关于郯城县七区捕灭“水鬼毛人”谣言斗争情况的通报》 (1953年7月25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长期卷1-2-29;《郯城县委关于八区发现“水鬼毛人”谣言情况的通报》(1953年7月13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长期卷1-2-34。“毛人就住在区公所里,逮着毛人可不要送区公所,因为他们是一伙,送去也不处理。” “北京有好几个军官叛变,毛主席已不在北京,跑到上海去了”。⑧《关于发生“毛人”谣言骚乱情况的专题报告》(1953年7月),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30。
因此,在谣言最为严重的阶段,乡村百姓与政府基本形成了对立状态。一些村庄“村干部民兵白天远离我们,夜晚不准干部出门,白天群众站岗,不准穿军装的进前,有送信的传进去,传出来”。县里下派进村工作的干部,村民要求必须检查,搜查是否有铜指甲 (谣传“毛人”的指甲)等“毛人”用的器具,然后才让进村,并不准随便活动。甚至有一个村开会时,有村民站起来称要刨死“工作人”。⑨《关于发生“毛人”谣言骚乱情况的专题报告》(1953年7月),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30。有的干部被村里扣留三天之久。不少工作人员在乡工作时“被群众持铁杈追赶”。⑩《关于郯城县平息地主、反革命制造“毛人”骚动事件的报告》(1953年8月4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30;《七区委当前谣言情况报告》(1953年7月22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七区委永久卷53-1-7。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下派干部在许多村庄已经无法立足。在闹得较为严重的郯城七区,一些村庄不准干部进村工作,“去就要逮要打”。⑪《情况简报》 (1953年7月21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七区委永久卷53-1-7。有的村虽能进村去工作,但有个别地方“晚上近前不上”,黑天即不容靠近。见到乡干部及脱产干部,就“乱喊呼乱骂”“要打”,有的甚至说“不如买枪反了”。⑫《中共七区委两天谣言情况报告 (25、26号)》(1953年7月26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七区委永久卷53-1-7;《七区委当前谣言情况报告》(1953年7月22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七区委永久卷53-1-7。因此,许多下派的县区干部不得不“退出村庄”。⑬《郯城七区平息毛人骚乱的初步总结》 (1953年7月),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30。
由古而今,追溯谣言的源头一般是最为困难的事情。此次谣言的矛头指向中共干部,毫无疑问不能排除革命的受冲击者即所谓“反革命分子”之流的造谣破坏,但此种造谣破坏是此次谣言爆发的源头还是“乘机活动”,至今还是无头之案。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传播过程中将矛头指向中共干部的“毛人”谣言何以能在乡村如此大规模地传播开来?乡村百姓为何会相信“毛人=中共干部”的谣言?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1953年“毛人水鬼”谣言的发生①李若建对此次谣言发生的原因有非常全面的解释。参见李若建:《虚实之间: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第13—76页。,即使有“反革命分子”的恶意造谣传谣,但其“滋生蔓延的土壤”,则是谣言内容与民众思想的“共鸣”。②彭卫:《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76页。郯城虽不是谣言的最早起源地,但谣言的传入与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几经进退的革命政权建设给予当地乡村百姓的心理感受的“共鸣”。正因如此,谣言引发的恐慌是集体性的,其恐慌者包含了乡村所有阶层人群,其“乘机活动者”亦包含了形形色色的各类人等。
谣言中乡村百姓的种种行为,显示了其与新生政权的隔膜与疏离,这也是中共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乡村基层政权初建时所遭遇的尴尬:农民利益的代表者并不为农民所立刻接受。
三、毛人—反革命:鸡生蛋与蛋生鸡的轮转循环
对于政府方面而言,此次谣言事件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共干部,这是最为触动其神经的方面,也确实是一个刚刚取得革命胜利的政权所难以容忍的。一个标志为农民利益代表的革命政权却不能立刻为农民所接受,一定程度上说是一种尴尬。因此,如何实现乡村对新生政权的接纳与认可,实际上成为政府处置“毛人”事件的关键。同时,关于社会中的谣言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即在意识形态框架内进行定性,认为“谣言是完全非法的,造谣惑众的人便是人民的敌人”。③《粉碎反革命谣言》, 《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7日。追谣亦被视为“主要是各级公安部门的责任”。④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1986年,第206—207页。1951年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以反革命为目的,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制造和散布谣言者,处三年以上徒刑;其情节重大者处死或无期徒刑。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第247页。但是,这一定性的具体操作却并非简单和一蹴可就,在谣言的口口相传中,如何确定“制造和散布谣言者”,如何判定是“以反革命为目的”等,皆是具有“技术难度”的问题。因此,郯城县1953年“毛人”谣言的传播与平息过程,不仅基本清晰地显示出乡村基层政权初步巩固的逻辑脉络,亦反映出革命政权的谣言处置技术在乡村的初步实践。
(一)由何入手
1953年“毛人”谣言在郯城县的爆发起于6月,此后逐渐在所属各区酝酿蔓延。由于类似谣言曾连年发生,虽然县级干部下乡巡查时与各地区乡干部有所沟通,但起初并未十分紧张。
1953年7月12日,位于郯城最南端紧邻江苏的七区区委上报县委,当地某村于7月9日“发现闹毛人水鬼”,村民郑景恩女儿小便时发现“有火球向她而来”,吓得“不敢动活喊(原文如此,以下不一一注明——笔者注)”,惊动村民十多人齐去打“毛人”,结果郑家三人被打伤不能动,由此引起村民恐慌, “集体睡觉,都拿棒、各种家伙”。⑥《七区区委给县委的简报》(1953年7月12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七区委永久卷53-1-7。
当七区委的简报7月13日上报县委时,最早发生谣言事件的郯城八区“就该区十个乡来讲,均已传遍”,郯城县委已经连续接到各地的类似上报,便于同日发出《关于八区发现“水鬼毛人”谣言情况的通报》,提醒各地警惕。关于谣言发生的主要原因,《通报》明确归结为“反革命分子有意识地制造谣言”和“放松了对坏分子的管制和监视”,亦提出要检查和控制已处理的“反革命分子”,“防止其乘机报复”。但是,《通报》此时提出的应对措施还是比较克制和谨慎的,要求各区“尽量做到在哪里发现在哪里消灭,发现了什么谣言,要揭发什么谣言”,“在已发现谣言地区要积极采取措施捕灭”,在未发现谣言地区,则要求“加强警惕”,但“不要向乡、村布置”。①《郯城县委关于八区发现“水鬼毛人”谣言情况的通报》(1953年7月13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长期卷1-2-34。
7月14日,七区委召开扩大会议,了解各点各乡情况,会后再次上报县委,“我区现在毛人水鬼谣言更加厉害”,全区12个乡有5个乡较严重,多个乡发生打伤人事件,“有的村以闹起来,干部也没法制了,怎样向群众解释也不听了,也有的干部也随着群众害怕起来,发现严重的乡村工作就受到影响,会也开不起来”,并请示县委“来指示怎么办”。②《七区委给县委的简报》(1953年7月14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七区委永久卷53-1-7。
7月15日,县委下派公安局宋姓局长至七区,与区委干部进行了商讨,但“如何反播谣言宣传内容,怎样进行、用哪些方式方法进行群众的教育”,区委还是不知如何下手,故七区委于7月17日再次上报县委,请求“来一具体指示”。此时七区的谣言进一步发展,全区12个乡已有10个乡“闹起来”。③《中共郯城县七区委目前闹水鬼毛人情况报告底》(1953年7月17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七区委永久卷53-1-7。至7月18日,全区“无有一个村不集体住的,小村集体,大村分片住,高悬灯光,男女每人持各种器具,有……火光等,就乱喊乱打”,至7月20日已误伤30余人。在此过程中,县委于7月19日召开全县三级干部大会,决定抽调35名县机关干部,由县委委员带领分赴各区,七区和八区为平息重点。但由于谣言的矛头指向就是中共干部,在闹得严重的村庄,这些下派干部受到排斥。村民见到下派干部即“利颜利色”,不准接近,白天远离,晚上不许出门。甚至有的村庄不许干部进村工作,“去就要逮要打”。④《七区委给县委的简报》(1953年7月21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七区委永久卷53-1-7。一些乡召开地主训话会时召集不到人,全区大部分乡村“民兵不能集中使用”,乡村干部亦无法进行工作。
面对如此严重局势,乡、村级干部已手足无措,急向区委“乱要办法”,区委干部则“缺乏冷静表现手忙脚乱、束手无策”,只好不断上报县委“反映情况”和请求具体指示。⑤《第七区发生毛人情况与今后反谣言斗争意见》(1953年7月21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七区委永久卷53-1-7。郯城所属临沂地委专署亦下派干部到七区调查,经专署、县与区的共同研究,7月21日,七区委召开全区乡干部大会,集中商讨谣言的应对问题。会议最后通过并上报县委《第七区发生毛人情况与今后反谣言斗争意见》,形成了应对谣言的初步思路。《意见》认为,此次谣言虽然原因多样,但“最主要是特务匪徒”,“是敌人有计划的对我们的阴谋破坏”,“离间我党群关系”并“向政府直接挑衅”。因此,要“正确的估计敌情,分析情况,揭发敌人的无耻阴谋”,“彻底打垮敌人破坏阴谋”。《意见》提出的反谣言方法主要包括:(1)立即动员群众基本与地、富、伪、顽分开居住,不要被坏人愚弄,划清敌我界线,整顿村组织,加强民兵的领导。(2)对因闹毛人误伤者,要进行慰问,并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对象,给予适当的治疗或救济。(3)加强管制工作,对已管制者,要严加管制,未管制者,要严加训话,并要分别召开反革命分子训话会,以及反革命家属会,令其老老实实,保证不造谣,不传播,遵守政府法令,积极进行生产,服从群众管制。在目前青纱帐时期,外出或来人,以及发现坏人谣言等,要报告乡村政府。⑥郯城县档案馆藏,七区委永久卷53-1-7。
七区委的这一思路得到县委和所属临沂地委的肯定,7月25日,临沂地委发布和上报了《关于郯城县七区捕灭“水鬼毛人”谣言斗争情况的通报》。⑦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长期卷1-2-29。谣言的处置被正式纳入了阶级斗争框架。
据此,7月22日,七区委向县委请示法办几个“反革命坏分子”。但是在这种集体性恐慌和各色乘机活动者中,如何过滤出所谓的“反革命坏分子”?如何处理在恐慌中打伤人或与村民一起“闹毛人”的干部?七区委只好在同一报告中向县委提出请示。⑧《七区委当前谣言情况报告底》 (1953年7月22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七区委永久卷53-1-7。
而谣言的发展“仍异常严重迅速”。到7月24日,郯城全县11个区135个乡“已蔓延九个区,六十八个乡”。①《关于发生“毛人”谣言骚乱情况的专题报告》(1953年7月),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30。其中七区的情况“极为严重”,“全区十二个乡无一幸免”,且全区近一半的村庄干部“进不去庄”。②《七区委关于执行贯彻平息毛人意见》(1953年7月24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七区委永久卷53-1-7。因此,县委又增加了60名下派干部,连同原来下派的35名,共95名干部,组成工作组赴谣言最为严重的七区和九区开展工作。③《关于发生“毛人”谣言骚乱情况的专题报告》(1953年7月),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30。
(二)排队与“捕、斗、管”:层层筛滤的多层过滤网
七区委于7月24日召开干部大会,决定先从能够进去的村入手,进村后“靠上党员干部和基本群众,一面要表明态度一面组织群众生产,组织民兵群众抓毛人、管制地主,广泛的宣传我们的各项政策,解除群众怀疑”。中心的工作一是严格对地主及五方面敌人坏分子的管制工作,二是“将村中的坏分子进行排队,分别对待”。④《七区委关于执行贯彻平息毛人意见》(1953年7月24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七区委永久卷53-1-7。具体作法是“深入的进行回忆对比教育,使群众转变认识,一致对敌——地主反革命”,同时,“将坏人排队收集线索,查对资料,准备有力的打击敌人”。⑤《中共七区委两天谣言情况报告 (23、24号)》(1953年7月26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七区委永久卷53-1-7。于是,“坏人排队”开始。
“坏分子”的标准是1952年由政务院批准、公安部公布的《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所规定的五种“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特务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头子、坚持反动立场之地主分子、坚持反动立场之蒋伪军政官吏。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44页。到7月26日七区委召开各点负责同志会议时,经两天的突击,有了初步成果:“这区装毛人造谣者、破坏者,通过进行站队,现适于五种坏分子之列的 (四个乡,六个村)应该逮捕严办的已有人证物证、十分严重、群众极愤的坏分子共八人。”⑦《中共七区委两天谣言情况报告 (25、26号)》(1953年7月26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七区委永久卷53-1-7。
白天在湖里看瓜时蹲在谷地里装鬼叫的胡木匠 (胡小鬼),乘机造谣吓唬分到自己财产的村民,将其吓跑后重新收回自己土改中被分掉的房产的地主马希奎,“领头闹毛人”的某村主任陈士祥,皆被作为“坏人活动”的典例上报县委。⑧《中共七区委两天谣言情况报告 (23、24号)》(1953年7月26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七区委永久卷53-1-7。
但是,在谣言中乘机偷盗的普通村民如何处理?区委还是心中无数。因此在关于25日、26日的谣言情况报告中,区委特附加了一个补充报告:“在群众惊慌不安的乱‘毛人’谣言中,我区现已发现小偷乘机偷盗群众的玉米。如高头乡与盐店乡发现的较多几个,而其他乡有的也萌芽的发现:这给群众更增加了气愤,对此极为不满,并还很少有捉住的,如果再继续发现,应如何来处理呢?希示之。”⑨《中共七区委两天谣言情况报告 (25、26号)》(1953年7月26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七区委永久卷53-1-7。
七区很快收到地县委“分化孤立打击反革命”的指示,在对地主进行排队和管制的同时,五种人被列为“反革命现行犯”:“(一)装毛人吓唬群众的;(二)打火球打照明弹的;(三)地主反革命分子惯偷乘机进行偷盗抢劫的;(四)放毒放火,破坏群众生产的;(五)武装匪特。”这种归类的针对性和实际操作性已经比较明确。七区委亦开始对具体操作有所领悟,表示要“严厉的镇压反革命,在群众中造成毛人就是地主反革命的舆论,把群众的仇恨迅速转向地主、反革命头上去”。⑩《今后平息谣言毛人骚乱事件意见 (草)》(1953年7月29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七区委永久卷53-1-7。
7月31日,县委形成《关于反“毛人”骚乱斗争今后意见》,决定“严肃打击地主、反革命及反动道会门头子”。作为全县的重点区,七区“共逮了九个毛人”,斗争会在各乡召开,会后则是游街“沿路宣传”,经过各村时村民“齐集路上看毛人”。这些所谓“毛人”除地主外,亦有“装毛人”者,如“引起群众公愤”的胡小鬼即为其中之一。这种“将打击目标转向敌人”,“把毛人转向地主身上”的方式立见成效,一些村庄谣言势头开始趋向缓和,原来下派干部进不去的所谓的“薄弱村”情况也开始出现转机。七区的工作因此得到县委的肯定。①《郯城七区关于平息毛人骚乱的初步总结》(1953年7月30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七区委永久卷53-1-7;《郯城县委关于反“毛人”骚乱斗争今后意见》(1953年7月31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30。县委7月底召开各区书记会议,“介绍了七、九区平息毛人骚乱的典型经验”②《郯城县委关于八月份工作情况综合报告》(1953年8月24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长期卷1-2-35。,并于8月2日向各区发出《关于“毛人”骚乱的通知》,推广七、九区的做法。同时一改原来的克制与谨慎态度,提出“目前不论在已闹或未闹的地区,普遍有策略的召开地主训话会,进行守法和前途教育,号召他们立功赎罪,听到谣言迅速报告,否则以包庇论处”。③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30。“逮毛人”工作在全县各区大张旗鼓地普遍展开。
县委提供的原则性举措包括:(1)首先是对所属区所有“坏分子”尤其是地主排队,分别统计出“倒果实”者、偷盗者、装“毛人”者、骂街者、土地出租者、接迎外人者、拉拢群众者、造谣活动者,等等。(2)对全部地主进行“分别主次”的处理与管制,规定“对现有闹‘毛人’活动的事实,过去有较大的罪恶,应逮捕法办,依国法制裁;对以前镇反被管制的,现在又造谣破坏,应进行斗争后严加管制,但要管死 (即是黑、白不许出门,但不能占多数);一般的也要进行管制,但要管而不死 (允许下湖生产)。三不准:不准赶集、不准走亲戚、不准接近群众,民兵要定期检查”。(3)对于“一般群众”, “群众被地主操纵进行破坏的一般的要教育批评警告,同时还可发动让他检讨、反省,对群众一般性的传谣主要的进行教育”,以达“争取群众,孤立坏分子”之目的。(4)对于民兵和干部,恐慌者被定性为“对敌人认识不足”,“思想被敌人俘虏”,一般多进行教育和挽救,少数“带头闹毛人”者则作为“不纯分子”被“清除出革命队伍”。④《郯城县委关于反“毛人”骚乱斗争今后意见》(1953年7月31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30。如前面提到的“带头造谣”的村主任陈士祥,“以谣言吓唬看瓜的群众杨生清,夜间集伙五个民兵偷瓜吃”的民兵马保坤,以及乱打枪并“吆呼毛人来了”造成群众恐慌的民兵李兆银⑤《我区谣言传播情况》(1953年7月23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塂上区委永久卷57-1-2。,等等,皆被清理。在此基础上,组织各村民兵站岗放哨。
但是,如前所言,谣言的恐慌者与乘机活动者皆包含了各个阶层人群。七区捕抓的14人中,地主5人,富农1人,复杂成分8人。⑥《郯七区委当前平息毛人骚乱情况及今后工作报告》(1953年8月7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七区委永久卷53-1-7。四区通过排队抓出的“趁机破坏造谣的和乘机偷盗的及思想不纯被俘虏的”共13户,即包括了“地主五户,富农一人,贫农二个,中农五人”。⑦《郯城四区委关于一月来反毛人骚乱斗争的情况和秋季农业生产情况的综合报告》(1953年8月19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四区委永久卷55-1-1。那么,如何使群众“明确认识‘毛人’是地主、反革命装的”,做到使群众把“反‘毛人’骚乱的目标完全转向地主、反革命”,“把‘毛人’帽子按到反革命、地主阶级头上,将群众的愤恨转移到敌人的身上”?⑧《郯城县委关于反“毛人”骚乱斗争今后意见》(1953年7月31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30。相关举措体现着两个特征:
其一,对于谣言中发生的“恐慌”和“乘机活动”,要在排队中“追根求源”,“均找到地主反革命身上”。为了使各区的“逮毛人”行动有所参照,8月8日,郯城县委发出《对地主反革命装“毛人”吓唬群众,进行反攻复辟活动的几个具体实例的通报》。在这些实例中,前面所述七区上报县委的典型材料中提到的,造谣吓唬村民以收回自己土改中被分掉房产的地主马希奎,毫无疑问名列其中。而装鬼叫的胡小鬼虽系贫农成分,但“系地主爪牙一贯被地主利用”,其行为被定性为“反革命直接破坏生产的表现”。八区用草人吓唬群众的李记学,虽然亦是贫农成分,但被定性为“因包庇地主、反革命被地主利用”的反革命分子。①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30。
其二,排队之后“捕、斗、管”的对象有明确目标锁定。如七区规定:“必须严格限制在不法地主及反革命分子身上,必须是既有历史罪恶又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分子。”“对个别有罪恶的还应呈报批准再捕,但应限制在现行反革命及极不法的地主”,而对其他“复杂成分的分子”则要求“不要乱斗一气”,群众中的小偷等“主要是令其检讨悔过甚至付还偷到的东西”。②《郯七区委当前平息毛人骚乱情况及今后工作报告》(1953年8月7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七区委永久卷53-1-7。十区则提出:“在斗争对象的确定上,必须是地主成份或富农成份,再就是斗争的对象必须是从毛人的谣言斗起,否则打的不准、不狠,地主就不会老实,对群众教育意义也不大。”③《十区委对反毛人斗争骚乱善后工作及当前秋季生产与结合工作进行情况报告》 (1953年8月24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十区委永久卷65-1-3。
因此,排队与“捕、斗、管”,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过滤网,通过层层筛滤,最后剩下的自然就是“毛人=反革命”。
(三)镇反补课:高潮之后的高潮
这种集中力量对准“地主与反革命分子”的方式的确颇见成效。据七区的总结:“哪乡哪庄对地主反革命分子管的严打的狠,坏根挖的净,那里就平息的快,群众情绪就安稳,干部群众的斗争劲头就大,觉悟提高的就快,对毛人骚乱打垮的就快,群众的生产情绪就会高起来,劲头就大。”④《七区委当前工作报告》(1953年8月11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七区委永久卷53-1-7。谣言虽然到8月上旬已经先后蔓延全县111个乡 (占总数的81.7%),462个村 (占总数的58.9%)⑤《郯城县委关于八月份工作情况综合报告》(1953年8月24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长期卷1-2-35。,但到1953年8月11日,“全县范围内已基本平息”。这时,县委发布《关于“毛人”骚乱中被镇压的地富反革命和过去镇反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提出“要结合解决过去镇压中遗留的问题”,“对已捕已被管制的分子有分别地进行适当处理或严格管制”。⑥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30。因此,谣言平息之后,对“反革命分子”的管制与捕斗不但未因此而止,反而形成新的高潮。
县委通告各区:“过去镇反不彻底地区,应趁此机会,补上这一课,即是过去有血债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反动道会门头子,群众甚为愤恨,这次斗争又暴露出来的,严重的即应整理相关材料,上报批准后逮捕之。”要“大力发动群众坚决的向地主阶级进行猛烈斗争,把反动地主气焰打下去,该捕的捕,该斗的斗,该管的管”。⑦《郯城县关于当前秋季生产与结合继续贯彻反毛人骚乱斗争的通知》(1953年8月中旬),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长期卷1-2-34。于此过程中,斗争的对象已经不限于“闹毛人”的“反革命分子”,而是全部的“不法地主与反革命分子”;没有“把群众痛恨转向地主阶级”,“抛开了向阶级敌人进行斗争而单纯追谣言”,皆被视为“‘毛人’骚乱平息无力”问题。⑧《郯城县关于当前秋季生产与结合继续贯彻反毛人骚乱斗争的通知》(1953年8月中旬),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长期卷1-2-34。
此时,各区对所谓“捕、斗、管”等斗争方式已经基本上驾轻就熟。在七区,“向不法地主与反革命分子开展了急烈的斗争”,共捕15人,斗争地主反动富农90余人,其余大都被管制。⑨《七区委关于当前秋季生产与结合处理毛人骚乱斗争工作意见》(1953年8月17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七区委永久卷53-1-7。在十区,共有地主118户,除4户军属地主外,“其余全部管制,不分对象”。⑩《十区委对反毛人斗争骚乱善后工作及当前秋季生产与结合工作进行情况报告》 (1953年8月24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十区委永久卷65-1-3。各个村庄纷纷展开了“整地主”的斗争,“各庄地主富农坏分子都被整苦了”。⑪笔者在山东省郯城县高峰头镇解庄村 (当时属郯七区)采访徐祇华的记录 (2009年1月7日)。徐祇华,男,1940年生,当时为中农成分。虽然有的村“整了十几天地主,也没整出来,没有地主交待装‘毛人’的事”。⑫笔者在山东省郯城县高峰头镇后高峰头村 (当时属郯七区)采访徐勤福的记录 (2009年1月8日)。徐勤福,男,1923年生,当时为贫农成分。但这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此时的“逮毛人”已经与“镇反补课”交叠在一起,“逮毛人”已成为“补上镇反这一课的机会”,甚至已经转换为“镇反补课”。
由于郯城地处苏鲁交界区,加之中共革命于当地的长期拉锯,如以中共的政治标准考量,本地民众与外来人口的个人历史与成分构成皆极为复杂。如郯城四区归昌乡,曾为郯城第三次解放后土改最红火的地区,亦是此后国民党反攻时被还乡团报复得最为厉害的地区 (全县被活埋250人,近半为此地发生),但该乡参加会道门者也是几乎占全乡户数的40%以上。①《关于郯城县“水鬼毛人”谣言又次发生情况的报告》(1953年12月下旬),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30。若追根揭底,各乡村可能几乎无人“根正苗红”。于此背景下的“捕、斗、管”渐趋激烈化,有的村连“干过几天甲长说过破坏话的都管制了”②《一区委对反毛人斗争与当前秋耕进度和秋种准备及夏征工作情况报告》 (1953年8月26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一区委李庄公社永久卷51-1-1。,有些村“逢斗必打,逢训话必打”③《郯城县委关于八月份工作情况综合报告》(1953年8月24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长期卷1-2-35。,有的村抓住小偷就“偷什么挂什么游街”,男女作风不好的被抓住也“挂着破鞋游街”④笔者在山东省郯城县高峰头镇店子村采访吴士奎的记录 (2009年1月11日)。吴士奎,男,1938年生,老家当时属郯城县码头区,为贫农成分。。七区某村一个妇女,“平时好骂人”,亦被捆到村南榆林里批斗。⑤笔者在山东省郯城县高峰头镇后高峰头村 (当时属郯七区)采访徐希涛的记录 (2009年1月6日)。徐希涛,男,1934年生,当时为贫农成分。
当8月底这场“反毛人骚乱斗争”彻底收尾和各地转入秋收生产,相关的斗争过程也完成了“毛人就是地主,地主就是毛人,毛人与地主反革命分子是分不开的”的逻辑表达。⑥《四区委对最近几天的情况检查简报》(1953年8月5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四区委永久卷55-1-1。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这一逻辑中,是“反革命制造了毛人”,还是“毛人制造了反革命”?问题已俨然“鸡生蛋”与“蛋生鸡”的轮转循环。
四、有效—无力:欲静难止的革命与去而又来的“毛人”
概而言之,谣言的本质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1953年“毛人”谣言于山东省郯城县的传入与传播,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革命政权建设轨迹与当地乡村百姓心理感受的“共鸣”。正因如此,谣言的“恐慌者”和“乘机活动者”体现了“全民性”和“集体性”的特征,皆包含了乡村社会所有阶层人群。谣言的矛头指向中共干部,显示了乡村基层政权初建时遭遇的尴尬。由学术视角回顾政府平息这一谣言的纵向过程:
一方面,必须肯定,政府的相关举措有效控制和平息了谣言,巩固和夯实了新生政权的乡村基础。1953年“毛人”谣言事件中的所谓“毛人”,本是“不存在的敌人”。刚刚取得革命胜利的新生政权,将斗争矛头集中和指向于乘机活动者中的“社会变革的受冲击者”,即新政权的敌对力量,将“不存在的敌人”具体化,如此一来使相关处置措施更具有可操作性。对“反革命分子”的“捕、斗、管”,亦对各类所谓的“坏分子”造成威慑之势,从而形成对整个社会的新一轮整肃。同时,中共的下派干部进村后积极组织民兵站岗放哨等,客观上也限制了各类“坏分子”的乘机活动,从而给百姓带来一种安全感与稳定感。这些工作无疑都有效控制了谣言的传播,此亦成为乡村社会接纳与认可新生政权的重要过程。
自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之后不久,郯城县的镇反即全面展开,到1953年“毛人”谣言发生时,当地已经进行了两期镇反。平息“毛人”谣言的过程与“镇反补课”的交叠,又成为新生政权将乡村诸类问题皆纳入阶级斗争框架内处理的工作技术进入乡村的过程。在革命理念之下的阶级斗争大潮中,新生政权对乡村的控制力进一步增强,在谣言的迅速平息中,各类“坏分子”迅即被荡涤殆尽,革命的威势再次彰显其有效性。
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在谣言的本质逻辑面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处置方式亦有其无力之处。郯城县各区乡村“毛人”谣言发展与平息的过程,虽时间先后稍有不同,但许多村庄皆呈现如下规律:当“捕、斗、管”较为严厉时,谣言即平息,一旦“有放松麻痹思想”,则谣言又起。①《郯城县委关于八月份工作情况综合报告》(1953年8月24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长期卷1-2-35。于是,县委再派工作组前往平息,如此数次方可。
1953年8月下旬郯城县委“毛人”谣言平息工作收尾之后,9月22日,郯城一区上报县委,当地谣言再起,各村谣传“八月十五没有太阳,毛人完成任务,毛人下来了”等等,部分村庄再次陷入恐慌,又开始集体睡觉。干部查问时则借口说是“在外面凉快”或说是为了“看花生”。②《一区委关于抗旱工作情况报告》 (1953年9月22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一区委李庄公社永久卷51-1-1。9月23日,三区委报告,当地谣言亦起,并有“闹神水”在多村发生,许多妇女跑去一个小庙取“神水”治病防病。③郯城县档案馆藏,塂上区委永久卷57-1-2。
到1953年12月,郯城县“毛人”谣言成规模地再起,再次“蔓延全县大部乡村”。④《郯城县政府关于1953年工作总结报告》(1954年1月5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县政府永久卷11-1-12。最值得玩味的是,曾经被县委推为典型的七区再次成为谣言重灾区。⑤《关于郯城县“水鬼毛人”谣言又次发生情况的报告》(1953年12月下旬),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30。谣言的内容有“毛人又来了”,“又有毛人了”,“某某村看见火球或黑影”,等等,实际与夏天如出一辙。此次谣言一般多是“暗传”,百姓多如对暗号一般谈论,如“现在传说都是那东西又来了,现在哪里又有了”,有人抢购电池别人问起时则答:“现在不是那个东西又来了吗”?⑥《七区委红花乡、问庄乡近几天谣言情况简报》(1953年12月14日),郯城县档案馆藏,七区委永久卷53-1-7。
于是,又一轮的“捕、斗、管”再次开始。
在夏天的谣言中,全县共逮捕60人。⑦《关于郯城县平息地主、反革命制造“毛人”骚动事件的报告》(1953年8月4日),郯城县档案馆藏,县委永久卷1-1-30。实际上,由于新政权社会控制能力的增强,此次谣言的规模远远小于夏天。12月初再起,25日即已平息。但全县逮捕的“毛人谣言犯”竟达113人。⑧李若建在其研究中即引用的这一数字,但据笔者的查阅,此数字当为12月份谣言的数字,而非夏天与此次加起来的数字。参见《郯城县志》,第24页。加上夏天的60人,共约173人。郯城县的第三期镇反时间为1952年11月1日至1955年3月31日,全县共逮捕各类“反革命分子”300人。在1953年平息“毛人”谣言中逮捕的人数占了一多半。⑨《郯城县政权志》,第104页。联系整个“毛人”事件的平息过程,此数字确实意味深长。基于此,革命的胜利虽大局已定,但树欲静而风难止。在这种“鸡生蛋”与“蛋生鸡”的轮转循环中,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谣言纳入意识形态框架内处理的有效性与无力处并存共生。在其历史延续中,革命惯性下的阶级斗争思维与工作模式逐渐被套牢于各类问题的处置而难以刹车。于是,每当政府置身于社会事件的处置,往往便是:阶级斗争了无休止,阶级敌人层出不穷。在曾经的历史中,这一逻辑的呈现,于大政府,于小乡村,皆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