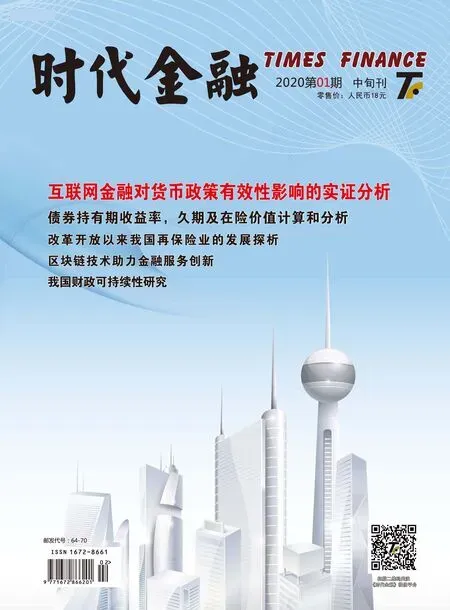危险犯的停止形态研究
温雅璐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危险犯的停止形态研究
温雅璐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刑法中的故意犯罪停止形态,是指在犯罪过程当中,行为由于某种原因停顿下来完成犯罪的一种状态,主要表现为犯罪既遂、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危险犯以危险状态出现与否作为既遂状态的标准,其也存在既遂、未遂两种停止形态。同时,危险犯还可转向实害犯,并成立实害犯的中止。
故意犯罪停止形态 危险犯 未遂 中止
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按其行为最后停顿时犯罪行为是否完成为标准,可分为两种类型:(1)犯罪的完成形态,即犯罪的既遂形态,是指故意犯罪在其发展过程中进行到底、行为人的行为已经完全符合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某一具体犯罪构成的全部构成要件的情形;(2)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即故意犯罪在其发展过程之中由于主观、客观方面的原因停止下来,行为人没有达到某一具体犯罪过程的全部构成要件的情形,主要为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三种形态。这三种形态有其相同点。但在未完成原因(意志内外的原因)、停顿时间(预备阶段、实行阶段、实行后阶段)及行为人主观恶性等方面,又有着本质的区别。
危险犯,相对于实害犯而言,指以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足以造成某种法定的公共危险。我国刑法通常将一些危害公共安全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危险状态直接规定在分则之中,并设置相应的法定刑,与实害犯相区分。但由于危险犯是以危险状态的出现为基础的特殊犯罪类型,其停止停止形态的认定一直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危险犯有无未遂之分,如果有又该以何标准来区分;危险状态出现后是否存在犯罪中止,若肯定则应属于那种犯罪中止等等。笔者将结合理论界的主要几种学说进行探究,以求得到较为清晰的解释。
一、危险犯的未遂状态之辨
关于危险犯是否存在未遂状态,我国刑法学界主要存在否定说、肯定说和折中说几种学说:
一是危险犯既遂说。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危险犯不可能存在未遂状态是因为危险犯以危险状态的出现为认定标准,也以此为犯罪构成要件。以此为基础,危险犯的成立和既遂实质成了同一个概念。[1]还有持法定既遂说的学者认为,危险犯实质就是实害犯的未遂犯,只因危险状态的出现危害到了公共安全或社会秩序,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而被法律拟制成为一类犯罪。既然是法定的独立既遂犯,自然没有未遂的余地。[2]
二是危险犯未遂说。此学说认为“刑法分则规定的危险犯,实际上是犯罪未遂”,无既遂可言。因为未遂的“未得逞”,就是指未达到行为人预期的犯罪目的。而在危险犯中,行为人的目的绝不仅仅是造成某种危险,而是为了追求某种危害结果。仅仅出现危险时,实质上是未得逞,即未遂。[3]
三是折中说。该学说认为危险犯既有未遂形态,也有既遂形态,危险犯的成立与既遂应该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拥有两个不同的标准。从成立到既遂的时间段内,当然存在未遂的情况。因此,危险犯有既遂与未遂之分。[4]还有学者认为只有部分危险犯存在未遂形态,但对危险犯的范围有分歧。第一种观点认为,具体危险犯才存在犯罪未遂,而抽象危险犯没有未遂形态。具体危险犯以发生一定的危险为要件,当行为人已着手却因意志外原因未发生法定的危险状态时,成立具体危险犯犯罪未遂。而抽象危险犯不以发生现实的危险状态为必要,通常不认为有未遂状态。[5]还有一种观点正好相反。具体危险犯很难存在可罚性的未遂,而抽象危险犯在原则上就改承认未遂形态的可能。假如构成要件行为并不至于形成具体危险,则不但不会形成犯罪,甚至不会形成未遂犯。[6]
上述观点中,前两种观点实质都否定了危险犯未遂状态的存在,笔者认为都不可取。既遂说第一种说法把危险状态或侵害法益的危险的出现作为危险犯成立的构成要件,又视为犯罪既遂的标准,混淆了成立与既遂的标准。按照我国刑法规定,成立犯罪是指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此为刑法总则规定的修正的犯罪构成要件;而成立犯罪既遂则是符合刑法分则中具体每个罪名的一般构成要件。危险状态的出现符合刑法分则对危险犯一般构成要件的要求,是危险犯既遂的标准。因此,法定危险状态即使尚未出现,仍然可以成立危险犯,只不过会成立危险犯的停止形态。
既遂说的第二种观点“法定既遂说”和“危险犯未遂说”立论基础基本相同,即认为危险犯是实害犯的未遂犯,因此也存在相应的缺陷。“法定既遂说”看到了危险犯的独立性这一点值得肯定,而未遂说不仅将未遂犯当作实害犯的一部分,还以犯罪目的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准并得出危险犯只能是未遂犯的结论,与学界公认的以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为既遂的标准理论相违背。
应当肯定,折中说具有一定合理性,也即是说危险犯不仅有犯罪完成形态,也有犯罪未完成形态。但认为具体危险犯或抽象危险犯只有一种存在未遂状态的说法是片面的。无论是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都有相同的理论结构和基础,都立足于对法益的侵害方式区别与实害犯的角度而言的,危险犯对于法益的侵害只是一种现实损害的可能性。在法益侵害可能性的角度上来看,二者并无构成基础上之区别。危险的发生都依赖客观的判断,只不过对危险犯的危险状态的判断不仅满足于构成要件行为的完成,还有待于危险状态的时间点判断,而抽象危险犯的危险判断已有了立法者进行拟制,拟制的依据就是类型化的行为方式。[7]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危险犯作为与实害犯相对应的独立犯罪,存在完成的既遂状态,也存在未完成的既遂状态,而非实害犯的未遂。
但犯罪过程中的危险状态和实害状态是一种发展并渐进的现象,危险状态出现后还可能存在继续发展成为实害犯的可能。所以,在这一过程中,行为人也有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而产生停顿,这便有了危险状态下停止形态的认定问题。
二、危险犯停止状态的认定
在危险状态出现前,由于行为人意志内、外的原因而停顿的,可能存在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危险犯的既遂,则应以“公共危险”的危险状态出现,并在犯罪过程中已经停顿作为标准。在危险状态出现后,由于各种行为人意志外客观原因产生停顿的,成立危险犯既遂;若是出现了实害结果,则转化为实害犯既遂。但刑法理论界对于犯罪人在危险状态出现后自动放弃犯罪或有效的阻止法定犯罪结果的出现该如何认定的存在较大分歧。此种情况应定犯罪既遂还是犯罪中止;若是以犯罪中止论,那是什么罪的犯罪中止这两大问题众说纷纭。
(一)犯罪中止与否的认定
1.否定说,即“犯罪既遂说”。法定的危险状态出现以后,即出现既遂状态,既遂后不存在犯罪中止。首先,这种既遂后的中止违背停止形态独立原则。其次,危险状态的出现即表示此类危险犯罪的完成形态,犯罪过程已结束,不符合中止的时间性条件。再次,危险犯的完成无实际的危害结果,“防止犯罪结果的出现”针对的是结果犯而言,也不符合中止的有效性条件。这些都会使犯罪中止的统一概念和原理遭到破坏。况且,对于自动防卫危害结果的危险犯,虽不作中止认定,但可将此行为做量刑从宽情节考虑,从而不影响罪行相适应原则的贯彻,[8]并有利于犯罪分子悔罪。
2.肯定说,即“犯罪中止”说。有观点认为,危险状态的发生并非就是犯罪既遂,只有犯罪结果的发生才是犯罪既遂(认为“犯罪结果”是危险犯既遂的标准),在此之前行为人放弃犯罪或有效组织法定犯罪结果的发生属于犯罪中止。以“危险状态出现”作为危险犯既遂标准的学者认为,犯罪中止只能出现在犯罪结果出现前而非既遂前,危险状态出现后仍然可以成立犯罪中止。还有观点认为,应借鉴“放弃重复侵害行为”的犯罪中止论的法理,将此种情况定位危险犯的犯罪未遂。虽在既遂后定为中止与犯罪停止形态的排他性原则相违背,但这有利于犯罪分子及时悔悟,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所以,应当作为一种特殊情况来对待。
应当肯定“否定说”中关于犯罪既遂后即不存在中止的观点,这符合我国刑法理论中停止形态排他性的原理。但是犯罪停止形态是以最后的停顿点为标志作为标准的。危害状态的出现从广义来看实质是在出现危害结果前的一个阶段过程,如前文所说,危险状态出现后犯罪状态还可能朝着犯罪危害结果发展,即存在着危险状态向实害状态发展的可能。所以,在危害结果出现后的停顿,不应视为一种既遂的标志,而应作为一种排除未遂的情形对待,具体定何种行为,还应视行为人的主观意愿而定。此时行为人若出于主观意愿而停顿,应视为从行为人开始预备行为至犯罪结果出现整个大犯罪过程中的中止停顿,即危险状态出现后依然存在中止的可能。
“犯罪中止说”也承认中止的存在,但笔者认为持“犯罪结果”为危险犯既遂标准的学者论证观点基础本身就值得商榷,这一理由应当不被认可。而危险状态出现后的自动防卫结果发生情况与“放弃重复侵害”不同,“放弃重复侵害”必须是第一个行为没有引起结果发生从而存在实施第二个重复侵害行为的可能情况下行为人放弃侵害,前后行为具有统一性。而危险状态出现后,危险犯行为已经完成,不需在实施同一行为危害结果也可能会发生,这一理由同样不够充分。
相较而言,笔者较偏向于“犯罪中止说”,危险状态出现后依然存在中止的可能性。但论证理由则与其有不一样的观点。笔者认为,危险状态后出现犯罪中止完全不违背犯罪既遂后不存在中止的原理。按照刘宪权老师的观点,这是危险状态出现后排除未遂情况下的一种停止形态,与“犯罪既遂后不存在犯罪中止形态”并未是同一层面的问题。当危险状态出现后,行为人的行为实质上还处在不确定的状态,即处在可能向实害犯转化的状态。若因客观原因停顿,如前文论述,应构成危险犯的既遂;若保持这种状态向实害状态发展下去,则构成实害犯既遂。若在转化过程中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或有效的阻止法定犯罪结果的发生,符合犯罪中止时间性、自动性、有效性三个特征,完全合乎法理,应以实害犯的犯罪中止定。
同时,定犯罪中止也十分必要。从形势政策角度看,定犯罪中止有助于鼓励行为人主动阻止结果出现的行为,这一法律的指示作用会对行为人产生积极的影响,充分发挥刑法设置犯罪中止这一“回归的黄金大桥”的积极作用;定犯罪既遂则有失罪刑相适应的平衡,犯罪人中止即表明其主观恶性的减小,定犯罪中止,更有利于保证法律的公正性,并从法律上保障了行为人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量刑情节。
(二)实害犯的犯罪中止
危险状态后的不仅存在中止形态,而且应该定实害犯的犯罪中止。关于这一界定,有学者认为应该定危险犯的犯罪中止,主要理由是:危险状态出现后并不等于犯罪既遂,在既遂前出现犯罪中止是完全有可能的,自然也就认为是危险犯的犯罪中止。[9]关于这一观点,前文已对其进行了辨正。从时间上来看,危险状态出现后,虽然有继续向实害状态转化的可能,但相对于危险犯来说,其法定的犯罪过程已经完结,不可能存在危险犯的中止形态。而相对于实害犯来说,其犯罪过程因还存在继续向前发展的可能,在犯罪结果出现前整个犯罪过程并不会结束,自然也就存在包括中止在内的停止形态。所以,应成立与危险犯相对应的实害犯的犯罪中止。
从中止第二特征—有效性要求出发,也只能定实害犯的犯罪中止。若是定危险犯犯罪中止,则不符合有关“有效阻止法定犯罪结果发生”这一最重要的条件。尽管在危险犯和实害犯共存的犯罪中,危险状态可能向犯罪结果发生转化,但刑法以明文规定将危险状态作为危险犯的犯罪法定后果,一旦危险状态发生,很难想像危险犯行为人如何阻止危险状态——这一法定的犯罪后果的发生,这一说法本身存在矛盾。而定实害犯的犯罪中止则可有效解决上述矛盾。在危险状态出现后向实害状态转化的这一过程,表明危险犯犯罪过程已结束,实害犯犯罪过程仍在进行,即实害犯法定的危害结果有出现的可能性但现实中却还未出现,此时行为人自动放弃犯罪或有效的阻止实害犯罪结果的出现,并不会影响危险犯的犯罪形态,但却可以成立实害犯的犯罪中止。同时,从量刑上看,将实际出现的危害状态视为实害犯中止所造成的损害,考虑了“危害状态结果”存在的因素,又考虑了行为人自动停止或有效阻止“实害结果”的因素,并对其适用“应当减轻”的法定情节也更合理。
[1]杨兴培.危险犯质疑[J].中国法学,2000(3).
[2]陈兴良.陈兴良刑法学教科书之规范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26.
[3]侯国云.刑法学[J].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184.
[4]张明楷.危险犯初探[J].马俊驹主编:清华法律评论(第一辑),1998.
[5]赵秉志.犯罪总论问题探索[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06,407.
[6]林山田.评刑法修正案草案[J].刑事法从论(2).
[7]高巍.论危险犯的未遂[J].法学评论,2010(1):116.
[8]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二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359,361.
[9]吴炳新.危险犯的停止形态研究[J].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3(2):46.
温雅璐(1985-),女,江西吉安人,华东政法大学2012级刑法学方向法学研究生,研究方向:青少年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