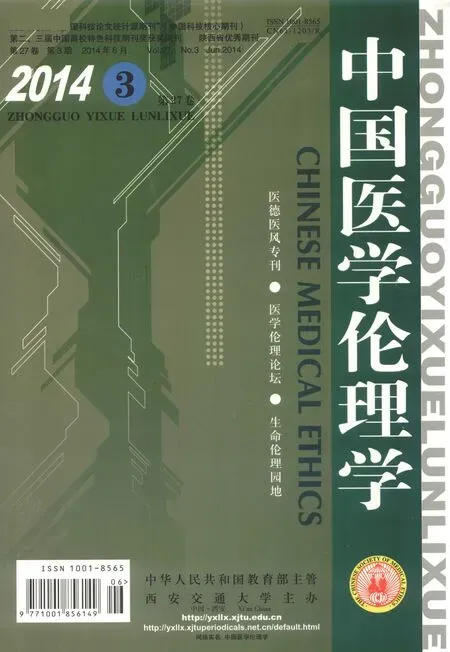传统儒家德性伦理对当前“医德”文化建设的启示
陈 默
(桂林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chenmokkk@163.com)
医德建设
传统儒家德性伦理对当前“医德”文化建设的启示
陈 默
(桂林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chenmokkk@163.com)
医德作为一种职业道德是传统儒家道德伦理在医学方面的体现,儒家德性伦理中的“五德”即仁、义、礼、智、信的内在精髓对于现代医德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同时也对当前医德文化建设提供借鉴,为公民的安全和利益提供保障。
儒家德性伦理;医德文化;仁;义;礼;智;信
传统儒家德性伦理中的“五德”——仁、义、礼、智、信是医学道德的发端,蕴含在其中的内在精神经历了历史和实践的考验。本文结合现代社会实际,分别谈谈它们对现代医德文化建设的启示。
1 对人生命关爱的内在之“仁”
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仁”是具有普遍价值的伦理原则。仁是什么?孔子这样解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孟子也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可见,在传统儒家看来,仁主要体现为爱人之心或同情心。在医学中,爱人之心和同情心是医者施展医术救人的首要前提,如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在其《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说道:“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医生应该以救人性命为首要目的,因为人的性命是千金难换的。对人性命的内在之“仁”是从事医生这门职业的首要的必备德性。
在现代,“仁”的精神运用到医疗事务中,首先表现在对人生命的尊重。随着科学的进步,医疗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但衡量现代科学技术价值的标准不仅仅是技术本身,更要看现代医疗技术是否从本质上维护或推进了人的生命价值。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提出,“医学现代化的一个必要的标志就是看:医学活动本身是否具有对生命的终极关怀的精神体现。技术只有在这样的境界下才具有意义和价值。”[1]生命是人类最珍贵的东西,对于任何人来说只有一次,因此,挽救人的生命是一件非常高尚、有意义的事情,如古人所说:“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也。医者赞天地之生者也”(张介宾,类经图翼)。因此,医生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件赋予人以恩德的事情。在现代社会,医学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解除病痛的技术层面上,更应该体现在抚慰和减轻患者精神痛苦的人文关怀之中;医学的功能不仅包含着对生命现象、生命过程的认识和研究,更包含了对生命的整体解读和对生命质量的关注等更多的人文内涵。因此,基于生命维度的认知和理解,需要爱心作为支撑起生命复杂内涵和平衡生命本体之痛的力量。”[2]
其次,仁的原则在处理医患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医患关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医生的职业态度和道德修养,因为在众多的医患关系模式中,虽然主动被动型医患关系模式自近代以来备受批判,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医生由于掌握诊疗技术,以及诊疗过程中医生必须拥有和发挥的主导权利,使得医生在大多数情况下主宰着病人的生死。因此,拥有良好的医德和仁爱、仁慈之心是医务人员和患者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基础。医务人员只有切实地站在病人的立场去想问题,才能真正体会到病人的真实处境,激发出自身内在的仁爱之心与同情心。在工作中,医务人员不把自己与病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求与被求的关系,而是设身处地地为他人排忧解难,将救死扶伤当成自己的基本职责,才能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再次,在工作中坚持仁的原则,更能激发从医者不断探索医学真理,完善自身医术和医技的向往和追求。因为生命是神圣的,只有抱有仁爱之心,才能不亵渎人的生命,在行医的过程中谨慎处理,不武断、轻率,不计较个人得失,全心全意地与病人一起战胜疾病的威胁。
2 医生和病人之间取得平衡之“义”
“义”是传统儒家提出的又一个重要德性。在孔子那里,“义”是纯粹的个体德性,如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义是内在的道德,礼是外在的道德规范。到孟子那里,义的含义发生了改变,逐渐向礼靠近,如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义成为行为的原则或规范。荀子之“义”又有了很大的改变,义不仅是个体行为的准则,而且是维护群体秩序的群体规范,如他说:“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荀子·王制)。“群”与“分”最终要通过“义”来实现,“故义以分则和”(荀子·王制)。
无论“义”的含义如何发生变化,其作用都是用来抗衡“利”。义利关系自古以来都是思想家们所探讨的热点话题。在传统儒家,一直坚持道义论,从孔孟开始,重义轻利一直是传统儒家在义利关系问题上的基调。尽管在《礼记·中庸》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义者,宜也”,也就是将“义”当作公正、合适处事的方法。但是,总体来说,在传统儒家看来,如果“义”、“利”之间发生冲突,必须坚持把“义”放在第一位。传统儒家的这一以“义”为先的价值观也直接贯穿到了传统医学伦理学中,医生行医必须坚持把病人的生命和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谋取自己的利益。但医学发展到现代社会,尤其是医疗服务商业化以来,坚持道义论已经不再符合社会的现实。在现代医学伦理学中,我们讲究的是既要维护病人的权利,也要维护医生的权利。因此,“义”体现为在医生和病人之间取得相互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因此,治病救人就不仅仅需要考虑当前的医疗技术和水平,还要综合考虑患者的情况与医疗机构自身的处境以及医务人员本身所处的位置。义的原则在医务人员实际工作的运用中就体现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作出最好的治疗对策。那种完全遵照义务论办事的工作态度是非常消极的,但是完全从谋取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也是不可行的。“义”便是在工作中遵循功利与义务相平衡的正义原则。
3 遵守规范强调法规之“礼”
“礼”是传统儒家所重视的第三种德性。礼的内涵非常丰富,在传统儒家看来,任何事都有属于这件事的礼,凡事都得按照礼的规范来办,如婚礼、乐礼、葬礼、祭礼等等,这一点在《礼记》里面详细地阐述过。通常认为,礼在传统儒家思想里代表外在的道德规范,与德性没有太多关系,但实际上,传统儒家所论及的德性修养一刻也离不开“礼”之规范,“礼在德性完善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按照礼修养自己的品行是成就德性的基础。”[3]
对于现代的医务工作人员来说,具备法的精神就体现在熟悉掌握国家的法律法规,了解本行业的规章制度等,力求在工作中严格地按国家法律与相关规章制度办事。随着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提高与人们医疗卫生知识的普及,患者在治病的时候具备更强的自主性,更懂得怎样维护自身的权益。作为现代的医务工作者,更应该熟悉掌握国家的法律法规,尊重患者的权利,避免在工作中造成不必要的医疗过失,承担自身无法承受或没必要承担的经济赔偿。随着国家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规范各行各业职业行为的法律、法规也相继出台,如果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忽视了工作中的法律因素,不重视患者的权利,就很容易产生冲突与矛盾,同时也影响到医务人员与医疗结构自身的权益。因此,传统儒家礼的德性在现代医务人员工作的具体运用中,就体现为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只有依照国家有关的法律政策行事,尊重患者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才能保证在从医的过程中不违反法律规定。
4 运筹帷幄处事能力之“智”
在传统儒家“五德”之中,“智”是最具实践性的德性。什么是智呢?孔子这样解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论语·颜渊)。在儒家看来,智是唯一能够与仁并列放在一起的德性。如孔子说:“仁者安仁,智者利仁”(论语·里仁),在这里,孔子明显提出智对仁具有辅助作用。在另一处,他又说道:“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在孟子那里,具备智德的人应该是善于反思、灵活应变的人。如他说:“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也。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孟子·离娄下)。在另一处,他又说:“智,譬则巧也”(孟子·万章下)。因此,智不仅是通过学习就可以掌握的知识或方法,而且是一种在实践中能够灵活运用、不断反思与革新的智慧,总体上说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充分体现。
可见,“智”不仅仅是一种德性,更是一种能力,是一种能够运筹帷幄的处事能力。在医务人员的工作中,具备这种德性才能应付医疗中的各种紧急情况。在传统的医疗模式中,更容易从自然属性上去探索人类的疾病与健康,而往往忽视了医学所应该具备的社会性。“在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医学模式中,任何科学知识、观念和技术都是无国界的、超民族和历史的。而对于人们所处的地域、民族、风俗人情等文化背景,以及在医疗活动中围绕着疾病而展开的人与人之间的认知与情感,注意较少”。[4]而在现实医疗过程中,往往受到患者所处的文化层次、家庭背景、地域民族、道德观念、价值评价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医务人员在治病救人的过程中治疗的不仅仅是人的生理生命,更要懂得如何掌握病人的心理,通过充分地了解病人的文化层次、职业、宗教信仰等等来综合治疗,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5 医患双方信任之“信”
“信”即诚实守信,不欺骗。孔子认为,做人就应该“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那就是说话必须诚实守信,做事必须有始有终。在另一处,他又强调:“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可见,信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根本,没有信,人在这个社会上寸步难行。
当前,信任危机已成为现代医患关系中的重要问题,首先是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医患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信息的不对称性是医疗领域存在的固有属性,医务人员的专业权威、职业权威常常造成患者对其绝对的依赖性,而这种权力分配方面的绝对优势也是造成医疗权力的滥用等医疗腐败现象的主要原因。“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是其择医的基础。一个医生或者医疗机构要得到群众的好口碑,除了要拥有先进的医疗器械和过硬的医疗技术,还要有一颗真诚为病人服务和负责的心。”[5]
其次,由于医患关系处理不得当而引发的血案频频发生,使得医务人员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生命安全,这反映了医方对患者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被延续着,医方担心医疗意外不被理解、欠费无法追讨、闹事伤人时有发生,于是出现将告知的不良预后尽量放大、检查项目尽量做全、用药尽量听患者要求的现象,以规避客观存在的医疗风险;患方担心医者的诊治水平、自己被重视的程度、费用支出的多少,于是出现利用各种关系提高信任程度、通过利益给予增加安全感、运用吵闹甚至威胁方式争取公平与实惠、排斥实习和进修医生的现象。失去信任的医患关系,瓦解着医患共同体,使双方都受到伤害。”[6]
可见,信任是双方的,“在现代相对松散的社会关系条件下,信任主体在道德上承担的义务不再是必需的,信任主体既可以选择信任对方,也可以选择不信任对方,信任主体主要依赖利益需求作出选择。如果信任对方的预期利益多于风险,人们就会选择信任行为,从而在相互间建立信任关系;反之,则不会建立信任关系,”因而“医患之间的信任是以双方利益得到切实保障为基础的。”[7]信任是人际交往中所需要的主要因素,信任得以建立的基础是将对方的利益与安危置于自己之上,在医患关系中,如果失去信任,产生的危害是很大的。一方面,患者不信任医生,则容易产生戒备心理,增加和激化矛盾与冲突;另一方面,医生不信任患者,就会分散诊疗的精力,积极的治疗就会变成保守的应付,职业责任感弱化,同情心淡漠。同时,医患间的不信任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也是极大的,没有医患间的相互信任,则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就下降,医学探索的脚步就会停滞,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就会增加。
综上所述,传统儒家的德性伦理为我们当前的医德文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借鉴。当前的医德修养和教育存在着“走形式”的弊病,其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深入地去分析医德文化在整个医疗过程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当代医疗技术不断发展进步,医务人员和患者更多地依赖“硬性”的医疗条件和设备的情况下,往往忽视了医德文化这样的“软性”条件在医疗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只有实现医术和医德“双结合”,才能真正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实现社会整体的进步与繁荣。
[1] 吴阶平.医学人文演讲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
[2] 张艳清.“医者仁心”的解读[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2,25(2):257-258.
[3] 刘慧敏,刘余莉.儒家的礼、“自我”与德性完善[J].吉首大学学报,2012,33(6):61.
[4] 冯兆棣,冯同强,崔佰生,等,医患关系的文化背景[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1995,11(11):670.
[5] 蔡定彬.医德与医术的辩证思考[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1,24(3):385.
[6] 吴宇彤.医患关系与社会和谐[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6,22(12):823.
[7] 莫军成.论医患间的信任危机及其重建[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8(4):13.
〔修回日期2014-02-20〕
〔编 辑 李恩昌〕
Reference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 Virtue Ethics on Current Medical Ethics Cultural Construction
CHEN Mo
(School of Public Health,Medical College Of Guilin,Guilin 541004,China,E-mail:chenmokkk@163.com)
Medical ethics as a kind of professional ethics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ethics in medicine."Five Virtues"in Confucian virtue ethicsmeans the benevolence,righteousness,propriety,wisdom and trust,which have certain significance and references for currentmedical ethics cultural construction aswell as guarantee the security and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Confucian Virtue Ethics;Medical Ethics Culture;Benevolence;Righteousness;Propriety;Wisdom;Trust
R197.32
A
1001-8565(2014)03-397-03
2014-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