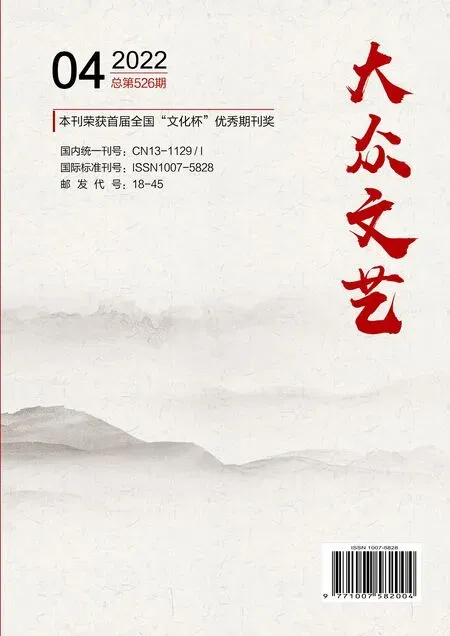汉代献赋活动与汉大赋的风格
何 凯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贵州贵阳 550001)
汉代献赋制度名义上以《诗》教“美”“刺”为其功用,而实际内容却颂圣为目的,与汉儒附会的《诗》教观念相去甚远。汉人献赋,多以美颂为主。君主对辞采的偏爱,以及赋家以献赋希求仕进的事实,乃是有汉一代赋作争競的至关缘由,并以献赋大势铺陈的风格。
一、汉代献赋活动以“献《诗》”为名
汉人论“献赋”同于“献诗”,且偏取“美颂”一端,首推班固。《两都赋序》谓“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者成康没而颂声寢,王泽竭而诗不作”3。以“成”“康”存,“王泽在”为“颂声”与“诗”的前提条件。到武宣之世“崇礼官,考文章”等帝朝廷实施的文治政策,在班氏看来,“炳焉与三代同风”,故有“言语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公卿大臣时时建作”。班氏将汉赋的作用规结为“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且将其等同于“奚斯颂鲁”,“皋陶歌虞”,要之,实取“赋者,美盛德之形容”4之意。班氏在《两都赋序》中,提到汉代武宣之氏献赋普遍存在的事实。
对献赋的评价中,仅取《诗》“颂”之一隅,不及《诗》之“讽刺”以苛论献赋的事实,在班氏看来,武宣之世的献赋,本来就不是讽刺时政阙失,而是歌颂当世的盛德。班氏的论述,则当世献赋,虽表面上等同于向来献《诗》之说,而实际却相去盛远。汉《诗》三家之说,均以《诗》有美刺二端,且就实际情形论,刺的内容远较“颂”的内容为多,而班氏只取献赋等“献《诗》以颂”的功用,显然与汉人说《诗》的大义并不相符。《两都赋》序虽云撰赋以讽,而赋实以美颂为主。
《后汉书•张衡列传》云“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赋》作《二京赋》,因以讽谏”5。据此则张氏作《二京赋》,亦以讽谏为旨,其与“献《诗》之说同义”。然《传》又谓“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则所谓“讽谏”,并不切实际。讽谏切求实效,此赋若以讽谏为意,“十年乃成”之时,当时要讽谏的社会现象可能完全不复存在。因此范书谓此赋为“讽谏”之说,并不准确。傅毅虽“以显宗求贤不笃,士多隐处,故作《七激》以讽”6,然其所献赋颂,实仅有献《诗》之名而已。范《传》云毅“于平陵习章句,因作《迪志诗》”。“建初中,以毅为兰台令史,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此时“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圣”,“因《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其所献赋颂,虽偶有“讽”“谏”,然美颂才是主要的倾向。
唯扬雄偏执“《诗》”学“献诗”以讽,《甘泉赋序》云“上方郊祠甘泉泰畤……还,奏《甘泉赋》以风”7;《河东赋序》云“……还,上《河东赋》以劝”8。扬子此赋,本文本伴随“其三月,将祭后土”的一次极其壮观的天下巡游,活动本身有劳民伤财之嫌,而《序》谓“奏赋以劝”,虽将献赋等于献《诗》,而其本身显然背离汉代《诗》学的精神。扬子《甘泉赋序》云“恐后世复修前好……因校猎赋以讽”9,此赋讽天子校猎奢靡太过,确取“献诗以讽”之意。扬子诸赋,确取“讽意”,其赋确实将“典终奏雅”作为献赋以讽的模式。考扬子作赋拟相如以为式,而司马迁谓相如之赋“归引之节”俭,当是错误理解相如亦献赋以讽,而不晓相如之赋以颂为要,拟其形制而失其意图。
“讽”“颂”“美”“刺”,被视作“献《诗》”的核心内容。汉人说《诗》,虽两有 “美”“刺”,而以“刺”为主。汉人将“献赋”等同于献《诗》,仅取其中“美”“颂”一隅。《诗》教在班氏的论述中发生从“讽”到“颂”的转变。易闻晓先生谓汉代之赋,多为赋体颂用10。辞臣献赋,本有见用的希冀,势必以美颂为主。汉人论汉代“献赋活动”,虽以“献诗”为名,而实无《诗》学“讽”“刺”之实。
这是一则来自娇韵诗的皮肤色素喷雾剂广告,用于皮肤的着色,使皮肤看起来犹如自然晒黑的一样。消费者解读该语的大致过程如下:
二、汉人献赋的实际效果
汉人献赋产生的实际效果,最能说明献赋必以美颂为主。辞作向君王献赋,本有希求见用的企盼,颂其功德,当是最为恰当的选择。从献赋产生的效果,可以看出献赋以颂的撰作取向。
相如以为诸侯之事无足观,“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奏之天子,天子大悦。”“赋奏,天子以为郞”11。天子大乐相如之赋,自然不是因为其赋归之节俭,因以讽谏,乃在意取美颂的铺陈气势。《资汉通鉴》载董仲舒荐其师申公,既至,“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余,对曰‘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如何耳’,是时上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12”。武帝对申公此对显然颇不满意。其不公仅欲闻治乱之事,且所对必求文采斐然。
汉代辞臣献赋,多居以郎官。《汉书•百官公卿表》云,“郞掌守门户,出充车骑”。则均以为近身侍臣。虽可“顾问应对”13,然以汉人言事多用论疏看,其所应对,当取“美”“颂”以合圣意。于情理而言,戍卫宫门与出充车骑,属于近身的长期侍从,帝王自然更希望其所应对,多合己意,而非事事规谏。所谓故谓应对,应该是以披敷辞澡的方式表达皇帝的意原。武帝好文辞,故相如以“包括天地,总揽人物的”的方式披敷辞藻,故能得到武帝的赏识。
《后汉书•班固传》云“自为郞后,遂见亲近”,“作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献赋本取“颂”意。范《书》复云“及肃宗雅好文学,固愈得幸,数入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每行巡狞,辄献上赋颂……赏赐恩宠甚渥”14。范《书》的记载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班固为郞后见亲近,同于司马相如。依帝意撰作文辞,当是辞臣的主要职责。其二,数入“读书禁中”,乃是恩宠的体现,居处不相离,如班氏献赋以讽,则于情理不合。其三,“读书禁中”,当是将文本读出来给皇帝听,《说文》曰“读,诵书也”15,其字从“言”,则诵书必有声响之义甚明,禁中乃皇帝居处之所,若非皇帝欲听,势必不能。其所读“书”,或包括所献之赋。当面“美颂”,故“恩宠甚渥”。
献赋产生的效果,决定于其所赋的内容与帝王意愿的契合程度。同赋关于东汉定都选址的朝野争议。《后汉书•杜笃传》有光武美其为为大司马吴汉之诔,不载其所献《论都赋》影响,其后仅“仅仕郡文学掾”,与班固、司马相如以为郞官,所受待遇相去甚远。《论都赋》所言,概在定都长安,不宜改营洛邑。定都洛阳,当是圣意已裁,杜赋已违其意,扬雄献《甘泉赋》讽天子宫室车骑后宫逾于法度。奏之天子,“天子异焉”,其所异者,16铺陈靡丽或是其一,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正在于扬子以经学讽谏的立场作赋,讥责太过,所献之赋即使不使帝王反感,亦必敬而远之。
三、汉人铺陈以献赋的取向
今存汉人所献之赋,多在京殿苑猎。意取美颂,则铺排必取车骑之众,山川之广,物产之富。其为赋以颂的文本意义,不是简单的定义,而是在籍名物的大量铺陈展现出来,甚至天惜借助虚构的名物展现所写场面的壮观和物产的繁阜。空间范围的使力经营,常常以点见面,四下铺开,其中每一相关系的事物,均呈现出一个相对完整的铺写单元。《上林赋》云“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壮上林苑的壮观,从东西南北四下展开。将上林物产系于各相关事物的铺写上。川泽草木,无不以繁阜为高。对物产的铺陈上,常常一类的事物相联铺排,在文本上形成联边字的现象。
帝王富有天下,山川物产是献赋“美”“颂”最好的取材内容。《上林》取材于苑猎,则必以上林物产为说。赋物产之丰,必将苑中所有,层层展开。其献赋的目的在于展现大汉帝国的气势,而其气势的展现,必然要借助名物的铺排。其后如班固《两都赋》所用“其东则”“其南则”按方位展开铺排的提示语,以及“其山则”“其木则”则表示物产铺排,都可以在相如赋中找到端绪。相如献赋,本不以讽,则扬雄献赋以讽,又每作赋必拟相如以为氏,显然赞赏相如所献之赋的铺陈形式,其所献诸赋,大势铺排上,确与相如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显然又误解相如赋献赋为讽,可谓南辕北辙。因此其所献赋形如相如,而旨不合。
汉代献赋本以美颂为主。而其所颂在于疆界之广,物产之阜,礼义之隆,美颂的指向,常在于一时代的自豪感,而非对具体帝王赤裸裸的颂扬。疆界之广,在赋的写作中体现为空间方位的四下铺开,物产之阜,体现为某一类名物的胪列;礼义之隆,则主要表现为使用当时普遍认同上古德行,资为作赋的典故。司马相如开端的献赋本于颂美,因此形成大势铺排的风格。其赋大气磅礴的气势,本身与颂美汉帝国结为一体,并不具有讽刺的倾向,就向来所谓“归引之节俭,与《诗》之讽谏何异”的奏雅之文,在赋文本表达为天子的自悟,以是具备圣君的品格,因而曲终之“雅”,已实际落实为天子具有的盛德,是颂而非讽。后来赋家,竞相规仿,显然认为相如奏赋以讽,必先极所赋之壮丽,文末示讽之意,是其讽谏的具体形式。于是,献赋之用讽颂分途。扬雄显然认为司马相如的讽谏是先极其壮丽,文末一语否定这种壮丽是其讽谏的形式,因而其所献诸赋在铺陈渲染上,亦是先极其壮丽,文尾否定。而如班固《两都赋》,按其《两都赋序》,明显把献赋当作“先臣之旧式,德音之遗美”,因而其赋亦是以东都主人对东都德盛的夸饰来否定西都宾对西都形盛的颂美。此颂美落实在东汉政权上合天理,下应民心,显然也是献赋以颂。因此,相如始献赋以颂要求作赋必然铺排敷衍,其后献赋或是误以为讽谏的具体形式,或是以为颂当如是,均以铺陈为主要特点,因此汉代献赋制度的存对此类赋作铺张扬厉的文风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注释:
1.《国语》,齐鲁书社,2005。
2.《毛诗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萧统编 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孔颖达《毛诗注疏》,《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5.范晔《后汉书•张衡列传》,中华书局,1965
6.范晔《后汉书•文苑列传•傅毅传》,中华书局1965
7.班固《汉书•扬雄传》,中华书局,1962
8.同5
9.同5
10.易闻晓《汉代赋颂文体的交越互用》,文学评论,2011(2)
11.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59
12.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86
13.杜佑《通典》,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14.范晔《后汉书•班固传》,中华书局,1965
15.董莲池《说文解字考证》作家出版社,2006.12
16.同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