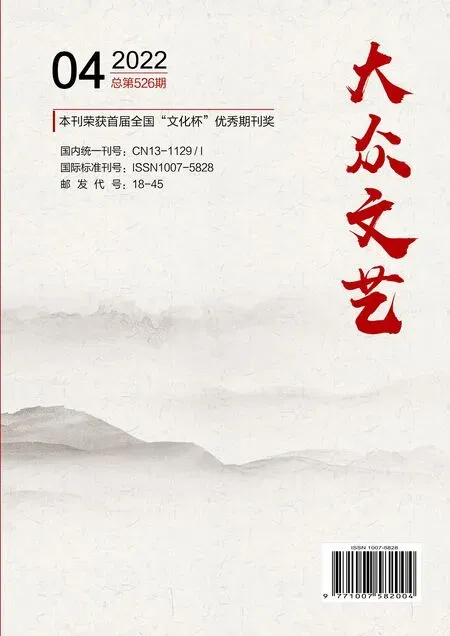论《边城》影视改编中的变化
黄 琼 (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安徽阜阳 236037)
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电影总是离不开文学作品本身的框架。总体来说,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电影大都遵循忠实于原著的原则,在精神内涵、艺术风格、内容结构上等方面与原著保持一致。但是考虑到文学与电影各自的艺术特征,影视改编也应该符合电影艺术形象的要求。由于作品的内容主要是由情节、人物、事件以及一些细节等要素构成的,因此改编也要紧紧围绕这几个要素。通过对原著和影片的阅读和对比,笔者发现小说《边城》改编成电影时,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对影片的成功与否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此外,文字到图像的转换所带给受众的审美感受也不同。
一、改变人物及形象
在电影《边城》中,改编者首先在人物的选择上突出了翠翠和爷爷这两个中心人物,对部分人物进行了删减和弱化。如“杨马兵”这个人物,作为“爷爷”的好友,他在小说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一直贯穿到小说最后。每一个重要的情节都有他的存在,从向老船夫说大佬喜欢翠翠,到天保大佬的死去,到撮合傩送二佬跟翠翠,再到老船夫的去世,杨马兵一直在引导故事情节的起落。但在电影中,自天保大佬去世后,杨马兵只出现一次与老船夫说起二佬与翠翠;老船夫去世后也并未提及他帮助翠翠办理爷爷的丧事以及照顾翠翠并成为她唯一靠山唯一信托人;更没有提到杨马兵回想年轻作马夫时,牵了马匹到碧溪,来对翠翠母亲唱歌,翠翠母亲不理会的旧事。虽然是次要人物,但是笔者认为“杨马兵”作为翠翠悲情爱情故事的见证者,关于他的一些情节是不能删除的。“杨马兵”作为见证者的出现,更能突出翠翠的人物形象,然而影片中该人物戏份太少。
其次,人物形象也有所变化。成功的影视改编作品不仅离不开好的故事,而且更离不开一些性格鲜明独特的人物典型。电影《边城》在改编是本着忠于原著的原则来拍摄,但是它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与小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并且各有特点。电影中翠翠的扮演者戴呐无论在年龄还是外貌形象上与翠翠都比较符合,但是却让人觉得形似神不似,因为影片中的翠翠少了几分少女的快乐和活泼,性格比较单一而且略显严肃忧愁。如老船夫得知中寨人要与顺顺家结亲后神情十分沮丧,翠翠以为爷爷发痧让爷爷去休息自己守船时小说写道:“翠翠自己守船,心中却古怪的快乐,心想:‘爷爷不为我唱歌,我自己会唱!’”对比电影,翠翠的表情不仅没有表现出她心中快乐,更是没有翠翠自己唱歌的一幕。她表情呆板严肃,好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又如翠翠在山上挖鞭笋时无意听到二老瑜脚夫的对话,知道二老喜欢的是“渡船”,回到家后爷爷让她猜猜是哪个熟人时她“脸红了”“半天不说话”后来又“两颊绯红跑了”。这一系列的描述充分体现了翠翠情窦初开的那种娇羞,而电影中翠翠却走开了而且面无表情,与小说完全不符合。
小说中的人物和电影中的人物有很大的差异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从文字到影像的转换过程中,人物的形象也会由模糊变得确定。文学文本所描述的画面必须依靠读者的想象和联想,在头脑中转化复现为逼真可感的艺术形象。“文字与它所表明的事物之间,也有着一种深刻的距离,所有使人都为如何能重视现实的问题而不安,就相中了邪一样1。因此小说的人物形象具有模糊性和间接性。
影视艺术通过蒙太奇组合的镜头来记录和复现客观世界,因此电影的人物形象真实直观,具有其他的艺术形式所没有的真实地反映对象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电影电视的本性就是活动的照相性,也就是逼真性2”。因此,影视改编中,人物形象也随着艺术形式的转换由模糊变得清晰。这种变化往往会造成读者和观众审美体验的不同。由于个人的思维模式、生活经历、个性追求、审美标准的不同,对同一个人物形象或有不同的想象。但是电影《边城》中人物的出现使得观众来自想象的美感消失,只能对于影片中人物形象做出外在的评价。这显然对人物形象的感受和影片主旨的理解是不利的。
二、细节的变化
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细节仍是决定作品成败的关键。影片中有几处对细节的改编与拍摄不是特别的恰当。如小说写到大老二老商量去翠翠家对面高崖唱歌时算算日子:今天十四,明天十五,后天十六,接连而来的三个日子,正是有大月亮天气。写到爷爷为翠翠讲故事时“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山上篁竹在月光下皆成为黑色”。但是电影拍摄却没有选择月色好的夜晚,只是黑漆漆的,这就使本该轻松的氛围显得格外压抑。另有一处,在老船夫得知大老淹坏了的时候到顺顺家打听,正在谈论此事的人“一到有人发现了身后的老船夫时,大家便把话语转了方向,故意来谈下河油价涨落情形了。”显然谈论此事的人有所忌讳,不愿意在老船夫面前说这事,也是间接表明对于大老的死大家对老船夫有误会。但影片中老船夫离烧纸钱的一群人距离很远,离近时又遇到了顺顺最后作罢,并没有表现出对老船夫有误会,反而是老船夫最后自己到河边往河里倒酒并自责地说“大老!都怪我!都怪我!”这显然与小说和事实不符,小说中应该是二老对老船夫有误会而不应该是老船夫自责。再如,小说中数次提到白塔。“白塔”象征着当地风水,更是翠翠与爷爷生活的一部分。电影中虽然也是多次有拍摄到白塔,但是却没有涉及白塔坍塌的细节。暴风雨过后,过度的缆绳与渡船不见了,白塔也坍塌了,就在翠翠不知所措时爷爷也去世了。作为翠翠生活的重要部分的一切都没了。而电影中只拍摄到溪里的急流(若无提醒很难立刻联想到渡船没了),却舍弃了坍塌的白塔。实际上翠翠是看到坍塌的白塔才去叫爷爷并发现爷爷去世的,因此笔者认为这一细节不可删去,否则就显得有些突兀。
三、审美效果的变化
科技的迅速发展、电视电脑的普及以及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得读书尤其是看小说的人越来越少了。相当一部分人就认为,那些经典的文学作品,如果没时间去仔细的阅读,看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也是一样的。其实不然。虽然改编的电影是依据文学作品原著,但是它并不能代替文学语言所创造的审美意象的特殊作用,因此欣赏原著和观看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其效果是有差异的。
文学属于语言的艺术,它所创造的审美意象是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审美价值的浓缩的“典型”,蕴含丰富深刻的内容和人生哲理,善于通过修辞的手法进行描述,给读者以广阔的想象空间,使他们在阅读的过程中调动起再创造的积极性,从而获得一种更高的审美愉悦。小说《边城》中的翠翠形象:“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在这里每个人脑海里所浮现的翠翠都是不一样的,是和个体的审美想象有关的。这种对于翠翠形象的不确定性,给了读者丰富的想象并且这种想象的感觉令人陶醉其中。电影是用声音和图像的综合形态来创造审美意象的。它的审美直观性很强,观众能看到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是一种人们用眼睛就可以获得的什么感受。这种方式就限制了观众的审美想象,使观众不能以自己的视角去欣赏原著中本身所塑造的审美意象。例如,翠翠的出场虽然让人感到她的天真活泼,却不容易察觉到她“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的特点。镜头的转换把实实在在的“翠翠”刻画在荧幕中,观众更无法得到想象的愉悦体验。
如果是从接受效果和消费价值来说,以图像为媒介符号的电影所需要的文化水平相对来说比较低,且它的声画效果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符合现代的文化消费潮流。因此总这一角度看,小说远无法与影视剧相抗衡。但是作家在创作作品时是能够通过词句的组织来传达完整的气氛和概念,从而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和审美体验的。因此不管是再高明的影视改编者,都是无法传达文字叙述故事的这种“神韵”的。正如莫言所说的“在有了录音机、录像机、互联网的今天,小说的状物写景、描图画色的功能,已经收到了严峻的挑战。你的文笔无论如何优美准确,也写不过摄像头的镜头了。唯有气味,摄像头还没法表现出来3”。这种文字特有的“气味”正是小说与影视审美效果的重要分水岭。小说改编成电影后,受众的身份也发生了转变,即由读者转变到观众。随着受众身份的转变,对作品的审美追求也不同。阅读更加追求文学作品的的思想深度,蕴含哲理和表达内容;而影像是读图听音的艺术,观众追求的是画面的壮观,声音的处理以及演员的功底水平,对于隐藏在原著作品深部的思想往往会忽略。不同艺术形式下的受众审美追求的不同,你然决定了其各自的审美体验,由此小说和电影的审美效果必然不同。
四、结语
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无论对于文学文本的生命力还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思想构建,都是大势所趋。影视的繁荣需要以文学的进步为支点,而文学作品的改编也会扩大小说的传播其影响。由凌子风导演的《边城》虽然本着忠于原著的原则,但是改编后的电影上座率并不高,并没有达到和小说相得益彰的效果。时过境迁,80年代拍摄的《边城》在如今看来在人物形象、细节处理、故事情节等方面都有值得商榷之处。尽管名著在影视改编中很难超越原著,但是只要较好地遵循影视艺术的特定规律,那么由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仍会取得较好的审美效果。恍惚二三十年过去了,这期间影视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对沈从文的研究也有了更深入的展开,笔者相信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实力和条件来重新解读这部名著,当代影视文化需要像《边城》这样经典作品来充实,让我们期待新的改编出现!
注释:
1.李晓盼.浅谈文学改编电视剧中两种语言体系转换的障碍[D].辽宁:辽宁大学.2012.
2.彭吉象.影视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3.莫言.小说的气味[J].天涯.2002年第2期,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