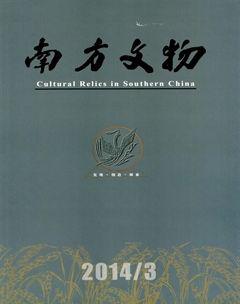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奠基之作
朱乃诚


《京山屈家岭》是一部很不起眼的考古发掘专刊。这部发掘专刊的文字及插图不足100页,图版不足60版,而且在1965年秋经科学出版社出版之后不久就逢“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京山屈家岭遗址发掘主持者与报告编写主持者张云鹏先生在文革中被残酷迫害而过世,后人对这部发掘专刊未作任何的宣扬。然而,这部不起眼的考古发掘专刊,却是我国江汉地区、也是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奠基之作,自然也是张云鹏先生为中国考古学留下的一份宝贵的遗产。
一、 屈家岭遗址的发掘过程与主要收获
京山屈家岭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成果,是20世纪50年代长江中游地区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的一个亮点。
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起步较晚,最先是从江汉地区开始的。1954年举办的“第三届考古训练班”有几位湖北省的学员。他(她)们学成结业之后,适逢在江汉地区的中心地带开展石龙过江水库的基本建设,他们带着在考古训练班学习的知识以及在西安半坡遗址实习积累的考古发掘经验,与“第一届考古训练班” 学成结业的湖北省学员一起,配合工程开始了江汉地区的首次新石器时代田野考古工作,调查发现了上百处古文化遗址,多为新石器文化遗存,京山屈家岭遗址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处。这一重要考古发现上报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即派遣张云鹏等先生前往领队主持考古发掘。他们经实地考察,认为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有重点保护的必要,提请将此段石龙过江水渠改道至遗址边缘地带穿过。此意见落实之后,于1955年2月在新规划的水渠线路上试掘开了四条探沟。一个影响至今的考古发掘就这样开始了。四条探沟的试掘收获,发现了一种在其它地方未曾见过的新的文化遗存。如薄胎的细泥黑陶、薄似蛋壳的细泥彩陶等,并认识到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决定在屈家岭遗址上,开始以探索长江中游史前考古学文化为课题的学术性考古发掘。于是在1956年6月至1957年2月进行了正式发掘,发掘工作由张云鹏先生主持,并得到夏鼐先生指导(由张云鹏先生通过书信往来即时请示汇报),湖北省的文物考古人员自始至终配合了考古发掘。此次扩大了发掘面积,在水渠旁、老槐树下布197个探方,揭露面积858平方米(图一)。《京山屈家岭》公布了第二次发掘的全部收获与研究认识。
屈家岭遗址第二次发掘发现的文化层堆积分为两大层,即早期文化层和晚期文化层,晚期文化层又分为晚期一与晚期二两段。
在早期文化层中发现灰坑24个,墓葬一座。灰坑中出土了一批陶器残片,以薄胎黑陶为主要特色。墓葬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有4件陶鼎、1件陶圈足器。黑陶鼎的形制与灰坑中出土的相同。在早期文化层中出土的遗物有石斧、锛、刀、凿、钺(穿孔铲)、球等石器,陶器有碗、缽、盘、碟、曲腹杯、纺轮、陶球、陶环、陶祖等,以带盖或无盖黑陶小鼎最具特色,朱绘蛋壳黑陶亦较突出,并出有白衣彩陶片等。还有玉坠、玉璜等小型玉饰品。
在晚期一文化层中发现一处建筑遗存、一座墓葬。建筑遗存的面积约500平方米,可能是一种建筑物倒坍后的堆积,其内揭露出近30平方米的一块烧土地面、墙面残块以及带有木柱痕迹的柱洞,显示木柱的直径约10厘米以上,深约30~40厘米。有的烧土块上有“白灰面”。尤为重要的是,在建筑物烧土中有大量的稻谷壳和作物的茎的痕迹。是我国首次发现的羼稻谷壳和作物茎的草拌泥建筑材料,经对稻谷壳形态的鉴定,属栽培稻中的粳稻②。发现的一座墓葬仅残留部分骨痕,可辨其为仰身直肢葬。
在晚期一文化层内出土的遗物,有石斧、锛、凿、刀、镰、杵、镞以及钺等石器、陶缸、甑、鼎、缽、碗、双腹碗、薄胎彩陶碗、蛋壳彩陶碗、豆、杯、蛋壳陶杯、蛋壳彩陶杯、三足碟、罐、壶形器、彩陶壶形器、器盖、纺轮、有彩或无彩陶纺轮、陶环、彩绘陶环、陶球等陶器,以及小型玉饰品。
在晚期二文化层中亦发现一处建筑遗存和一座墓葬。建筑遗迹南北长14米,东西宽约11米。分南北两部分。北边是一个长方形烧土台子,东西长8.9米,南北宽6.62米,高0.55米,在南、北两侧各有4个柱洞,柱洞直径约0.26~0.46米,深约0.4米。南边是一片平坦的烧土,低于北边的烧土台子约0.2~0.5米,东西残长约5.04米,南北宽7.38米,厚约0.1米,上面有16个不规则的圆洞,直径在0.13~0.4米之间。在这处建筑遗迹的烧土中亦发现有稻谷壳。发现的一座墓葬为屈肢葬,骨架已朽。
在晚期二文化层内出土的遗物较为丰富。石器有斧、穿孔钺、锛、刀、镰、凿、钻形器、杵、镞、矛(采集)、小型锛、棒形器(笄?)等。其中石钺已是典型的“风”字形钺,石笄首部穿孔。都是进步的文化因素。陶器有陶镰、镞、棒、纺轮,彩绘纺轮、陶针形器、尖圜底盆形大陶锅、甑、双腹盆形鼎、罐形鼎、碗、双腹碗、蛋壳彩陶碗、缽、盘、豆、双腹豆、盘形或碗形圈足豆、杯、蛋壳陶杯、蛋壳彩陶杯、小型陶杯、高圈足杯、凹底、弦纹等各种罐、各种壶形器、盂形器、缸形器、瓶形器、筒形器、四耳器、各种器盖、彩陶器盖、陶环、彩绘陶环等。有的器形如四耳器等的用途至今尚未明确。玉器有小型饰品。还有骨针。
屈家岭遗址第二次发掘,获得了两处建筑遗存、一批灰坑、三座墓葬及一大批石器与陶器。其中两处建筑遗存虽然不完整,但其规模已显示了当时的建筑形式较为进步。一大批陶器的出土,首次展示了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早、晚两期的文化面貌,以及鲜明的地域与时代特征。而蛋壳彩绘陶器、穿孔石钺,尤其是“风”字形石钺、玉饰品以及大批粳稻遗存等物质文化,则已显示江汉地区拥有的发达的原始农业经济和十分进步的灿烂的史前文化。如此繁荣多彩的屈家岭文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学术界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屈家岭遗址的发掘收获,成为20世纪50年代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一个偏离黄河流域研究中心区域的闪光点。
二、 《京山屈家岭》的编写体例与特点
屈家岭遗址第二次发掘是在遗址边缘的一角进行,揭露面积不大,是20世纪50年代成规模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形成考古学专刊的9处遗址中,发掘面积最小的一处遗址,出土的文化遗存也最少。但经张云鹏先生等人对遗址发掘的层位把握,以及对出土物的细致分析与科学的整理,形成了一部很有特色的发掘专刊。
《京山屈家岭》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言,交待遗址所在的地理位置与环境特点,发现与发掘过程,以及本报告的内容。并附清晰的遗址地形和探方位置图,以及探方分布图。
第二部分为地层堆积。详细介绍发掘区的层位现象,介绍依据层位现象和出土物的分析而明确的早期文化遗存、晚期文化遗存,以及为何要分为晚期一文化遗存、晚期二文化遗存的地层依据。
这部分是《京山屈家岭》报告的精华之一,也是20世纪50年中期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特别注重提倡的科学内容。其中晚期一与晚期二的地层划分,在1956年的实施,是相当的前沿,稍微粗略的田野考古学家,很可能会错失良机而将他们作为同一个时期来对待。张云鹏先生依据揭露的两大片红烧土层存在着“出土先后和交界处的互相压迭”现象敏锐地将此作为“这一文化堆积的早晚期的划分界线”。
当年对屈家岭遗址的这一层位划分,奠定了屈家岭文化分期的依据,并且直至今日未曾动摇。
屈家岭遗址发掘过程对层位关系的划分,确立了《京山屈家岭》发掘专刊按早期文化遗存、晚期文化遗存、并在晚期文化遗存中又分为晚期一文化遗存与晚期二文化遗存进行编写的体例。
第三部分为早期文化遗存。全面介绍了早期文化遗存的遗迹与遗物,并分为遗迹和所出遗物、文化层中出土的遗物两节。将遗迹中出土的遗物按遗迹种类分别介绍,如灰坑与灰坑中出土的遗物,墓葬与墓葬中出土的遗物,还公布23座灰坑出土陶片的陶系统计表,便于读者对遗迹的文化面貌与特征的把握。这种公布资料的方式,贯穿整个报告。
第四部分为晚期文化遗存,并分两部分,分别全面介绍晚期一文化遗存与晚期二文化遗存。
在第三部分与第四部分中介绍的出土遗物,按用途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其他等几类进行,在用途分类内再按石质与陶质等质地分别集中介绍,然后按器类与样式两级分类方式介绍每一件器物。这种对出土物的分类别介绍方法,是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考古发掘报告通用的方式。
《京山屈家岭》对一些特殊的器物,以特殊的方式进行介绍。如早期文化遗存中的朱绘黑陶片、晚期文化遗存中的彩绘陶纺轮、彩陶碗、蛋壳陶杯与蛋壳彩陶杯、彩绘陶杯、蛋壳陶碗与蛋壳彩陶碗、彩陶器盖、彩绘陶球等,一件一件详细地介绍陶质、胎厚以及彩色纹饰等细微的特征。
第五部分为结论,阐述了作者对屈家岭遗址第二次发掘收获的总体认识。提出“屈家岭文化”的命名,论述屈家岭文化的分期与特点,分析屈家岭文化的社会经济、精神文化,结合鄂西北郧县青龙泉等遗址的发掘成果,阐述屈家岭文化与仰韶文化及龙山文化的年代关系与文化关系,以及屈家岭文化的分布范围,推论屈家岭文化的年代、屈家岭文化早晚演变关系等,基本上论述了1960年前后可论及的有关屈家岭文化的各个方面。
《京山屈家岭》整部报告的各章节,短小精简,但脉络相当清晰,表明作者对报告内容的整体把握得心应手。而文字阐述十分精练,没有一句赘言。如一些章节的序,用一句话表明,言简意赅。文如其人,读《京山屈家岭》,可从中得知张云鹏先生是一位办事精练、性格秉直、干脆的学者。
三、 《京山屈家岭》的学术贡献
屈家岭遗址的发掘,是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以空前的速度开展起来的大背景下进行的③,由于其文化内涵的特殊,尤其是大量朱绘黑陶与蛋壳彩绘陶的出土,以及蛋壳彩绘陶叠压在朱绘黑陶之上的清晰的地层关系的揭示,受到学术界的热切关注。发掘报告在1960年编写完成尚未出版之前,报告的主体内容就被《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④和尹达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一文所引用⑤,成为当时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研究中,吸引研究者的一个闪光点。在屈家岭遗址发掘近六十年、报告出版近五十年的现在重读这一发掘专刊,仍然感受到其在许多方面的重要的学术贡献。
第一,填补了江汉地区新石器文化研究的空白。
在1955年以前,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只知道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甘肃仰韶文化)与齐家文化、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浙江北部的良渚文化、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松辽平原西部昂昂溪文化,等等,对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文化面貌一无所知。屈家岭遗址的发掘,揭露出一种面貌全新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在整个长江中游地区激起了浪花,使研究者对长江中游地区乃至整个长江流域及华南广大区域的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前景充满信心。5年后,学术界结合四川巫山大溪遗址、江苏淮安青莲岗遗址、南京北阴阳遗址等的发掘收获,将长江流域从西起巫峡、东至大海的整个区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的关系问题,最终导致了长江流域的原始文化并不落后的认识的产生。
屈家岭遗址的发掘,在江汉地区确立了一个新的新石器文化,极大地推进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开展。
第二,开始了江汉地区新石器文化编年与文化谱系的探索。
1956年在屈家岭遗址发掘中揭示明确的屈家岭早期文化遗存、屈家岭晚期一文化遗存、屈家岭晚期二文化遗存的先后编年关系,为后来的江汉地区乃至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编年与文化谱系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意义有三个方面。
一是将屈家岭早期这类以朱绘薄胎黑陶器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从以双腹式器形、蛋壳彩绘陶器类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中区别出来,并明确前者早于后者、两者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前后发展演变关系,成为后来进一步探索屈家岭文化源头的不可动摇的信条。尽管至今对屈家岭早期文化遗存的归属仍存有争议,但这类文化遗存早于典型屈家岭文化、是典型屈家岭文化的前身,没有异议。
二是将屈家岭晚期文化遗存区分为有着早晚演变发展关系的晚期一文化遗存、晚期二文化遗存,成为后来进行典型屈家岭文化分期的标志。
三是以“早期文化遗存”、“晚期一文化遗存”、“晚期二文化遗存”三个名称的巧妙使用,为后来深入探讨屈家岭遗址的早期文化遗存与晚期文化遗存的文化名称问题,留下了可供深入的巨大空间。
张云鹏先生对屈家岭遗址第二次发掘出土的遗物的分析,首先区分出早晚两种文化遗存,然后在晚期文化遗存中再区分为晚期一、晚期二。这样的分析表明:早期文化遗存与晚期文化遗存的区分,是第一个层次上的区分,这种区分方式,使得在今后的研究中,随着资料的增多,可以将这两种文化遗存作为两个考古学文化来对待。而晚期一与晚期二的区分,则是第二个层次上的区分。这种区分方式,使得在今后的研究中,随着资料的增多,可以将这两种文化遗存作为一个考古学文化的两个期来对待,而不能分作为两个考古学文化。
张云鹏先生如此巧妙地使用这三个名称,完全出于他对屈家岭遗址发掘出土物的细致分析,掌握分析对象的文化特征及其存在着的演变规律。当然,在50年以前,张云鹏先生以及整个学术界,不具备条件将屈家岭早期文化遗存单独提取出来命名为另一个考古学文化,而只能将屈家岭早期文化遗存与晚期文化遗存合并在一起作为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早晚期来阐述。但其阐述方式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方便。
现在看来可将以朱绘薄胎黑陶器为主要特征的屈家岭早期文化遗存单独作为一个文化类型来看待,以反映江汉地区新石器文化发展至距今5300多年至距今5000年之间而产生的一个文化上具有过渡特点的文化现象。
第三,首次明确了我国距今四五千年的稻作遗存。
我国原始稻作农业的研究,起步较晚,屈家岭遗址发现的大量稻谷壳和茎遗存,开启了从植物遗存探索原始稻作农业的研究序幕。发现的稻作遗存,经丁颖先生分析研究,确认为粳稻,由此将粳稻的栽培从原来认识的汉代上推至距今四五千年。这在50年前是原始稻作农业研究的重要成果。
第四,展示了江汉地区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已达到的相当发展的文化现象。
如大面积红烧土及带有柱洞的建筑遗存,表明当时的建筑物规模比较大。朱绘薄胎黑陶器、蛋壳彩绘陶杯与陶碗,年代比龙山文化早,表明在距今4600年以前,江汉地区的制陶技术居于领先地位,大批彩陶纺轮又表明这里的纺织技术在当时也居于前茅。而稜脊明显、刃部锋利的小石锛,很有地方特色,在同时期的其他文化遗存中十分少见,也说明了当时江汉地区的手工业生产技术较为进步。
值得重视的是,约距今5000年前的玉器在屈家岭遗址发掘中首先得到了确认。在屈家岭早期文化遗存、晚期文化遗存中都发现有玉质装饰品,如小型的穿孔坠饰、各种形状的弯条形玉坠饰或是残断的玉璜等。这些小件玉器,因有确切的出土层位,年代不可置疑,其中屈家岭早期文化遗存中的玉器,年代在距今5300多年至距今5000年间。这是屈家岭遗址发掘对史前玉器研究的重要贡献。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发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
还有,出土的屈家岭晚期的“风”字形石钺,型制十分规范,是表现当时社会存在部族间争斗的重要现象,表明江汉地区的文明化现象起步较早。这一点在1989年夏第三次抢救性发掘屈家岭遗址时得到印证。如第三次发掘清理的属屈家岭早期文化遗存的墓葬有13座,其中M2、M12两座墓规模较大,分别随葬陶器70件和54件⑥,表现出江汉地区在距今5300年前社会即已产生了明显的贫富分化。
此外,大型陶祖形器,上下、四面贯通的六孔陶管,高约40厘米的镂孔筒形器等都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有待探索。
四、 结 语
《京山屈家岭》是湖北省第一部考古发掘专刊,也是长江中游地区第一部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专刊。屈家岭遗址在发掘之时,即得到学术界的特别重视,发掘之后的成果未及出版就被及时引用。这些都充分表明,京山屈家岭遗址发掘以及《京山屈家岭》报告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屈家岭遗址面积约40万平方米,1955年、1956年、1989年的三次发掘,规模都不大,都是在遗址的边缘地带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如第一、二次发掘是在遗址的西南边缘配合石龙过江水渠工程而开展的,第三次发掘是在遗址的北部边缘配合建设工程动土而开展的。三次发掘的总面积不足1000平方米,以第二次发掘规模最大,揭露面积858平方米。这样的发掘规模以及发掘区域位置可能达不到全面、准确揭示屈家岭遗址文化内涵的目的。但是,学术发展史表明,屈家岭遗存第二次发掘收获及其研究成果,奠定了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基础。屈家岭遗址因第二次发掘而被重点保护了下来,列入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年张云鹏先生等发掘工作人员居住的村民的民房亦完好地保存至今(图二)。
近五十年前出版的《京山屈家岭》一书的封皮在退色,内页却在增色,逐渐增黄,而文字内容以及那些体现器物特征与精湛的绘图技巧的器物插图和彩色的、黑白的器物照片,却总是那样的精练与精致,不断地吸引着后来的研究者,使得这部薄薄的精装本《京山屈家岭》,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熠熠生辉。
注释:
① 王劲、吴瑞生、谭维四:《湖北京山县石龙过江水库工程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4期。
② 丁颖:《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的稻谷考察》,《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
③ 见尹达:《新石器时代·再版后记》,三联书店,1979年。
④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
⑤ 尹达:《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考古》1963年第11期。
⑥ 屈家岭考古发掘队:《屈家岭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
(责任编辑:周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