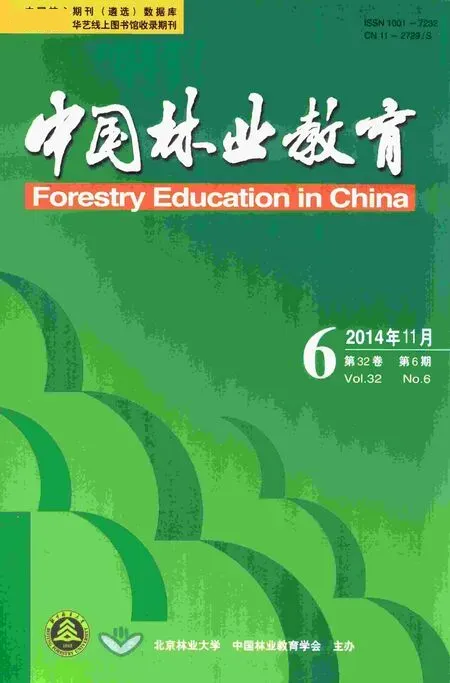农林院校“景观生态学”本科课程的教学设计
郑景明 康峰峰 周志勇
(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北京 100083)
景观生态学是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吸收现代地理学和系统科学之所长,把景观和区域尺度的资源、环境、经营与管理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尤其着重中尺度的景观结构和生态过程关系的研究,具有综合性和宏观区域特色。近年来,景观生态学发展迅速,已从地区性应用学科发展成为体现生态学主流并盛行于全球的综合性学科,在研究理论、方法和应用上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在此背景下,必须加强景观生态学的教育与培训[1],以适应景观生态学发展的需求。
一、农林院校“景观生态学”本科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目前我国很多综合性大学、农林院校、师范院校都开设了“景观生态学”的本科课程,但“景观生态学”课程开设时间相对较短,理论体系仍在发展过程中,教材、实验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使得教学效果差强人意。
(一)在专业培养中的定位不明确,课程设置不合理
我国高等院校的“景观生态学”本科课程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在专业培养中定位不明确,在学科发展中的定位也缺乏连续性。虽然景观生态学对于自然资源管理、环境规划、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是基础性的学科,但高校中的“景观生态学”本科课程通常不作为必修课程开设,选修范围一般局限于少数专业,课时较少,这种现象在农林院校中尤为普遍,“景观生态学”课程往往被视为主要专业的拓展性课程。究其原因,首先从大环境上看,国内的景观生态学教育起步较晚,与德国和英国比较成熟的景观学科教育体系相比有很大距离[2-3]。其次,农林院校的课程体系的设置现状也是“景观生态学”课程教学效果不佳的原因。景观生态学的主要知识基础是地理学和生态学,然而在大部分农林院校中,相关专业学生更多偏重农、林学或大生物学背景,缺乏地理科学专业主干课程的相关知识结构,遥感和地信等相关操作技能储备不充分,景观生态学只能以交叉学科的名目沦为农学、林学、环境学、生物学、园林规划、资源管理等专业的附属课程。这些不利因素最终导致“景观生态学”课程处于被动、从属的状态[4]。
(二)师资力量不足,课程建设落后
当前在各高校现行的考核体系中,教学所占比重难以匹敌科研是不争的事实,尤其研究型学院的教师在科研工作中投入的时间很多,专职从事景观生态学研究的教师人数相对较少,使得景观生态学的师资力量薄弱。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自行编写的“景观生态学”中文教材数量屈指可数,编写质量和更新速度也难以同欧美等国相媲美。中文教材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农林院校的“景观生态学”课程的教学水平发展缓慢、课程建设落后。
(三)实习实验设施不足,实习效果不佳
很多开设“景观生态学”课程的院校没有合适的实习基地或精心设计的实习计划,导致实习环节效果不佳;有的甚至没有设置课程的实验或实习,使得学生产生“景观生态学”课程过于理论化,难以在实践中广泛应用的错误印象。因此,应当根据农林院校的实际情况深入研究“景观生态学”课程的教学设计理论,在新的形势下加强“景观生态学”的课程改革,为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大学生和后备研究人员提供助推力。
二、农林院校“景观生态学”本科课程的教学设计
(一)指导思想
考察生态学的发展历史,生态学知识体系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史研究中蕴含的各种理论知识,也有昆虫防控、植被区划等经验性知识。景观生态学的发展也有着类似的轨迹,既有欧洲学派的区域规划传统,也有北美学派的生态系统的研究手法,还有全球环境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新的概念、思想、方法不断被纳入,使景观生态学在迅速壮大的同时略显粗糙。因此对于本科教学而言,景观生态学的体系不够严密,内容抽象,可操作性不强。农林院校中作为选修课程的”景观生态学”课程不超过50学时,且缺乏实习和实验环节,造成了理论和实践脱节的情况[5]。因此,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本科生的“景观生态学”课程应以培养景观生态学思维方式、掌握景观生态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强化景观生态学空间分析的基本技能为核心,对理论内容不宜求全求新,应设立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景观生态学”课程的教学目标。
(二)内容体系
景观生态学是以较大尺度的土地单元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本质上属于宏观生态学,它以格局—功能—动态关系为中心,在自然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可持续发展规划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性。任何课程知识体系的构建都要既立足于课程自身的特点,又要着眼于专业的发展需求,“景观生态学”课程也是如此,如地理学专业的学生往往生物学知识不足,必须在课程中适当补充[6];农林院校的学生在学习“景观生态学”的过程中,教师除了需对学生适当补充地理学相关知识和技能外,还应根据选修学生的不同专业、不同的发展方向设计课程内容,不能一本教科书通用。鉴于“景观生态学”课程的选修对象是来自不同专业的大学生,所以应当按不同专业的知识结构及特点设计不同的教学内容。以北京林业大学为例,选修“景观生态学”课程的本科生主要来自林学、自然保护区学、环境与城乡规划专业,这些专业的知识体系有共同之处,都有林业和生物学背景。但这几个专业的发展方向是有差异的,林学专业更侧重森林生态系统管理和利用,自然保护区专业更重视物种多样性保护和生境管理,环境规划则更关注城乡区域规划问题。因此,应针对不同的专业发展方向设计“景观生态学”的课程内容。
首先,“景观生态学”核心理论内容应包括景观的空间性特征、尺度的概念、景观的构成要素、景观格局的概念、景观的动态、景观的功能、结构和功能的联系及最佳景观格局原理。
其次,基本空间数据分析技能方面应包括空间生态数据的调查方法、空间地理数据使用和数据格式转换、采用格局分析软件做景观格局指数计算与生态学意义分析、采用空间马尔科夫模型做景观动态预测、景观制图及文献检索与综述。
第三,实践技能方面可包括森林景观的分析与管理设计案例、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廊道设计案例、小城镇和乡村可持续发展规划案例等。
(三)教学方法
“景观生态学”课程选修一般是在大三年级开设,而这时学生刚刚开始涉及到主要专业课内容。在这种情况下,让学生理解景观生态学中相对繁多的理论和假说及广泛的应用领域,对于大学生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授课教师应针对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在“景观生态学“的教学中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方法的革新。
1.引入直观性教学材料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加大直观性教学材料的引入。与现实环境问题紧密联系的、丰富的图片和影像,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采用GOOGLE EARTH、WEB GIS等平台教学,可以增强学生对景观生态学对象的直观感受,从而激发其对课程内容的兴趣。
2.教学内容模块化设计
教师可以将教学内容分解成几个模块,每个模块归纳为知识群,每一个知识点辅以适当的案例,摒弃“填鸭式”授课方式,鼓励学生自主选择学习。
3.实施启发式教学
教师应针对每一个核心的概念和知识点组织课堂讨论,及时点评作业,吸引学生参与相关研究项目,使学生主动学习,积极实践,有利于将课程理论内容与实践相结合。
4.加强与相关课程的联系
“景观生态学”课程与很多课程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景观生态学”课程学习中,选课学生经常提到虽然一些内容已经在其他课程中学习过,如遥感图像解译、森林经营技术,但并没有很好地融会贯通,通过学习“景观生态学”课程,发现很多知识在课程实习和实验中都串联起来了,从而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思维活跃程度。所以各院系在专业课程设置时,应考虑到相关课程的知识体系的联系程度,在课程开设时间顺序、实验内容的设计等方面合理安排,从而提高学生专业知识的学习效率和实验操作的技能[7]。
三、农林院校“景观生态学”本科课程教学改革的效果
北京林业大学通过几年的“景观生态学”课程的改革实践,认识到要保持“景观生态学”课程的生命力在于通过讨论式、参与式等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宏观生态思维方式,精心设计配合核心理论内容的实习实验,促进学生对相关专业知识的融会贯通,最终在熟练掌握景观生态学基本研究技能的基础上提高创新能力。通过对改革后的“景观生态学”课程教学效果的调查结果分析,大部分选修“景观生态学”课程的学生在认真完成课后作业和实习实验内容后,加深了对所学专业知识的理解,提高了软件操作、数据分析、科技写作等综合能力,对现实中的大尺度生态环境问题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与传统教学方式相比,按新思路设计的教学效果有了显著的改善,基本达到了“景观生态学”课程所设计的预期目标。因此,不断开展“景观生态学”课程的教学设计和研究,逐步解决好专业课程设置中的一些问题,“景观生态学”完全有可能成为农林院校某些专业的核心专业课程,在培养具有开阔的视野、丰富的理论储备、扎实的操作技能、较好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人才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四、实践教学
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尺度的土地单元,理论知识比较抽象,不易被学生接受。要把课堂知识转换为实践能力,必须通过加强“景观生态学”的实习来实现,主要的实习环节是野外实习和模拟实验。
“景观生态学”课程的户外实践教学工作有3个层次,即学位论文的专题研究、中期野外实习、辅助课堂教学的短期观摩。对选修课程的本科生而言,短期观摩尤为重要。各个农林院校可以因地制宜,根据校园周围或实习基地附近的景观特征,通过网络模拟设计实习路线,按实习内容合理设计观摩地点,户外观摩教学与地方管理者研讨等方式,使学生直接观察到真实景观的组成和格局特征,接触到现实的环境问题,并从景观结构、功能的角度思考问题,加深对景观生态学理论的认识,提高学以致用的能力。
现有的景观生态学实验方法可分为3类:野外比较观测性实验、操作性实验设计、计算机模拟实验。由于景观的宏观生态学性质,模拟实验是克服实验条件不足的一个重要替代途径,并对景观生态学理论的检验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8]。在此方面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S.E.Gergel和M.G.Turner(2002)组织编写的“景观生态学”实验指导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不但设计了“景观生态学”中重要主题的各种室内数据分析和模拟实验,同时也区分了适用不同学习者(研究生、本科生)的实验难度,可以用于课程实验或自学[9]。由于该书编写的时间较早,其中的一些软件已经过时,景观生态学发展的新内容没有纳入。因此,教师可借鉴其实验设计方法,采用国内资料和常用的软件设计适用不同专业的“景观生态学”课程实验体系,逐步完善景观生态学的实习教学活动。
五、课程考核方式
“景观生态学”的课程内容实用性强,单纯书面考试的形式不利于促进学生动手能力的提高,也不利于将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所以,笔者在课程初期按照教学内容设置了一系列的单项小实验,要求学生定期完成实验报告和主题综述,将其作为成绩评价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进入课程后期的实践扩展阶段,则以小组为单位完成综合性实验,采用学生演示和教师组织讨论的形式进行学习成果的总结与提升。最后利用综合考试、平时实验报告和综述及小组汇报结果,客观评价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投入和效果。考核方式多样化,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他们运用所学景观生态学知识分析和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10]。
[1]邬建国.景观生态学——格局、过程、尺度与等级[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90.
[2]陈芳,冯革群.德国大学的景观生态教学[J].世界地理研究,2005,14(3):103-108.
[3]邓位,申诚.英国景观教育体系简介[J].世界建筑,2006,26(7):78-81.
[4]何东进,洪伟,吴承祯,等.景观生态学精品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研究[J].高等农业教育,2011,8(8):51-55.
[5]楚光明,宋于洋,李明艳,等.林学专业“景观生态学”课程教学探讨[J].安徽农学通报,2009,15(8):221-222.
[6]黄义雄.地理理科基地班景观生态学课程教学工作的探讨[J].福建地理,2002,17(2):25-26.
[7]彭奎,李远,李宏.景观生态学双语教学探索[J].中国冶金教育,2011,15(4):66-69.
[8]沈泽昊.景观生态学的实验研究方法综述[J].生态学报,2004,24(4):769-774.
[9]GERGEL S E,TURNER M G.Learning landscape ecology-a practical guide to concepts and technique[M].New York:Springer-Verlag,2002:1-50.
[10]卢杰,郑维列.景观生态学课程教学方法探讨[J].西藏科技,2008(3):5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