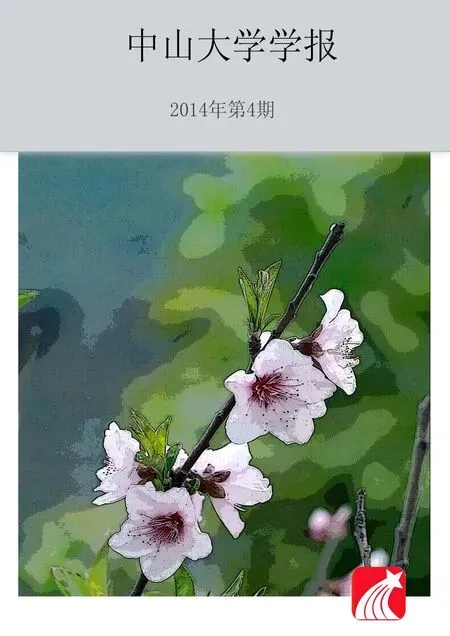论黄药眠小说《李宝三》的文学史意义*
林 分 份
在此前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中,黄药眠为研究者所青睐的小说作品,是其小说集《暗影》①黄药眠:《暗影》,香港:中国出版社,1946年。这部小说集收录了他于1939年至1947年发表的小说4篇,即《古老师和他的太太》、《县长》、《陈国瑞先生的一群》(此是文中正题,在小说集“目录”中则题为《陈国瑞先生和他的一群》)、《暗影》。中的短篇小说《陈国瑞先生的一群》。该作品最初发表于1939年2月18日重庆出版的《抗战文艺》第3卷第9、10期合刊上,主要描绘了抗战爆发之后,以陈国瑞为代表的国民党官员表面高谈抗战,实则醉生梦死、虚伪堕落的生活画面。据此,王瑶、唐弢、严家炎、钱理群、朱栋霖等文学史家,主要将其归入抗战时期以张天翼《速写三篇》为代表的讽刺小说序列,着重肯定它在“塑造反面人物形象”、“揭发抗战痼疾”、“侧重道德虚伪性的揭发”②参见王瑶《王瑶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卷第90页,唐弢、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3卷第137页,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5页,朱栋霖等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上册第278页。其中,朱栋霖等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将作品名字误写成《陈国瑞先生的一天》。等方面的特色。迄今为止,这也是学界对黄药眠的小说创作成绩的主要定论。
然而,从抗战爆发至新中国建立之前,除了以国统区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集《暗影》外,黄药眠还出版了另一部小说集《再见》③黄药眠:《再见》,香港:群力书店,1949年。此书收录了他在1942年至1949年间创作的小说5篇,即《再见》、《热情的书》、《淡紫色的夜》、《小城夜话》、《李宝三》。以及其他几篇未入集的短篇小说。这些篇章,在创作视野、思想主题方面,都比《暗影》集中的作品更为开阔,其表现手法也更为丰富和圆熟。尤其是小说集《再见》中的短篇小说《李宝三》,更是此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本文拟从《李宝三》入手,试图探讨这篇长期被现代文学研究者忽略的小说所具有的文学史价值,从一个侧面呈现抗战以来黄药眠小说创作的丰富性及其历史意义*实际上,就已经发表的作品来看,黄药眠最迟在1928年前后就开始了小说创作。此一时期的小说颇具“蒋光慈气”,计有《痛心》、《一个妇人的日记》两个单行本和《毒焰》、《A教授的家庭》等短篇小说。但此是另一话题,本文暂不涉及。。
一
小说《李宝三》约二万二千字,最初发表在1944年3月10日重庆出版的《文艺杂志》第3卷第3期,篇末标有“一九四三,十,七日脱稿”字样。作品以粤东韩江上游的人民去南洋谋生为背景,讲述了归来“番客”*黄药眠在《李宝三》篇末的“注二”云:广东韩江一带的俗话说往南洋是说“过番”,南洋回来的华侨俗话叫做“番客”。李宝三由风光无限到穷困潦倒直至死亡的故事。
小说原文共7节。第一节写李宝三从南洋回到家乡附城,穿着时髦,出手阔绰,成为受李氏族人尊敬、爱戴的番客。然而,不到半年,他的手头渐渐拮据,乃至无力置办过冬的保暖衣物。小说第二节借由另一位番客熊致祥之口,讲述了李宝三在南洋做工的种种经历。小说第三节则写李宝三的老婆病死了,他想去赌一份棺材本回来,可是赌输了,只能将老婆草草下葬。自此,李宝三的底细暴露了,成了族人眼中的“流氓赌棍”。小说的第四、第五节展现了作为小工和厨师的李宝三在生活中的诸多面向:他不仅深知各位熟客的性格脾气,而且能做中西菜点,使得小饭馆生意兴隆;他同情穷苦人,总是或明或暗地给乞丐们一点剩余的饭菜;他略通中医药知识,用干牛粪医好了一位外乡老婆婆的单烧症,从此成了穷人们的免费医药顾问;凡此等等。小说的第五节则写李宝三不惧人言,与一个被乡人视为“发花癫”的陌生女子恋爱、结婚,并高调享受“自由恋爱”的幸福生活。小说的第六、第七节则叙述了李宝三的再次沉沦及其最终结局:李宝三的第二个老婆不到一年也病死了,他意志消沉,再次堕入好赌的生活,乃至搬去跟叫花子们同住,每天半夜出去偷菜偷鱼卖钱度日;然而不久,他忽然消失了,三个月后,当他爬回家试图将仅剩的两间房子转让给道先叔(李道先)的时候,却受到了道先叔等人的辱骂和驱赶;第三天,李宝三被发现死在了他第二任老婆的坟上。小说的最后以小吃店的食客怀念李宝三所炒牛肉的“又脆又嫩”结束。
对于该篇小说,黄药眠自称“是写我们家乡的所听所闻”*黄药眠:《再见·作者自序》,香港:群力书店,1949年。。换言之,这是一篇忠实于作者家乡生活的乡土文学作品。在黄药眠写作《李宝三》的同一年,上官筝(关永吉)在《揭起乡土文学之旗》一文中就指出:“作家忠实于自己的生活,并认识了自己的生活,且能把握了自己民族的性格与特质,而写出来的文章,自然就是‘乡土文学’。”而鲁迅那篇“典型了中国国民的性格”且“更明确的显示了中国的社会”的《阿Q正传》,正是“乡土文学”的杰出作品*上官筝:《揭起乡土文学之旗》,上海《华文日报》第10卷第1期,1943年1月1日。。可以说,后来的“乡土文学”作家,在鲁迅《阿Q正传》的启发下,创造了一系列阿Q式的形象,如许钦文《鼻涕阿二》中至死都遭人歧视的鼻涕阿二,彭家煌《陈四爹的牛》中被人霸占了老婆和家产的猪三哈(周涵海),台静农《天二哥》中借着酒意欺负弱小的天二哥,王鲁彦《阿长贼骨头》中的惯偷阿长,王任叔《疲惫者》中因遭人诬告而沦为乞丐的帮工运秧,等等。这些人物的身份、经历和命运,都在一定程度上与阿Q相似,以至于张天翼认为:“我们中国现在的许多作品,是在重写着《阿Q正传》。”*张天翼:《论〈阿Q正传〉》,《文艺阵地》第6卷第1期,1941年1月。
就小说所写主人公兴衰浮沉的过程来看,李宝三这个人物形象,实与鲁迅的阿Q原型颇多渊源。首先,主人公原本都身份低微且穷困不堪:阿Q是浙江绍兴农村一个无固定职业的无产者,平时靠打零工过活;李宝三则本是广东韩江上游地区的一个乡下摊贩,每天挑着篮子卖麦芽糖为生。其次,从主人公的经历来看,他们都一度成为当地的“名人”:阿Q进了趟城,回来后发达了,一度因手头有丝绸杂货成为未庄人关注的焦点;而李宝三去了南洋,回来后变阔绰了,更因整天出去“办事”,成为大家尊敬的“番客”。再次,他们发迹的过程都不大光彩,最终再次潦倒:阿Q到城里去做贼发了财,而李宝三则从南洋借了一笔钱跑回来;由于后来都暴露了底细,从而都为当地人所冷落、提防。又次,他们潦倒、死亡的原因也颇为相似:阿Q是被极有可能的“本家”赵秀才所举报,说他参与洗劫赵家,因而被县衙抓捕并枪毙了;而李宝三的偷菜偷鱼则极有可能被同族的李道先父子所告发,甚或由此遭遇牢狱之灾,最后潦倒而亡。
不惟如此,小说《李宝三》借助主人公兴衰浮沉的过程,展现了粤东乡土社会的众生相。无论是绅士、文人、土学者,还是普通乡下人,小说通过描述他们对待有钱番客的眼光、态度和言行,揭示了城乡大众拜金、势利的心理。番客熊致祥在C城的大街上一走过,“在他后面就有不少的人闪着羡慕的眼睛……连在学校里读书的少女们有时也不免回过头来对这个财神投视一瞥多情的眼睛。”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绅士们的反应:
还有那些绅士,有些眨眨眼睛,有些用手指伸进鼻孔去挖了又挖,有些则故作镇静,把那个身子有规则地向左右摇晃,他们的态度虽各有不同,但有一件事情是他们大家都在心里共同努力的:那就是大家都在极力地用着自己生了锈似的迟钝的脑筋,设法来向这个财神贡献一些好听的说辞。
这个地方的文人和绅士,对金钱的崇拜几近于痴迷。其中有一位诗人,在一次宴会席上请求熊致祥给他的诗集捐印刷费:“只要我把你的名字写在我的诗的前面,你的名字也就和我的诗一样永垂不朽了。”最后这位诗人所得到的数目“虽然不过十分之一,但也够他感激涕零了”。而中年绅士徐秀文,则常常在刺探熊致祥的家世,盘算着要把即将高中毕业的女儿送给熊致祥做妾。他甚至为此早早地拟好了说辞,寻思着找个时间去跟熊致祥说:“熊先生,小女虽是中等程度,但能够有机会伺候你老先生,那她一定会觉得十分快乐而且会觉得骄傲的!”
对于金钱,普通的乡民又如何呢?小说一开头写李宝三“过番”回来给大家派发礼品、礼金的场景,对李氏族人的言语和心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绘:
“你知道,他送给道先叔多少?一个人就五百现钱的红包……”李宝三的远房堂嫂,风嫂子暗地里说,伸出五只手指。
显然的,李宝三的豪爽,很快就获得了一屋子人的尊敬。就是平素最看不起李宝三的李树明,一个中学毕业生,一向都是“阿宝三,阿宝三”叫个不了的,现在也不知不觉地把阿字缩了回去,而在“三”字下面凑上了一个“哥”字。
自然,李树明对他都如此客气,其他的人更用不着说了。每当李宝三穿着那套西装翻领出去的时候,于是“宝三哥”,“宝三叔”,“宝三伯”,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喊着,简直像许多虾蟆,张口就叫似的。
在众多族人眼里,这个原本卖麦芽糖的小摊贩阿宝三,已然成为李氏家族引以为荣的大人物。
小说在刻画李氏族人拜金心理的同时,也描绘出他们逐利弃义、罔顾亲情的一面。当李宝三穷困潦倒的时候,他们不仅未表同情,不予帮助,而且还施以各种冷遇与排斥:
从此李宝三再也不从大门出入了,他总是从小门口溜出溜进,大家看见他都把面翻了过去。把笑容藏了起来。甚至有些人,一看见他走过,就吐一撮口水,来表示他的厌恶。虽然在过去他也曾吃过李宝三锅子里的猪肉。
从此李宝三夜里回来,再也没有人替他开门了,在从前,他的老婆,还有些叔母,伯母,只要谁先听见,谁就会来开门。同时她们都知道,门一打开,她们的手里就可以接到什么。但现在谁也不来开门了,李宝三只得爬墙回家。
李道先先生甚至对同屋的人下着秘密的命令:“阿宝三,不务正业,以后你们东西要小心……”
此时,让李氏族人和众多乡邻亲近李宝三的理由,则是李宝三偷鱼偷菜贱价卖给他们的时候:“桥头的主妇们没有一个不知道关于李宝三的谣言,但没有一个人不抢着去买李宝三的东西。”“连任嫂子风嫂子都赶着要来买。有时为了便宜,还叫一二声宝三叔。”
不难看出,围绕在李宝三周围的这些人物,对于李宝三的遭遇,有着与《阿Q正传》中那些未庄“看客”相近的态度:阿Q周围的那些人,无论是赵太爷、假洋鬼子、王胡、小D和吴妈,对于阿Q的遭遇,没有一点阶级弟兄之间的友爱心,只把别人的痛苦当作笑料来加以鉴赏;而李氏族人、温姓邻居、小饭店的老板、食客等一帮人,对于穷困潦倒的李宝三,也加以白眼、嘲笑以及排斥,乃至在关键时刻冷漠绝情、落井下石。无论是阿Q的“看客”还是李宝三的“看客”,他们的内心麻木都有如鲁迅所说,是到了“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4页。的地步。1945年,乡土小说家许杰指出:“我理想中的乡村小说,应该是通过现代的科学精神,而提炼了乡村的落后意识,指示人生与社会的前途的。”*许杰:《论乡村小说的写作》,载1945年8月19日至27日《东南日报》(南平版)。就此而言,黄药眠的《李宝三》,当属于许杰所谓理想中的“乡村小说”亦即“乡土小说”的序列,更确切地说,是属于鲁迅所开创的现代“乡土小说”的序列。
二
谈及《李宝三》的创作,黄药眠宣称,它和另一篇小说《小城夜话》,主要“是写我们家乡的所听所闻,但当时立意也只求写出一些气氛和情调,并没有企图铸造出一些深刻的人物性格”*黄药眠:《再见·作者自序》。。虽然如此,就实际来看,小说《李宝三》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地方,仍然是通过叙述主人公兴衰浮沉的过程,塑造了李宝三这个具有复杂个性的番客形象。
李宝三本是附城当地一个每天挑着篮子出门卖麦芽糖的摊贩,8年前到南洋谋生,干过各种小工。据番客熊致祥说,李宝三“脾气不好,好赌,偷了老板的钱去赌博,给老板知道了赶了出来”。欧战爆发后,“听说他借了人家两千多荷盾,就这样跑回唐山去了!”然而回乡之后,李宝三不务正业,不仅终日沉迷赌博,而且输光家产,乃至沦为小偷,最终潦倒而亡。综观李宝三沉沦的过程,不难看出他有着坏脾气、好赌、不守信用、狡猾、浮夸、虚荣、世故等众多负面因素,称得上是一个不务正业的“流氓赌棍”。然而,李宝三的身上也有着诸多正面的特点:他尊老爱幼,为人豪爽,在“风光无限”之时,不忘给族里的老人小孩派送礼金或糖果;他聪明伶俐,清楚各位食客的性格脾气和用钱的大方或小气;他勤劳能干,善于做各种中西菜肴,深受顾客们的喜欢;他急公好义,救人于危难且不求回报;他富有同情心,经常关照乞丐和穷困户,还劝老板和老板娘积德;他乐天安命,能够坦然接受命运的转折……不难看出,在作者的笔下,李宝三称得上是个亦正亦邪、善恶并存的人物。
李宝三虽然去过南洋,但身上仍然保留着乡土中国普通人共有的某些特点:比如他一回来就给李氏家族的男女老少送礼物、派礼金,上演了“荣归故里”的一幕;比如他通晓世故,懂得去重点讨好李道先、李树明父子这两位家族里的伦理权威、学术权威;再比如他略通中医,用干牛粪帮别人治好了病,等等。然而,使得李宝三与众不同的,恰恰是他身上那些迥异于乡土社会普通人的面向。首先,李宝三回乡后,有钱却不务正业,整天沉迷赌博,即使“身家都赌了三副”,为李氏族人所鄙夷,他也不改恶习。其次,李宝三不守信用,从南洋借了钱跑回来,这本就让李氏族人难堪,而他沦落到小饭馆当小工,更是丢了李氏族人的脸,但他对这些都毫不在乎。此外,李宝三还有很多为普通人难以理解、接受的观念和行为:他认为人赚钱就是为了要花掉的,主张“积蓄到差不多的时候,就通通把他花光”;他追求洒脱,不重视个人名声,宣称“我又不要人家替我起牌坊……”他不顾李氏族人反对,坚决跟一个被湖墟王家赶出来的“发花癫的女人”结婚……
李宝三的这些观念和行为,对处于乡土社会中的普通人而言,称得上是“异端”。而这些“异端”的来源,实与他在南洋8年所获得的异域经验密切相关。作者在小说后面的“注一”中指出:“广东韩江上游,赴南洋谋生的人极多,他们一去八九年或一二十年不等,因此他们回到家里也就带回来了不少南洋殖民地的风情。”韩江上游自古地薄人穷,为求发展,不少人只得抛妻别子,远涉重洋到海外谋生,谓之“过番”。但过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是筹措路费,或典当,或借贷,或变卖物件,有的则被迫卖身,即“卖猪仔”,到南洋后白做3年来赎身。如此情形,诚如粤东山歌所唱:“家中贫苦莫过番,过到番邦更加难,若系同人做新客,三年日子样得满。”*佚名:《过到番邦更加难》,《粤东客家山歌》(内部资料),广东省梅县地区民间文艺研究会、梅县地区群众艺术馆编印,1981年,第153页。同样是过番,有钱的番客可以自己做生意,而没钱的却只能给人担锡泥、割橡胶,工作繁重,生活艰苦,还要受当地人的歧视。不仅如此,由于身处异乡,一遇动乱,他们随时都有被抢劫、杀害的危险:“锡山州府纷纷乱,几多强贼抢人钱。有福之人银抢走,毛福之人命相连。”*佚名:《过番》,广东省兴宁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兴宁文史第30辑·粤东之风(罗香林专集③)》,兴宁市城东印刷厂,2006年,第197页。
据此不难推知,8年前就“穷得人嫌鬼恼”的李宝三到达南洋后,其生活遭遇的困厄与艰险。而这样的过番经历,对他的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念显然不无影响。当李道先劝诫李宝三不要再赌博时,李宝三说:“唉,道先叔,出门人生活寂寞,天下哪里有那么多的孔夫子呀。”而当别人质疑他在外头嫖赌过日子时,李宝三回答说:“出门人哪个不嫖不赌!有了两个钱,不快乐快乐又干什么呢!”很显然,李宝三的好赌、堕落,在他自己看来,多半缘于“出门在外”的境遇:流落异乡的寂寞感,加上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漂泊处境,难免让人容易产生诸如“人生苦短不如及时享乐”的消极念头。
但另一方面,李宝三在南洋所经历的人生苦境乃至大风大浪,使得他面对命运转折和生活困顿,有着良好的心态。当李宝三从无比风光的番客沦落为小饭馆的帮工而遭人讥笑时,他如此安慰自己:“乡下佬,笑什么。笑我的鸟!有钱当番客,没有钱就给人家打工,这也用不着你们笑。”这种于无奈中夹杂着的傲慢,也与李宝三去过南洋、见过世面所产生的优越感有关。换言之,正是8年的过番经历,使李宝三获得了有别于乡土中国普通人的观念和视野。当李树明问他在外头做的是哪行生意时,李宝三的回答是“义和隆……你知道,替大头家管钥匙……钱箱里全是金银宝贝,荷盾……”或许正因为见的钱多了,李宝三养成了出手阔绰的习惯,“有了钱就只会花,不像他们那些吝啬鬼!”而当李树明又问他准备在家乡做什么事业时,他回答说“去见县长”,并宣称“我是华侨会的会长”,“中国地方大,矿又这么多,最好的办法是批一块地方给我,我替他们开矿”。虽然事后证明李宝三所说的这些大都是假话和空谈,但就是如此“一知半解”的见识和想法,也已折射出他对乡土社会的经济模式、价值观念的疏离以及对现代社会的商业组织、采矿工业的认同。而这,也正是过番归来的李宝三与彼时乡土社会普通民众的一大差别。
不惟如此,过番归来的李宝三,头脑中有着迥异于一般乡下人的审美意识、浪漫态度和婚恋观念。当他给过路的陌生女子送去食物后,女子吃完食物,对着他唱起了山歌:“风吹竹叶好青青,风吹阿哥真有情,竹叶不怕风吹打,有情难得耐心人。小溪外面是黄河,阿妹难得有情哥,莫说阿妹颜色好,山歌难得有人和。”见此情景,旁人都艳羡李宝三运气好,碰见了“发花癫的女人”,唯独他却对山歌赞赏不已:“唉,他妈的,唱是的确唱得好!”不仅如此,李宝三还从山歌中听出了爱的召唤,因而在第二天早上,他就把这个女子带回家,让她成为了宝三嫂。而此时的他,“面向着朝阳,带着一重欣悦的光辉”。在爱情光辉沐浴下的李宝三,也与以前稍微不同了:“衣服也穿得整洁些,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斜靠右边分成了一条很清楚的发路。炒菜时运用铲子的手腕,也格外灵活似的,对于客人的招呼,也特别的周到。”此外,每到黄昏,工作完毕,他就穿戴整齐,带着宝三嫂到河沿边去散步,或者碰见有什么晚会,或游艺会,“他一定要多方设法,向学生们找两张票子。在游艺会开幕前一个钟头,他就穿好了反领西装,白色衬衫[,]戴上帽子,欣然的偕着宝三嫂一同到会场上去了。”李宝三如此庄重的态度,显然也与他在南洋的阅历有关。据晚清诗人黄遵宪的《番客篇》所载,虽然多数在南洋的番客仍然保留着大陆的衣着样式,所谓“披衣襟在胸,剃发辫垂索”。但在婚宴、喜庆等重要场合,却也能入番随俗,盛装出席:“蕃身与汉身,均学时世妆,涂身百花露,影过壁留香。”*以上参见黄遵宪:《人境庐诗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87、84页。李宝三着装隆重地与宝三嫂约会,乃至一起参加晚会和游艺会,正显现出其在浪漫意识、婚恋态度方面对于南洋习俗、异域风情的认同。
在旁人眼里,彼时李宝三和宝三嫂的幸福不仅高调,而且公然逾越了当地人的禁忌。“有时,月亮清,于是竹林下,草丛里,山冈上,河沿边,不时浮起了女人的歌声。”“到了散会回来的时候,人们还看见他们手挽着手靠得很紧呢!”如此恋爱场景,对于那些头脑中充满着“女红针业纺织,鲜抛头露面于市廛”*参见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2页。的保守观念的当地人来说,自然是难以接受的。因而,就有李氏族人警告李宝三,说宝三嫂来历不明,要小心吃官司,而小饭馆的老板也批评他的恋爱“做得太离题”,“有伤风化”。李宝三对此坚决给予了反击:“这是恋爱的事情,谁也管不着!在外头,到了夜里,那(哪)一株椰子树下没有人唱山歌……所以我说中国人学文明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外国人。”面对乡人的干涉和指责,李宝三再一次以来自“外头”的见识,展现了其浪漫意识、婚恋观念中所具有的异域情调乃至超凡脱俗的一面。而读者自此也不难看出,虽然李宝三在经历、命运方面与“鲁迅派”乡土小说中的阿Q、鼻涕阿二、猪三哈、天二哥、阿长等人物形象颇多相似,但与他们因“缺乏平等自由观念和人权意识”而演绎的人生悲剧*参见余荣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流变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58页。相比,显然有着巨大的差别。换言之,有着种种缺点的李宝三,却也因其乐于扶危济困的品行,来自异国他乡的经历和视野以及颇具浪漫意识、懂得男女平权、捍卫恋爱自由等各种思想和行为,得以与上述现代乡土小说中的“麻木者”、“落伍者”的形象区别开来。
1948年,社会学家费孝通在论述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精神差别时,援引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西方陆沉论》(今译为《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关于西洋曾有亚普罗式(Apollonian)和浮士德式(Faustian)两种文化模式的观点,指出:
亚普罗式的文化认定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但是人连维持它的力量都没有,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
在费氏看来,“乡土社会是亚普罗式的,而现代社会是浮士德式的。这两种精神的差别也表现在两种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生活里。”乡土社会容不下浮士德式精神的存在,“它不需要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决定的,它更害怕社会关系的破坏,因为乡土社会所求的是稳定。”*以上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45—49页。借此或许有助于进一步探讨李宝三与李氏族人之间的差异。与李氏族人等普通乡下人相比,李宝三脾气很坏,经常变换工作,热衷赌博性刺激,追求及时享乐,钱赚到一定程度就会花光,主张“自由恋爱”……总之,追求生活上的激情、变化乃至冒险,无疑是李宝三生命的主要形态。而这种颇具异域情调、“浮士德式”的生命形态,对于乡土中国里讲究传统道德、秩序的李氏族人乃至普通人而言,显然是不容存在的“异端”。由此也就不难明白,无论是作为有钱的番客,还是作为“流氓赌棍”,李宝三何以一再为李氏族人、温姓邻居等怀疑、嫉妒乃至排挤了。
1935年,鲁迅在评价“乡土文学”时,曾含蓄地指出蹇先艾、裴文中、许钦文、王鲁彦等乡土作家的小说中,“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5页。。与上述不同的是,黄药眠的《李宝三》所展现的主人公令人费解的嗜赌成性、善恶并存的个性品质,亦正亦邪的人生哲学以及超凡脱俗的浪漫意识和婚恋姿态,都使得这篇小说超出了“鲁迅派”乡土小说的范畴。换言之,在鲁迅评价“乡土文学”难有“异域情调”约略十年之后,黄药眠的小说《李宝三》成功塑造了在性格、情感、思想、行为诸多方面都颇具“异域情调”的李宝三的形象,不仅开拓了读者的心胸,也开拓了现代乡土小说的创作视野和表现空间。
三
在客家文学史上,黄药眠是被誉为与郭沫若、李金发齐名的三位中国现代“黄钟大吕”式的客家诗人之一*谭元亨:《黄药眠:清名上帝所忌》,见李克定:《黄药眠评传》,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但有关其小说创作中的客家元素和地方色彩,至今却无人论及。就题材内容而言,小说《李宝三》无疑是一篇充满客家民系元素和粤东地方色彩的作品。比如,故事的发生地韩江上游,即今天的梅州市,古称嘉应州*韩江唐称恶溪,后为纪念韩愈驱鳄又改称韩江。由发源于福建省武夷山南麓的支流,与发源于广东省陆河县与紫金县交界的另一支流,在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三河镇的三河坝汇合之后的河段,称为韩江。故这里的韩江上游,乃是今天的梅州市一带,即古代的嘉应州及其周边。,本是粤东客家人的聚居地;而小说所涉及的到南洋谋生的过番经历,也属当地客家人的生活内容之一。再比如,小说中所涉及李姓、温姓两个家族,正是粤东客家人常见的大姓;而写到“发花癫的女人”时,更是用了八句客家山歌来表达她对李宝三赠予饭食的感激之情。此外,小说中的赌徒李宝三,在现实中有其原型。在至今流行的粤东民谣和客家山歌中,有多处涉及讽谏或劝诫赌博的篇章,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赌徒吴三保的故事。粤东民谣曰:“赌博好唔好,问过吴三保,亲手造条万盛街,亲手卖到了。”吴三保是粤东兴宁县人(今梅州市辖下),因以赌博为业,导致破产,其故事也被编入客家山歌《十望夫》中,被人们广为传唱:“三望亲夫莫赌钱,十个好赌九个难,赌博造街吴三保,三保本身卖到完。”*参见《粤东客家山歌》(内部资料),广东省梅县地区民间文艺研究会、梅县地区群众艺术馆编印,1981年,第154、156页。
小说《李宝三》虽然主要写的是李宝三兴衰浮沉的过程,却也从侧面呈现了粤东番客回归故里后的某些现实遭遇。客家人到南洋谋生,大多处境艰难,而少数人在艰苦创业之后,即使回归故里,也仍然可能受尽乡人刁难、盘剥乃至官府的迫害。黄遵宪的诗作《番客篇》,对此就有确实的描述:
岂不念家山,无奈乡人薄。一闻番客归,探囊直启钥。西邻方责言,东市又相斮。亲戚恣欺凌,鬼神助咀嚼。曾有和兰客,携归百囊橐。眈眈虎视者,伸手不能攫。诬以通番罪,公然论首恶。国初海禁严,立意比驱鳄。借端累无辜,此事实大错。事隔百余年,闻之尚骇愕。谁肯跨海归,走就烹人镬?*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第87页。
而现实中,归来番客的艰难境遇,直到三四十年代,在相关报刊杂志的报道中,仍然屡见不鲜*参见佚名:《归侨仍视潮汕为畏途》(《华侨半月刊》第76、77期合刊,1936年1月),佚名:《“番客”耶?“难民”耶?今日暹罗之归侨》(《南洋报》,1948年2月17日)。。
在小说中,李宝三的“荣归故里”,不仅为邻居温姓后生所怀疑,也遭到了李氏族人的嫉妒、刁难乃至迫害。小说第一节就刻画了李氏族人对李宝三的心理不平衡、嫉妒等复杂心态:“不过日子一长久,背地里的闲话就多了起来,比方李宝三每天都是大鱼大肉的落锅,这就使得那些吃咸菜豆腐的人有点眼红。李树明的父亲道先先生就为此而大不高兴。”不仅如此,嫉妒、贪婪甚至在后来成为李氏族人报复李宝三的心理动因。风嫂子有一次没有吃到李宝三的猪肉,对此怀恨在心,因此后来在羞辱、驱赶第二任“宝三嫂”时,“她的声音特别放得那么高,故意使那个宝三嫂听见”。而为了霸占李宝三的房产,平时最受族人尊敬的李道先,也露出了虚伪、贪婪的真实嘴脸:“李树明早已同他的父亲一样打定了主意,要把阿宝三的那两间空房子拿去卖,这事道先叔于经过一番假装的沉吟以后,他就决定放弃阿宝三每个月所孝敬的蹄胖,而把假的契纸都做好了。”对于李宝三消失(或说被警察逮捕)3个月的缘由,小说虽然没有直接点明,但李道先父子,显然是最有可能的肇事者(告密者)。当李宝三爬着回家,寄望于将两间房产转让的时候,遭到了李道先“义正词严”地呵斥:
“阿宝三,你今天还有面目回来见你的祖宗……你做了贼,吃了官司,做了叫花子……你立即替我滚,不然我就叫警察来把你拉回到监房里去。”
“唔,你还要房子……试问你还有什么资格,回到李家来……见我们李姓的祖宗!你给我快滚。”道先叔完全不像吃蹄胖时那样善良了。
结果,在李道先道貌岸然的指责和李氏族人的合力驱赶下,李宝三被迫逃离了自己的家,放弃了他寄以厚望的房产,也最终走向了死亡。
无独有偶,在《李宝三》发表3年之后的1947年,广东籍作家陈残云的中篇小说《南阳伯还乡》由香港南桥编译社出版,该小说讲述的也是归来番客的故事:珠江三角洲的乡民罗闰田在年轻时到南洋艰辛创业,事业有成后带着女儿“落叶归根”,试图造福乡里,却遭到各种地方势力和官府的纠缠、敲诈和迫害,最后不得不再度背井离乡。归来番客的悲剧,又一次被文学作品所演绎。就实际来看,《李宝三》与稍后于它的《南阳伯还乡》,都称得上是反映归侨生活的优秀小说。然而时至今日,却没有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或地方文学史,曾对黄药眠的《李宝三》作过相应的介绍和评价,这实在是个不小的遗憾*比如,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3卷第4章《华南作家群》中,用一节介绍了陈残云及其《南阳伯还乡》等小说,而对于黄药眠,作者只是笼统地将他作为抗战胜利后寓居香港的作家之一,此外并未提及黄药眠的小说创作;而罗可群《现代广东客家文学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在提及黄药眠时,仅将其作为1927—1949年间“时代曲”的代表诗人给予介绍,对其小说创作也是只字未提。。
对于木刻艺术和文学创作,鲁迅曾指出:“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鲁迅:《致陈烟桥》(1934年4月19日),《鲁迅全集》第13卷,第81页。可以说,书写具有地方色彩的人物和生活,正是黄药眠《李宝三》的鲜明特色,也是这一时期他的相关小说的整体取向。而这实与作者彼时的文艺主张和自觉实践密不可分。1939年10月底,在桂林文协分会展开的“文艺上的中国化和大众化的问题”讨论中,黄药眠指出,中国化的问题本质上也就是大众化的问题:“假如一个作家,他能够随时留心到最大多数的中国人的生活,把他们的生活态度,习惯,姿势,和语言,加以选择和陶炼,如实地写了出来,那么他这个作品一定是中国化的,同时也是大众化。”有鉴于此,他认为,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的文艺作品醉心于模仿欧美作家的手法,所反映出来的真正中国人实在太少了,“因为它们所反映出来的,已并不是中国土生的农民,而是在都市里沾染了一些洋货的知识分子了”。而要创作出真正中国化和大众化的伟大作品,在黄药眠看来,作家必须深入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必须“纯熟的运用土生的中国语气”,“更多的应用地方土语”,或者“以目前所流行的普通话为骨干,而不断地补充以各地的方言,使到他一天天的丰富起来”*黄药眠:《中国化和大众化》,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1939年12月10日。。
黄药眠不仅如此主张,而且付诸创作实践。在比《李宝三》早约一年半发表的小说《一个老人》*黄药眠:《一个老人》,《文艺生活》第3卷第1期,1942年10月15日。中,作者用来表现人物的语言就已经显露了地方色彩。小说中描写傅叔公神情和语言的句子如:“他的眼镜呆呆地视着那地上冒烟的烟屎”,“(傅叔公说)让他们有财有宝的去搬!他们的命都是金枝玉叶,我们的命都是猪屎狗屎!”这里的“烟屎”、“有财有宝”、“猪屎狗屎”正是粤东一带的土语。而比《李宝三》早4个月发表、后来也收入小说集《再见》中的《小城夜话》*黄药眠:《小城夜话》,《文学创作》第3卷第2期,1944年6月。,也不乏这样的例子:
“我今天还有点手尾……”(洪子良说)
“唔,这样无思无想的人!”陈老板斜乜着他,低声骂道。
“想不破啦,嘻嘻,女人们就是这样的……”(刘先生说)*“手尾”在现代粤语中用来表示尚未完成的、收尾性的琐屑工作;“无思无想”意即没有思想;“想不破”意即想不开。
这里的“手尾”、“无思无想”、“想不破”等,不仅展示了人物所处地域的特点,也流露出其言语里面的立场和态度。
而在小说《李宝三》中,除了凸显人物身份的“番客”、“过番”等当地俗语外,作者在描写人物对话时,采用地方俗话、土语的现象尤为突出。比如:
“义和隆……你知道,替大头家管钥匙……钱箱子满是金银宝贝,荷盾……”阿宝三抛浪头,就把心目中认为最阔绰的职业,拿来加在自己的身上。
“那有什么,我又不要人家替我起牌坊……”(阿宝三说)
学生们看见了,都会笑他“李宝三,你这样好心,你死后金童玉女会带你上天堂……”
“现在做长辈的也太没有牙根,如果是从前曹叔公还在的时候,唔,那她就休想进我们李家的门,一百个屎扫帚来铲……”风嫂子亦高声附和着。
“唉,现在这样的乱世,还管得那么许多,只求阿宝三有职业,不会在家里偷鸡吊狗,也就罢了……”(道先叔说)
这里的“大头家”意即大老板,“抛浪头”意即吹嘘自己或吓唬人以显示自己威风、出风头,“起牌坊”意即立牌坊,“好心”意即好心肠,“没有了牙根”意即规矩、态度等不严厉,“屎扫帚”指专门用来清理粪便的扫帚,“偷鸡吊狗”意即偷盗禽畜、不务正业。以上这些无论是单词还是短语,都属于地方方言的习惯说法,放在对话内容中,无疑使得人物的言语、神态、思想具有粤东一带原生态的乡土气息和生活氛围。对此,黄药眠在小说篇末“注一”中也着重指出:“在直接引用语里面,在必要时,也采用了一些土语,但作者并没有想把许多别的地方的人所难于了解的土语也都一律掺杂进去。因为有些土语,可以用国语代替,而其意义完全一样的,也就无需乎用土语了。”
值得注意的是,或许是为了增强作品中语言的土味,这一时期黄药眠的个别小说如《县长》、《一个老人》等,在表现人物的动作、语言、神态方面,甚至出现了不合汉语语法的情况:
县长太太起身想去到茶几上倒开水。(《县长》)
“那就让我来去罢!”吴秘书自告奋勇。(《县长》)
(傅叔公说)“现在的富人家,真是越来越不懂事体!越来越没有规矩,接到封皮就是信,也不同人家商量,好像日本人已经走到大门前一样,马上乱烘烘[哄哄]的,全副身家搬去走!”(《一个老人》)
傅叔公的老花眼睛才一□□那个被人叫做寿嫂子的已经站在他的面前了,她胖肥胖白的躯体有着一股中年妇人的臃肿。(《一个老人》)
这里的“想去到”、“来去”、“搬去走”、“胖肥胖白”,无论是表示动作还是状态,都不是标准的汉语语法,而是方言土语的用法,作者将他们用在描写小说人物上面,正是为了展现这个地方的“气氛和情调”*黄药眠:《再见·作者自序》。。
不难看出,在人物对话中使用方言土语,已然成为这一时期黄药眠小说创作中的某种整体趋向,而这也印证了作者此前的主张:“创造文学民族形式上的中国化大众化的问题不应该只当成问题来讨论,而应该把它看作为一种运动,作为创作的实践。”*黄药眠:《中国化和大众化》,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1939年12月10日。或许,正是居于此种自觉与实践,黄药眠在《李宝三》等小说中对“地方色彩”的呈现以及对方言土语的运用,在某种意义上,已然开启了40年代“华南方言文学运动”的先声*有关40年代“华南方言文学运动”的论述,可参见王丹、王确《论20世纪40年代华南方言文学运动的有限合理性》一文,《学术研究》2012年第9期。。
四
总体而言,黄药眠的小说《李宝三》以欧战为背景,借由李宝三兴衰浮沉的故事,书写了战争中粤东侨乡人民的生活、心理和社会众生相。只是,与30年代乡土小说追求农民群众、集体力量的展示以及抗战爆发以来乡土小说追求反抗意识、阶级斗争等实用性和政治性的美学原则相比,小说《李宝三》所塑造的主人公,不仅不是一个进步者、反抗者的形象,而且是一个有着诸多缺点和复杂个性的赌徒形象。换言之,撇开作品发表的时代背景不谈,李宝三与许杰《赌徒吉顺》中的吉顺、刘贝汶《赌徒别传》*许杰:《赌徒吉顺》,初载《东方杂志》第22卷第23期,1925年12月;刘贝汶:《赌徒别传》,初载《文艺春秋》第6卷第6期,1948年6月。中的水郊等,堪称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具有典型意义的赌徒形象。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李宝三与吉顺、水郊等赌徒相比,看似相同的嗜赌如命中却有着明显的区别:吉顺越赌越输,由于扳本心切,甚至准备把自己的妻子典给别人生孩子,以换取赌本;水郊则输光了其父留下的家产,为逼迫母亲把仅剩的菜园卖出去,甚至用柴刀砍伤了她,以至于面临牢狱之灾。在吉顺、水郊那里,不断地试图扳本,却又不断地赌输,内心嗜赌的魔鬼一直推着他们往前走,而自始至终他们的心中也只信奉一个上帝,那就是金钱。而在李宝三这边,对于自己的嗜赌,他十分忌讳,每当有人和他提起赌博话题的时候,他都不愿意别人再问下去。此外,李宝三虽然好赌,却并不奉金钱为上帝,其乐善好施的品德,平等、浪漫的意识及其“挣钱是用来花”的潇洒态度,更远非吉顺、水郊等赌徒所能比。
尤为重要的是,李宝三并非一味地沉迷赌博。在输光家产后,面对欧战背景下日渐窘迫的生活困境,他也努力过、抗争过。第一任老婆死后,李宝三到小饭店当小工和厨师以养活自己。娶了第二任老婆后,他一度“为了这女人戒了酒,也戒了赌!”由此过上一段虽仍贫穷却堪称幸福的生活。而第二任老婆死后,他也没有放弃,希望有人借他一笔钱来开一间小伙食店,甚至有过去当“革命家”的念头。当家里所有的东西卖光后,为了过日子,他甚至搬去与乞丐同住,并干起了偷菜偷鱼的勾当。经历牢狱之灾后,他爬着回家,仍然寄望于将两间房产卖给李道先以换几个钱度日……总之,李宝三穷困潦倒直至死亡的过程,正是其面对生活、命运不断抗争的过程,也是其与吉顺、水郊等赌徒最为本质的区别。
1936年,茅盾在一篇题为《关于乡土文学》的文章中指出:
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一个只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蒲(茅盾):《关于乡土文学》,《文学》第6卷第2号,1936年2月。
茅盾在此强调的是,衡量“乡土文学”价值的标准,并非取决于作品对“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而是取决于作者是否“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或曰深刻的人生体验和生活感悟,由此展现那片土地上的人“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不难看出,小说《李宝三》所写李宝三从摊贩到番客,再从番客到赌徒、小偷直至死亡的兴衰浮沉的过程,正是人性本能、求生欲望所驱使的对于生活的抗争过程,也就是茅盾所说的“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不惟如此,李宝三在穷困潦倒之时仍能保有古道热肠,坚持乐善好施,并且大胆追求幸福,更是折射出令人惊叹的人性光辉。在这个意义上,同样是书写赌徒或者破产者的命运,与许杰《赌徒吉顺》、刘贝汶《赌徒别传》、王鲁彦《阿长贼骨头》、彭家煌《陈四爹的牛》、王任叔《疲惫者》等现代乡土小说相比,黄药眠的《李宝三》显然具有了更为深邃的思想内涵和更为高远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