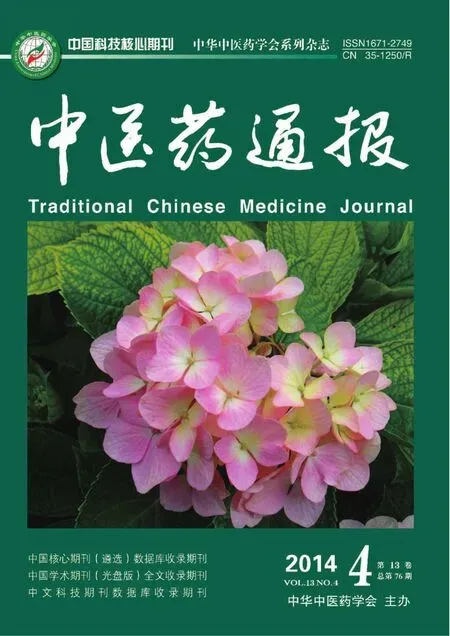乌梅丸加减治疗不寐验案一则※
● 王潇永 王兴臣
乌梅丸加减治疗不寐验案一则※
● 王潇永1王兴臣2
本文通过对随师临诊一则的理、法、方、药的分析,阐述了乌梅丸在治疗厥阴证不寐中的作用机制,并证实了从六经论治不寐的可能性,开拓了中医治疗不寐的新思路。
经方 不寐 厥阴证 乌梅丸
不寐又称失眠,是临床常见疾病,使无数患者苦不堪言。医家历来多从郁火、痰热、心脾两虚、心胆气虚、心肾不交等方面论治。近年来,许多中医研究者将伤寒六经辨证与不寐加以联系[1],从另一角度诠释不寐的病机,拓展了中医治疗不寐的思路[2],其中从厥阴证论治不寐[3]令人耳目一新。《伤寒论》第326条文曰:“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从字面上看,这条厥阴证总纲似乎与不寐没有关系,但临床上,阴阳复盛,寒热错杂的病机却体现在很多不寐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的身上。导师王兴臣教授擅用经方调治不寐病,尤其在乌梅丸的使用上可谓独具匠心。下为随师临诊一得。
1 验案举例
患者姜某某,男,67岁,已婚,退休。2014年2月6日上午初诊,自述前夜12:30左右尖叫惊醒,醒后心慌,胸中烦热,眩晕,耳鸣,口渴欲饮,手足逆冷,肢体颤动。舌质暗,苔厚腻,脉滑。患者不寐十余年,规律服用“百乐眠胶囊”早晚各4粒,遇事易时时思虑,常有郁郁不舒之感。辨证为不寐(厥阴证),方用乌梅丸加减。药用:乌梅45克(醋浸),黄连6克,黄柏6克,人参12克,当归9克,桂枝9克,细辛3克,炮附子9克,川椒3克,远志12克,珍珠母30克,茯神15克。7剂水煎温分服。
二诊:2014年2月20日复诊,述初诊服药后效果较好,虽仍有不寐,但不惊醒,平时胸口烦热,时有眩晕、耳鸣,且近几日肛门隐有急坠感。舌质红,苔厚腻,脉滑。处方:上方黄连、黄柏量加至各9克,夜交藤30克。7剂水煎温分服。并嘱患者放松心态,勿思虑太过,勿事事追求完美。
随访患者病情向愈,多年不寐症状逐步缓解。
2 讨论
柯韵伯曾言:“乌梅丸为厥阴之主方,非只为蛔厥之剂也。”之所以说乌梅丸为厥阴病之主方,是因为乌梅丸的组方方义极为贴合厥阴病病机。方以醋泡乌梅为君,乌梅本为酸性,归肝、脾、肺、大肠经,以醋浸泡益其酸味,引诸药入厥阴肝经。《伤寒论》第337条云:“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由此可知,厥阴证的病机为阴阳气不顺接,中医认为:阳入于阴则寐,阳出于阴则寤。厥阴证寒热错杂,阴阳不相顺接,使阳不入于阴而不寐。乌梅丸方中乌梅、细辛、蜀椒、附子、干姜、桂枝、当归七味药性温热,黄连、黄柏、人参三味药性寒凉,全方温药祛寒为主,连、柏清里热、顾阴气为辅,使被郁之阳气得解,阴阳之气顺接,而不寐自愈。
本案患者平素舌苔厚腻,脉滑,显为痰湿血浊体质,且年老肾衰,母病及子,累及肝阳。时常因事弗郁,肝失条达,郁而化热,渐成水寒木郁,寒热错杂,证属厥阴。《伤寒论》第328条曰:“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言明厥阴证欲解时即凌晨1时至上午7时,验案中患者自身阴阳复盛未能达到平衡,于凌晨1时之前突然发作,郁阳化火上扰心神,惊醒心慌,心中烦热,口渴欲饮,肝火引动引动体内痰湿血浊上蒙清窍致眩晕、耳鸣、肢体颤动,而又因肾阳亏虚见手足逆冷之寒象。四诊合参,辨为不寐厥阴证,以乌梅丸助阳解郁,兼清里热,去干姜防助热太过,加远志、茯神、珍珠母,化痰定惊、宁心安神,遂使诸症得缓。
厥阴证病情复杂,寒热并具,阴阳复盛,寒进则热退,热进则寒退,《伤寒论通俗讲话》中说:“病至厥阴,阴尽而阳生,由于正邪斗争有胜负,故其病变有厥热进退的机转。”[4]复诊时患者自述胸口仍有烦热且肛门下隐有急坠感时,使人联想到《伤寒论》341条:“伤寒发热四日,厥反三日,复热四日,厥少热多,其病当愈。四日至七日,热不除者,其后必便脓血。”即在乌梅丸的药力下,厥热胜复略过,使患者出现“热不除”的症状及“便脓血”的征兆,故加大寒凉药物黄柏、黄连的用量,调节阴阳,另加夜交藤以改善睡眠。
3 小结
本案生动展示了厥阴证阴阳复盛的进退过程,验证了张仲景对于厥阴病的多项论述,也为不寐的六经辨证论治提供了可信的临床依据。从这则验案中可以看到,厥阴证不寐虽然并不是典型的乌梅丸证,但其“消渴”、“心中疼热”的症状符合厥阴病提纲证,病机相同,治法相同,正如刘渡舟老先生从《伤寒论》小柴胡汤证“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得到启发,提出“抓主证”这一临床思维,实际上也体现了中医“异病同治”思想。同样,乌梅丸也不仅仅局限于《伤寒论》338条的“蛔厥证”,由于其组方的精妙,适用的范围更加广阔,临床上除治胆道蛔虫及久痢外,得其立法立方之旨,可广泛应用于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妇科、泌尿系统、五官科、肿瘤及神经科等涉及厥阴寒热错杂及厥阴感寒诸疾的治疗[5]。总而言之,仲景六经辨证博大精深,经方立意深刻,在临床实践过程中,我们应在继承基础上,大胆创新,辨准病机,活用经方,从而为患者祛除病痛,为中医发展做出贡献。
[1]张毅之,王 评.伤寒论六经辨治失眠探讨[J].江苏中医药,2010,42(9):1-2.
[2]李巨奇.失眠症伤寒六经辨治规律探讨及临床研究[D].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2011:1.
[3]李智文.加味乌梅汤治疗厥阴证失眠临床疗效观察[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3.13-15.
[4]刘渡舟.伤寒论通俗讲话[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152.
[5]周 贤,王光耀.乌梅丸的临床应用研究[J].中医学报,2009,24(145):122-125.
医论
阴阳升降论
天地之道,阴阳而已矣。阴阳之理,升降而已矣。自开辟以至混沌,一大升降也。小儿一岁有一岁之升降,一日有一日之升降,人身之道亦然。以一岁言之,自冬至一阳生,以至芒种而此阳之升极也。自夏至一阴生,以至大雪此阴之降而极也。所谓一寒一暑,岁序行焉'一岁之升降也,一日之内,子半而阳生,寅卯而日出于天阳之升也。午半而阴生,酉戌而日入于地阴之降也,所谓日往月来而晦明成焉。一日之升降也,考之先天,八卦自震而乾,为阴之升,由巽而坤,为阴之降。大圆图之自复而乾自垢而坤,无不若合符节。人与天地为一,少而壮,壮而老。一大升降也。小而日兴夜寐,一日之升降也。气出而呼,气入而吸,一息之升降也。昔古圣人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其与天地之阴阳升降,无少差谬,故阴阳不能犯而寒暑莫能侵。至庸甫者流,外为风寒所逼,内为色欲所伤,一身之内,非阳伤则阴损,阳伤者不升,阴损者不降。不降不升而生生之机息矣。病之纷然杂出者,可胜道哉。神农氏出,悯人民夭枉,辨药性以夺造化微权,嗣后岐黄传《内经》,以及历代名医咸有著作,而其大要皆以辨药性之阴阳,以治人身之阴阳,察药性之升降,以调人身之升降而已。故经云:调气之方,必别阴阳。阴病治阳,阳病治阴。又云: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又云: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为圣度。夫所谓调治阴阳而和之者,即其因病立方。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所利之大法也。故吾人业医,必先参天地之阴阳升降,了然于心目间,而后以药性之阴阳,治人身之阴阳,药性之升降,调人身之升降,则人身之阴阳升降自合于天地之阴阳升降矣。
(摘自清·芬余氏·《医源》)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项目(子课题)——山东省中医药科技发展计划、山东中医药管理局重点项目(No.2013Z003-4)
1.山东中医药大学2008级七年制硕士研究生(250001);2.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5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