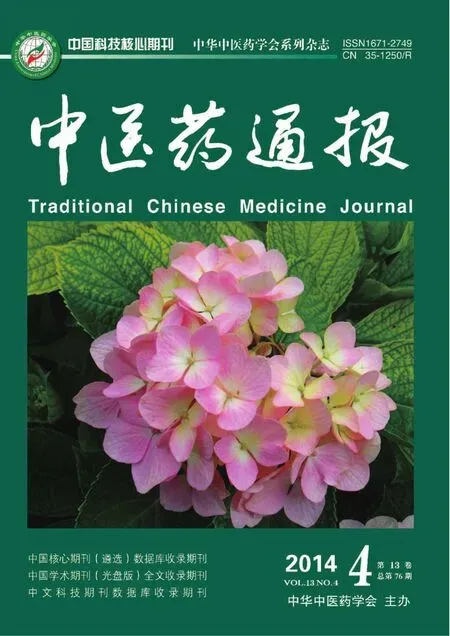魏晋南北朝医学与《金匮要略》论心痛病的比较
● 张志峰
魏晋南北朝医学与《金匮要略》论心痛病的比较
● 张志峰*
魏晋南北朝上承东汉之末,下迄隋初,名医辈出,医著繁富。就心痛病病机、证治而言,魏晋南北朝医学所论与《金匮要略》相较,病机阐述以继承为主、亦有补充,证候描述传承中有发展,治疗方法继承中尤其着重创新。通过二者所论的比较,古代对于心痛病的因机证治体系较为完整地展示出来,对于当今诊治该病不无裨益。
心痛病 金匮要略 魏晋南北朝医学
《伤寒杂病论》成书于东汉末年,不久即毁于兵燹,其中伤寒部分经王叔和编次,得以完整流传至今;杂病部分(后世谓《金匮要略》)则隐而未彰,至北宋林亿等校正医书时亦未能窥其全貌。魏晋南北朝去其时未远,因此探究该时期医学,与今本《金匮要略》作比较,明确其传承与创新之所在,既可厘清医学发展史,又可补后世于张仲景论杂病之未逮,还可为当今临证开拓思路。以下举心痛病为例,就二者所论作粗浅比较。
1 二者论心痛病病机的比较
1.1 《金匮要略》所论《金匮要略》第九篇:“阳微阴弦,即胸痹而痛,所以然者,责其极虚也。今阳虚知在上焦,所以胸痹、心痛者,以其阴弦故也。”[1]87即以“阳微阴弦”之脉象阐释心痛病的病机。其中阴、阳的理解,历代医家虽存不同见识,但结合原著以阴阳示脉象的其它论述,如“血痹阴阳俱微”[1]58、“妇人得平脉,阴脉稍弱”[1]201、“审脉阴阳,虚实紧弦”[1]219,徐彬“关前为阳……关后为阴”[2]的看法较为妥当。即以关部为界,关前寸部为阳,“阳微”即寸脉微,候上焦心肺阳气虚;关部及关后尺部为阴,“阴弦”即关、尺脉弦,候中、下焦阴邪(如寒、饮邪)盛。一方面上焦心肺阳虚,另一方面来自中、下焦的阴邪,趁虚而入,窃据阳位,痹阻心阳,从而导致心痛病。
第十一篇:“心中寒者,其人苦病心如噉蒜状,剧者心痛彻背,背痛彻心,譬如蛊注。”[1]112心中阴寒,寒凝脉络,阳气郁闭,轻者心中如噉蒜状,剧者心痛彻背,背痛彻心,症候虽有轻重之别,但皆由阴寒痹阻心脉所致。
1.2魏晋南北朝医学所论《针灸甲乙经·卷九》有篇名“寒气客于五脏六腑发卒心痛胸痹心疝三虫第二”,并载“心痛有三虫,多涎,不得反侧……心痛身寒,难以俛仰,心疝气冲胃,死不知人……心痛上抢心,不欲食,支痛引鬲……胸胁背相引痛,心下混混,呕吐多唾,饮食不下……”[3]1551认为心痛病由寒邪客心,痰饮壅滞,气机冲逆所致。
《脉经·卷二》载:“寸口脉迟,上焦有寒,心痛……”[4]52,“阳维为病,苦寒热;阴维为病,苦心痛……诊得阴维脉沉大而实者,苦胸中痛,胁下支满,心痛”[4]60,《脉经·卷四》:“胃中有寒,时苦烦痛、不食,食即心痛,胃胀支满,膈上积”[4]101,所论心痛均由寒邪所致。《脉经·卷六》有与《金匮要略》第十一篇略同之述。
《小品方·卷第一·述看方决》:“今先记述上古已来旧方,卷录多少,采取可承案者,为《小品》成法焉。《华佗方》有十卷。《张仲景辨伤寒并方》有九卷……《张仲景杂方》有八卷……”[5]785《小品方》引述张仲景著作两部,对心痛病的认识当承袭《伤寒杂病论》的论述。
《肘后备急方》、《范汪方》、《深师方》、《集验方》、《新录方》、《龙门石刻药方》等有证治,缺病机之论。而《胡洽方》、《秦承祖药方》、《删繁方》等则论、治皆佚。
1.3二者所论的比较概而言之,是传承为主,亦有补充。
魏晋南北朝医学对心痛病的认识,继承了《金匮要略》“阳微阴弦”、“心中寒”的病机阐述,从《脉经》、《针灸甲乙经》等早期著作的记述即可见一斑。《肘后备急方》等方书,虽多方少论,但其方多为祛除寒饮、宣发胸阳、通畅气机之剂,以方测证,审证求因,仍是立足于“阳微阴弦”的病机而立法。
《脉经》引《难经·二十九难》:“阳维为病苦寒热,阴维为病苦心痛”[6]57,则补《金匮要略》之未逮。《针灸甲乙经》载:“厥心痛,暴泄,腹胀满,心痛尤甚者,胃心痛也”[3]1547,所描述的症候主要责之于胃,其病机见于《难经·六十难》,即“其五脏气相干,名厥心痛;其痛甚,但在心,手足青者,即名真心痛。”[6]108而《脉经》“胃中有寒,时苦烦痛、不食,食即心痛……”之论,则明示此处所谓心痛显然指胃痛。《内经》、《难经》所称的“真心痛”、“厥心痛”、“胃心痛”等病名,《金匮要略》虽未见述,但魏晋南北朝医学有较为详细地论述,其对心痛病的病机认识也更为全面。
2 二者论心痛病证治的比较
2.1 《金匮要略》所论《金匮要略》第九篇第4条:“胸痹不得卧,心痛彻背者,瓜蒌薤白半夏汤主之”[1]88,虽名胸痹,但以心痛彻背为主症,故宜属心痛病。第8条:“心中痞,诸逆,心悬痛,桂枝生姜枳实汤主之”[1]91,寒、饮停胃,气逆而上,故心悬痛,属心胃同病或心痛轻证。第九条:“心痛彻背,背痛彻心,乌头赤石脂丸主之”[1]92,相同的症候描述见于第十一篇,属心痛重证,故须乌头、附子同用峻逐阴寒,蜀椒、干姜为伍温中散饮,大辛大热之剂,为心痛之危急重证而设。
2.2魏晋南北朝医学所论《针灸甲乙经·卷九》引《灵枢·厥病》“真心痛,手足青至节,心痛甚,旦发夕死,夕发旦死”[3]1548,《脉经》、《小品方》亦引,以描述心痛病的主症。又引《灵枢·杂病》“心痛引腰脊,欲呕,刺足少阴……心痛,但短气不足以息,刺手太阴”[3]1550,以阐明心痛病的针刺治法;并明确具体取穴,“厥心痛,与背相引,善瘈,如从后触其心,身伛偻者,肾心痛也。先取京骨、昆仑,发针立已,不已取然谷……厥心痛,卧若徒居,心痛乃间,动行痛益甚,色不变者,肺心痛也,取鱼际、太渊”[3]1547。
《脉经·卷六》:“心病者,胸内痛,胁支满,两胁下痛,膺背肩甲间痛,两臂内痛。虚则胸腹大,胁下与腰背相引而痛。取其经,手少阴、太阳,舌下血者。其变病,刺郄中血者……邪在心,则病心痛,善悲,时眩仆,视有余不足而调之其俞。”[4]184《脉经·卷二》:“……心痛,咽酸,吐酸水。宜服附子汤、生姜汤、茱萸圆,调和饮食以暖之。”[4]52分别载心痛病的症候及治疗。
《肘后备急方·卷一》:“治卒心痛。桃白皮煮汁,宜空腹服之。又方:桂末若干,姜末,二药并可单用,温酒服方寸匕,须臾六七服,瘥。又方:驴屎,绞取汁五六合,及热顿服,立定。又方:东引桃枝一把,切。以酒一升,煎取半升,顿服,大效。”[7]14
“又方:灸手中央长指端三壮。又方:好桂削去皮,捣筛,温酒服三寸匕。不瘥者,须臾可六七服。无桂者,末干姜佳。”[7]15
“又方:尽地作五行字,撮中央土,以水一升,搅饮之也。”[7]15亦见载于《如意方》。
“治心下牵急懊痛方:桂心三两,生姜三两,枳实五枚。水五升,煮取三升,分三服。亦可加术二两,胶饴半斤。”[7]17症、治与《金匮要略》同。
“治心痹心痛方:蜀椒一两(熬令黄),末之,以狗心血丸之,如梧子。服五丸,日五服。”[7]17
《范汪方》收录《金匮要略》心痛病的证治,如治心下悬急懊痛的桂枝生姜枳实汤,治心痛彻背、背痛彻心的乌头赤石脂丸。此外,载有心痛病更为详细的证治,如“疗心下切痛引背,胸下蓄气,胃中有宿食,茱萸煎方:吴茱萸一升,蜀椒五升,甘草二两炙,干地黄一斤。右四味,以清酒三升渍三宿,绞取汁,铜器中煎令沸,麦门冬五升去心、干漆一斤内煎,中色黄,绞去之,内石斛五两、阿胶一斤、白蜜六升,凡九味以汤煎,令可丸,取如枣大。含,稍稍咽之,日三,甚者日五六服……奉车都尉陈盖试有验。”[5]674胃中宿食停滞,气机痞塞心胸、脘膈,致“心下切痛引背”,故当属胃心痛。
“又芫花汤,主卒心痛连背,背痛彻心,心腹并懊痛,如鬼所刺,绞急欲死者方:芫花十分,大黄十分。右二味,捣下筛,取四方寸匕,着二升半苦酒中合煎,得一升二合,顿服尽。须臾当吐,吐便愈。”[5]674
“治卒心痛,桂心汤方:桂心八两。右一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分二服。忌生葱。”[5]674《肘后备急方》、《集验方》有相同记载。
“疗胸中寒热心痛,清唾满口,数数欲吐,食不化,干姜丸方:干姜一分,桂心一分,矾石一分熬令汁尽,半夏一分,蜀椒一分。”[5]674胃寒饮停,痹阻心阳,故心痛、多唾、食不化,仍属胃心痛。
《小品方》亦详引《灵枢·厥病》有关“真心痛”、“厥心痛”的论述,又载:“九痛丸主九种心痛……附子二两,巴豆人一两,生狼毒一两炙令极香抨,人参一两,干姜一两,吴茱萸一两。六味,蜜和,空腹服如梧子三丸……好好将息,神验。”[5]792通治九种心痛。“解急蜀椒汤,主寒疝气,心痛如刺,绕脐绞痛,腹中尽痛,白汗自出,欲绝方。蜀椒三百枚汗,附子一枚炮,粳米半升,干姜半两,半夏十二枚洗,大枣三十枚,甘草一两炙。右七味切,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澄清,热服一升,不差,更服一升……《医心方》作‘数用,疗心痛最良’。”[5]791
又载灸心痛方,“心懊憹,彻痛烦逆,灸心俞百壮。心痛如刀刺,气结,灸鬲俞七壮。心痛胸痹,灸膻中百壮。心痛冷气上,灸龙头百壮。在心鸠尾头上行一寸半。心痛恶气上,胁急痛,灸通谷五十壮。乳下二寸。心痛暴绞急绝欲死,灸神府百壮。附心鸠尾正心,有忌。心痛暴恶风,灸巨阙百壮。心痛胸胁满,灸期门,随年壮。心痛坚烦气结,灸太仓百壮。”[5]848
《深师方》载:“治卒心痛方:当归二两,芍药一两,桂心一两,人参一两,栀子二十一枚。五物,口父咀,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分服五服。又云,治三十年心痛,附子丸方:人参二两,桂心二两,干姜二两,蜀附子二两,巴豆二两。凡五物,下筛,蜜丸如大豆,先食服三丸,日一。神良。”[5]952又载:“疗胸满短气,心痛吐涎虚冷,防风茯苓汤方:防风二两,茯苓二两,桂心六两,甘草二两炙,半夏四两洗,干姜四两炮,人参三两。右七味,切,以水一斗,煮取三升,绞去滓,分三服,良。”[5]952所载三方均用益气之人参、温通心阳之桂心。
《集验方》:“卒心痛,桂心汤方:桂心八两。右一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分二服。”[5]1194《新录方》:“治心痛方:饮井花水二升。又方:以热汤渍手足,以差为度。又方:烧秤锤令赤,投二升酒中,分二服。”[5]1332《龙门石刻药方》:“冷心痛:吴茱萸一升,桂心三两,当归三两,捣末,蜜和丸如梧子,酒服十丸,日再,渐加三十丸,以知为度……灸法:从项椎骨数下,至第七节上,灸三十壮。又,灸心下一寸,二七壮。”[5]1383
2.3二者所论的比较其一,证候描述趋于完备。《针灸甲乙经》、《脉经》、《小品方》等引《灵枢·厥病》“真心痛,手足青至节,心痛甚,旦发夕死,夕发旦死”[8]之论,结合《金匮要略》“心痛彻背,背痛彻心”的记述,魏晋南北朝医学对心痛病的典型证候认识已跃然纸间。
其二,治疗方药更加丰富。魏晋南北朝医学除载有《金匮要略》的乌头赤石脂丸等三方外,还载有大量的方剂。如《肘后备急方》中的众多简便效廉方,《范汪方》中的茱萸煎方、芫花汤、桂心汤等,《小品方》中的九痛丸、解急蜀椒汤等,《深师方》中的治卒心痛方、附子丸、防风茯苓汤等,《集验方》中的桂心汤等。这些方药大都切中病机,应用效验,如《范汪方》茱萸煎方后“奉车都尉陈盖试有验”,即举病案加以证实其功效。它们均未载于《金匮要略》,具有创新性,而当今临床亦罕见其应用,故值得深入挖掘、研究。其中有少数方药,在今天看来未必有效,如《肘后备急方》、《如意方》均载“尽地作五行字,撮中央土,以水一升,搅饮之”以治心痛之法,当客观公正地看待其疗效。
其三,治疗手段趋于多样。《内经》虽有针刺疗法,但《金匮要略》并未见载;《针灸甲乙经》、《脉经》、《肘后备急方》、《小品方》等均载有该法,尤其《肘后备急方》、《小品方》、《龙门石刻药方》又载灸法,《范汪方》载涌吐疗法。可见,魏晋南北朝医学治疗心痛病,较之《金匮要略》,并非仅内服汤药一端,而是药、针、灸并用,内、外治兼顾,手段明显趋于多样。
3 小结
就心痛病病机、证治而言,魏晋南北朝医学所论与《金匮要略》相较,有继承,有扬弃,亦有创新。病机阐述以继承为主、亦有补充,证候描述传承中有发展,治疗方法继承中尤其着重创新。通过二者所论的比较,古代对于心痛病的因机证治体系较为完整地展示出来了,对于当今诊治该病不无裨益。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医书中有关该病治疗方药的创新内容,大多为当今中医所忽视,继绝存亡,挖掘创新,才能发挥中医特色与优势。
[1]何任主编.金匮要略校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
[2]清·徐忠可著.金匮要略论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122.
[3]张灿玾,徐国仟主编.针灸甲乙经校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
[4]沈炎南主编.脉经校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
[5]严世芸,李其忠主编.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总集[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
[6]凌耀星主编.难经校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
[7]晋·葛洪原撰,梁·陶弘景补辑,金·杨用道补辑,胡冬裴汇辑.附广肘后方[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8]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点校本)·第二册·医经注释[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217.
张志峰,男,医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历代医家学术思想研究。
湖北中医药大学中医临床学院(43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