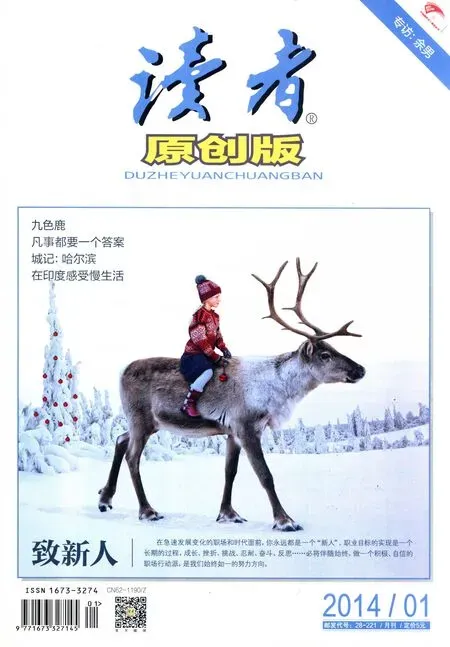鹏鹏
文 _ 田弘毅
鹏鹏
文 _ 田弘毅

1
“不是‘朋友’的‘朋’,是‘大鹏’的‘鹏’。”别人把他的名字写错时,他总这么纠正。鹏鹏是我上小学第一天认识的两三个人之一,我还能记起那天他穿着一件红白相间的二指背心的样子。背心上面印着《芝麻街》里那只又黄又胖的大嘴鸟。他总喜欢噘着嘴,和那只胖鸟也有几分神似。
小学时我们班有50多人,如果稍微留心,就能把这群小朋友归成几类—古灵精怪最得老师宠的,张牙舞爪只知道捣乱的,羞答答一声不吭缩在角落的,当然,还有一两个照陕西人的话说,不那么灵性的。
鹏鹏一开始就算不上灵性。语文课上,他总记不住生字的笔画;数学课上,他总掌握不了加减法;体育课上,他跳绳的动作永远不得要领。他宽而扁的脑袋,不管高兴或不高兴随时噘起的嘴巴,还有常常造访上嘴唇的两行鼻涕,让他变得很滑稽。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小朋友都给鹏鹏起过外号,但我们的创意有很大的局限,多半脱离不了傻、笨、呆的意思。
有一天,早上第一节课,鹏鹏因为出去倒垃圾而迟到,老师并没有批评他,只是告诉他劳动光荣,但不能耽误学习。我看着他,他的扁脑袋,他沾着灰尘的鼻涕,他脏兮兮的衬衣短裤,他周身透出的“劳动人民”的气息,我突然很鄙夷地笑了。我对同桌说:“他这种人就配倒垃圾。”我的声音不大,老师和鹏鹏都没有听到,但还是在周围引起一阵笑声,我挺得意。
15年之后,我发现自己仍然没有忘记那句话。相反,那个句子里的每个字在我舌头上跳动而过的感觉,脱口而出后在四周空气里轻轻震荡的回响,都保持了那一天那一刻的真实和准确。文艺路小学二年级四班那个早晨的一切都被瞬间还原。年幼时的残忍无情丝毫不输长大后的刀光剑影,可它究竟是从哪儿来的?
2
三年级开始,男孩们好像一夜之间长出了獠牙利爪,打架成为风靡全年级的体育活动。班上的几个男孩隔三差五把鹏鹏堵在教室门口,二话不说就在他身上练起拳脚。鹏鹏不哭也不还手,他只是站在原地等待事情的结束。我记得很清楚,有几次他是笑着挨完一顿打的。鹏鹏唯一的反抗也是口头上的:“我告诉老师呀!”他经常在整个过程临近尾声时才扯着嗓子用极高的音调发出这样的威胁。打人的男孩们一开始有些心虚,但很快发现鹏鹏只是喊喊,根本没有胆子去告诉老师。
一年之后,我从小组长升为中队长,经常作为老师的“使臣”被委派到几个所谓差生的家里,向他们的家长告状。
有一次,我奉命和鹏鹏一块儿回家。鹏鹏他爸开门一看见是他,就咆哮起来:“你咋回来了?又咋了?”他一只手揪着鹏鹏的耳朵,把鹏鹏往门里拽。
“叔叔,崔鹏又没写数学作业,他还跟老师说他忘带了,他都忘带好几次了。”
“你又给我惹事,老子自己的事还不够烦的呢!看老子今天怎么收拾你!”如果忽略他的语言,他简直就像院子里那些拍洋画片的小孩一样叫着跳着。
“叔叔,你别打他了。”
“你别管。”他掐着鹏鹏的脖子,把他拽进另外一个房间。
门摔得响亮,整栋楼微微颤动。咆哮声紧接着传来,含混不清,鹏鹏的哭喊声变得尖锐。唯一令我感到庆幸的是,我没有听到皮带在肉上“硬着陆”的那种爽脆利落的声音。后来,我从一个同学那里得知,鹏鹏的爸爸经常用那种老人坐的木质小板凳打鹏鹏,砸他的脑袋。那声音是钝的,埋藏在父子俩的喊叫声中。
门开了。鹏鹏他爸在鹏鹏背上推了一把,鹏鹏一个趔趄,几乎是滚着出来的。
“你给老师说,我已经教育过崔鹏了。”他脑门上结满汗珠。
我和鹏鹏走出院子,天还是一大片稠浊的灰色。我们穿过路上浙江人开的布匹摊子朝学校走去,花花绿绿的窗帘布从我们脸上轻轻拂过。我们都哭了。
3
六年级的一次作文课,题目是“以后的我”。按照惯例,动笔之前老师会叫一些学习好的同学说说自己的想法。鹏鹏在课堂上从不主动发言,但那天鹏鹏第一个举起了手。他坐在他的“特座”上—那是老师专门给他安排的座位,就在讲台旁边—右手慢慢举起来,在半空晃悠着。
“来,崔鹏,你说说。”
“长大的我,”他站起来,声音变得庄严,用一字一顿的学生腔说,“会当一个董事长,我会有一个大公司。我的公司里人很多,生意很好,人们都尊敬我。每天早上我上班,门口的保安小李都会跟我说:‘崔总,您的信!’我对他说:‘你辛苦了!’这就是以后的我。”
巨大的、海浪般的笑声瞬间爆发,险些震碎玻璃。有人笑趴在桌上,有人高喊着“崔总”,有人接着高喊“您的信”。
这好像是个分水岭,所有之后发生的事情都罩上了一层模糊的壳,所有的声音都变得瓮声瓮气。时间在这毛玻璃罩子下撒开腿飞奔,快得发狂,仿佛有人突然按下了快进键。
姜文电影里的孩子把书包高高抛起,书包落地,孩子已长成少年。其间的苦乐,让它停在云端,落在枝头,消失在鸟儿的嘴尖吧。多浪漫!恍惚中,我看到毕业典礼之后,鹏鹏一个人站在操场上,他头顶上是巨大火热的太阳,整个操场陷入一片涌动的光海之中。他也把自己的书包向天空抛去,却久久不见它落下来。
4
鹏鹏消失了8年。直到大二那年暑假,我偶然联系到一两个小学同学,才猛然想起他。
同学们的样貌大都脱离了小学时候的“初稿”,时间描线,荷尔蒙上色,青春一下子跳跃在纸上。鹏鹏是个例外,好像有一双大手为了省事,只是把他从头到脚全部选定,拖着一个角把整个人按比例放大,除此以外再无变化。老师说这次聚会是鹏鹏发起的。
“同学们,朋友们,”鹏鹏的嗓音粗了些,“今天是个快乐的日子,今天是我们相会的日子!我们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工作了,林老师也结婚了。以前有些人欺负过我,但我们还是好朋友。大家今天都要吃饱玩好,祝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说完,他把手里那张皱巴巴的发言稿塞回裤子口袋。
再没有海浪一样的笑声,所有人都鼓着掌,老师说:“我们的崔鹏确实长大了。”
我抿紧嘴角,两只手把屁股底下椅子上的衬布抓起了几十层褶子。我终于没有哭。彼时彼刻,我像一个被关押已久等待执行的死刑犯人听到赦免的消息,像一个打家劫舍、恶贯满盈的江洋大盗在佛前滚鞍下马。
我没有作恶。我在心里像默诵经文一样默诵这几个字,终于感到一丝宽慰。
鹏鹏告诉我,他在一所警官学校学习,过几个月就去派出所实习,转正的希望不小。他说他爸爸在一次车祸中去世,家里只剩他一个人。他在警校谈了个女朋友,长得很漂亮,穿上警服神气得不得了。聚会结束时,他要了个塑料袋,把桌上的剩菜一股脑儿倒进去,说是要喂他的警犬。
那天晚上,我和一个小学时候的好友聊天,说起鹏鹏。
“你在国外吃汉堡、薯条吃傻了?”他对我言语中流露出的欣慰大惑不解,“那都是编的!我们给警校打过电话,人家说根本没听过这个人!”
“那照片……”
“你不信自己上网去看,他所有在警校的照片要么只有他一个人,要么只有别人没有他。我估计他的警服都是借来的。”
“那他的女朋友呢?”
他笑得呛住了,吐出一大团烟雾:“他从别人的QQ空间里复制照片,说是他女朋友。”
“他说他爸去世了,这不会是假的吧?”
“放屁!我们上周还在院子门口见他爸了。你都不想想,你家喂警犬用蕨根粉和麻婆豆腐?崔总嘛,能编得很!”
我一下愣住,脑子爆炸了,但悄无声响。
5
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鹏鹏通知所有人他要结婚了。这消息突如其来,让人不免心生怀疑,但包括老师在内的多数人还是准备参加婚礼。婚礼当天,人们按照鹏鹏的指示在一家饭店门口集合,却被告知当天根本没有婚宴。傻等半小时后,鹏鹏打来电话说通知错了地方,他已经租好面包车来接大家,从此再无音讯。
我问过几个同学,这是不是鹏鹏蓄谋已久的报复?他们并不这么认为。那为什么呢?他们撇撇嘴:“可能还是傻吧。”
这便是我能想起来的所有关于鹏鹏的故事。我原以为,我从这个方块字垒起来的迷宫里走出来时,会得到一个起码令自己满意的答案,但看样子是办不到了。
我眼前一遍又一遍浮现出鹏鹏遭受欺负的模样:他的衣服上满是鞋印和污泥;他孤零零地站在一间教室的中央,噘着嘴,鼻涕正不急不缓地流下来。在另一间屋子里,那个被按比例放大的他也站在中央,但他的脸上一片模糊。
我作恶了吗?夜空里的钟摆来回晃着,轻轻触碰我大脑空间的边缘。
图/沈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