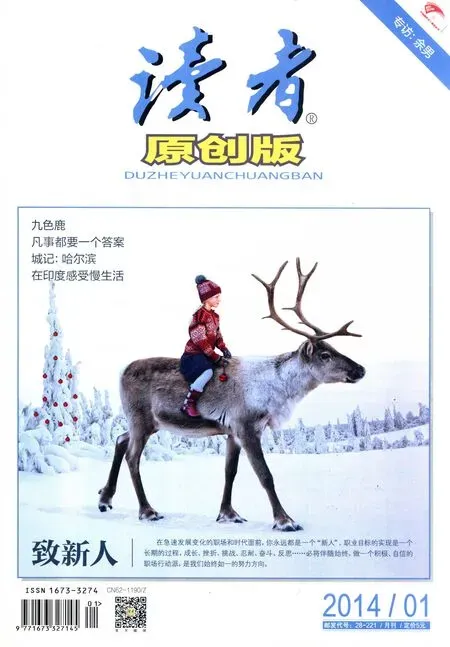坐上桌玩一把
文 _ 碧城
坐上桌玩一把
文 _ 碧城
你想象中的职场生活是什么样子?计划周详,按部就班,责任大过天?或许你需要放松自己,去了解工作中的沟通、求助、适度拒绝,以及公平和机会。坦然坐在桌边,自信、投入地玩一把。

工作是对人的异化,但多数人仍需要通过工作实现价值,回归自我。所以,工作是现代人打不破的迷梦、必须要的负担,对于那些对自我期待很高的人来说,更是自我实现的途径。而身为女性,在职场中,既有《杜拉拉升职记》那样充满正能量的励志轨迹,也需要更超脱的性别视角和自我认识。
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博格在演讲中说,女性在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领域都还没有占据绝对领导的位置,至少她那一代女性,没有在任何一个领域占据50%的领导席。她建议职业女性首先要学会在桌边坐下来—自信地和男性以及老资格们一样坐到桌边来,坐在一个表明自己能够光明正大承担工作的位置上。我花费5年半时间,才粗知这个道理。
戴面具的“职场新人”
我毕业第一年的10月,出差路过兰州,去看大学死党,他有一种“你是不是内芯被换了”的讶异。那个嚣张跋扈、懒惰自大、视循规蹈矩为对智商的侮辱的文艺女青年,在短短几个月中变成了一个完全相反的人。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戴着想象出的面具的职场新人。现在回想那一年,以及接下来的两三年,我都是同一副形象:拘谨自制,严肃刻板,充满了过剩的责任感,对自己经手的每一件事都抱有莫名的荣誉心,以一种几乎是戒惧的姿态应对每一个工作细节,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我从不质疑领导,非常尊重前辈,所有的压力都指向自我要求,从小学起就不肯上早读课的懒散,几乎被一夕治愈。我对因工作约定的时间有一种几乎变态的在意:如果有人连续3次在我参与的工作会议或出访中散漫或迟到,我会对他产生一种根深蒂固的厌恶。而如果有人给我一份不合格的表格,我就会在心里默默地把他划入“智商及工作能力有问题”这个类别。
也是那一年,部门要做客户答谢及年终总结会,我原本负责广东一个偏远小学学生的邀请和组织工作,会议倒计时第三日下午,突然又接到同组资深同事“做不过来”的一个小组的总结PPT制作任务,时间跨度从部门开始做第一个项目起到那一年年底。我虽然从实习期就协助多个项目,入职就负责一个独立项目,但毕竟进组未满半年,对整个小组的工作,尤其是已经运作了两三年的一些项目,几乎从未得到过系统的信息培训。我所掌握的都是我在辅助其他同事工作的过程中接触到的各种散乱文件:一年一签的各式合同、媒体报道中的各种片段、大量的照片、不同时期的广告……中间因为人员变动出现的交接空白和各式文字表述不清的信息,我根本无从得知。
但那时候有一种“绝不允许自己手头出现一件完不成的工作”的痴傻执拗,所以我几乎没有提任何条件,也不懂让老同事们交出他们梳理过的文件,就答应了。我盘点手头的工作,要完成所有事项,剩余的时间只能以小时计。然后,我下午3点打完所有联络电话,坐在电脑前,持续做到次日凌晨4点,没有吃饭,没有睡觉,除了喝水、去卫生间,几乎没动过。我梳理了3年多来部门如何从无到有,从一个项目发展到多个项目的脉络及亮点,最后做出了60多页PPT。
群发邮件给小组领导及那位资深同事后,我回到家里,收拾行李,早上6点钟出现在深圳火车站,登上已租好的车,直奔阳江一个小镇。中午1点钟到达学校,接上已经准备好的老师和小学生,马上返程,到下午5点多钟,全天没有吃过一口饭的我终于带着小组走进酒店时,看见那位之前说“做不过来”的资深同事在酒店商务中心那里,以15块一张的价格,打印着一份PPT。那就是我昨夜的成果,她换上了统一的心形母版,把握十足地跟总监助理描述自己做得多么辛苦。我的世界观都要碎裂了。我沉默又恭谨地做好任何一件事的时候,可从没想过会有这样的情形。
次年,我们有一个项目要在异地完成,我负责统筹,北京的同事负责征集观众。那是一位非常自信且仪表堂堂的男同事。在前期沟通中,我为“春季冷又多雨,如果信息传递不足,是否会出现观众不够的情况”担忧时,他非常自信地表示:“你就放心吧,我不仅联系了执行方,而且找了场地协助人,至少会多出50人至100人。”这样的承诺在多方电话会议中也一再出现,我有什么理由怀疑一个看起来这么靠谱的人呢?结果活动前一日落雨,活动当天,春寒料峭,阴云不开,时间快到,嘉宾已齐,我接到他慌慌张张的电话,狂奔过去拉开某礼堂那庄严华贵的大门时,心跳都停止了:那就是活生生的噩梦上演,整个礼堂红艳艳的300多把丝绒座椅上,零星坐着不足30个观众!
那一天是如何度过的,我几乎不记得了。
就在这样的考验中,我终于逐渐伸展蜷缩得太紧的自己,把对工作的理解和要求,从单独的苛责自己上转移出来,开始去理解工作中的沟通、求助、适度拒绝,以及公平和机会。
但我的时间已经逝去,那个埋头吞掉工作事项,如同黑洞一样存在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我没有自我,没有表达立场和规划的意识。我的同事们知道我是可靠的人,所以什么项目都想请我协助;我的领导知道我是有责任心的人,所以给我各种必须推动的事项;而部门决策者对我的了解都建立在资深同事对我的描述之上,所以也并不能明确我的特质。于是有一段时间,他们先是把我调到北京的另一个小组,然后让我负责策划工作,接着是品牌工作……
投入地玩一把
在每一个时期,我都尽我所能,把“需要我”的工作做好,甚至超出预期,但是我没有主动告知过任何一个人我的规划和需要。在这种双方不能详尽了解的痛苦中,我辞职了。我牢记我是一个“职场新人”,永远让前辈发声,让更自信的人掌控局面,让别人先行,自己把工作默默做完。但我忘记了“我”,我的成长、我的喜好、我的技能、我的创造力及其所需要的特有轨道。
接下来的一两年中,我用很多种方式试图主动传达自我,激烈跋扈过,严苛过度过,也有过分公事公办,冷冰冰、“职业化”到让人愤恨。我也试图从各个方面证明自己,创意、策划、管理、团队……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我的存在。我渴望充分表达的同时,无限地透支自我。有人叫我女强人,有人说我是工作狂。有一个女同事曾经问我:“除了工作,你心里还会想别的事吗?”这种局面并未让我好过,我的小组成员都长期过劳,压力巨大,没有午后慵懒、下午茶聚的逍遥时刻。部门领导认为我过于排斥合作,也就是管了太多事,不给别人发挥的空间。
我几乎觉得工作是我永远摆不平的一个模块了,那种焦虑感和“时间在白白流逝”的忧惧充斥我心。年初,我飞去马尔代夫度假,在悬隔世外的小岛上,我问自己:这些焦虑、忧惧、苛刻、对自己和对别人的不放松,都是从哪儿来的?那个答案就是:不自信。我不相信自己可以从容地应对工作,不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分量掌控所有工作局面,不相信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重要且令人敬佩的人”。突然有一天,就是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和集团同事们围桌开完长会的那一天,我听到了谢丽尔·桑德博格的演讲。她把我所有的努力总结为一句话:“Sit at the table(坐在桌边).”
在桌边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来,既不自我贬抑,埋入墙边角落,也不过分自满,骄纵不知分寸。忘记自己是个新人、女性、不漂亮、没爹拼……忘记所有的自我评价和限制,只是坦然地坐到桌边,投入地玩一把。这是工作对个人的全部要求,也是个人开始享受工作的关键起点。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