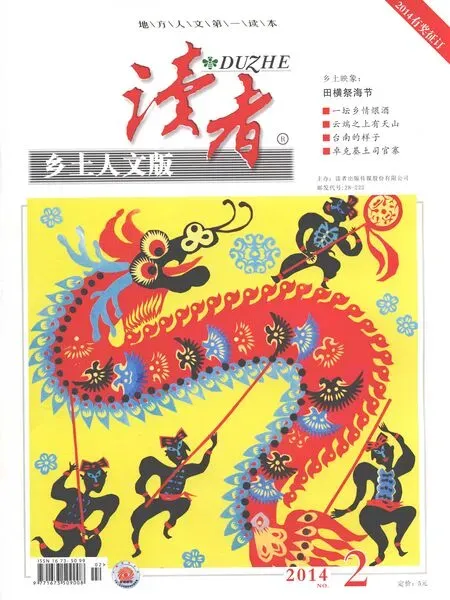山西,山西
文/柴 静
山西,山西
文/柴 静

我出生在1976年的山西。山西姑娘没见过小溪、青山之类的景致,基本上处处灰头土脸,但凡有一点诗意,全从天上来。苦闷时也只有盯着天看,晚霞奇诡变化,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阵雨来得快,乌黑的云团滚动奔跑,剩了天边一粒金星没来得及遮,一小粒明光闪烁,突然一下就灭了。折身跑时,雨在后边追,卷着痛痛快快的土腥气扑过来。
一
2006年我回山西采访,在孝义县城一下车就喉头一紧。同事说:“哎,像是小时候在教室里生煤炉子被呛的那一下。”
是,都是硫化氢。
天像一个烧了很长时间的锅一样盖在城市上空。一眼望去,不是灰,也不是黑,是焦黄色。去了农村,村口有一所小学,一群小孩子正在剪小星星往窗户上贴。有个圆脸大眼的小姑娘,不怕生人,搬个小板凳坐在我对面,不说话先笑。
我问她:“你见过星星吗?”
她说:“没有。”
“见过白云吗?”
“没有。”
“蓝天呢?”
她想了好久,说:“见过一点点儿蓝的。”
“空气是什么味道?”
“臭的。”她用手扇扇鼻子。
6岁的王惠琴闻到的是焦油的气味,不过更危险的是她闻不到的无味气体,那是一种叫苯并芘的强致癌物,超标9倍。离她的教室50米的山坡上,是一个年产60万吨的焦化厂,对面100米的地方是两个化工厂,她从教室回家的路上还要经过一个洗煤厂。不过,即使这么近,也看不清这些巨大的厂房,因为这里的能见度不到10米。


村里的各条路上全是煤渣,路边庄稼地寸草不生。在这焦黑的土地上,她的红棉袄是唯一的亮色。
二
我家在晋南襄汾,8岁前住在家族的老房子里,清代的大四合院,砖墙极高,朱红色的漆已剥落的门口有只青蓝石鼓,是我的专座,磨得溜光水滑。奶奶要是出门了,我就坐在那儿,背靠着凉丝丝的小石头狮子,等她回来。
一进门是个照壁,上面原来是朱子家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北厦有两层,阁楼不让上去,里头锁着檀木大箱子,大人说有鬼。小孩们不敢去,手脚并用爬上楼梯往里看一眼,太阳照透了,都是陈年尘烟。小孩儿总是什么都信,大人说这房子底下有财宝,我们等大人们中午都睡着了,拿着小铲子,到后院开始挖坑,找装金元宝的罐子。
一下雨就没法玩了,大人怕在积了水的青砖院子里滑了脚。榆木门槛磨得光滑又暖和,我骑坐在上头,大梁上的燕子一家也出不去,都呆呆地看外头。外头槐绿榴红,淋湿了更鲜明。我奶奶最喜欢那棵石榴树,有时别人泼一点水在树根附近,如果有肥皂沫,她不说什么,但一定拿小铲铲点土把肥皂水埋上,怕伤着树。
那时候,河边还有明黄的水凤仙,丁香繁茂,胡枝子、野豌豆、白羊草……蓝得发紫的小蝴蝶从树上像叶子一样垂直飘下来,临到地上了才陡然一翻。还有蟋蟀、蚂蚱、青蛙、知了、蚯蚓、瓢虫……那时候吃的也多,把青玉米秆用牙齿咬开,嚼里面的甜汁。挖点马苋菜回家拿醋拌了,还有一种灰白的蒿,回去蒸熟与碎馒头拌着蒜末吃,是我妈的最爱。最不济,河滩里都是枣树,开花时把鼻子塞进米黄的小碎蕊里拱着,舔掉那点甜香,蜜蜂围着鼻子直转。秋天我爸他们上树打枣,一竿子抡去,小孩子在底下捡拾。
三
河边上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盖纺织厂、纸厂、糖厂、油厂……柏油路铺起来,姐姐们进了厂工作,回来拿细棉线教我们打结头。那时,工厂里有热水澡堂,姐姐们带我们去洗澡,她们揽着搪瓷盆子冲着看门的男子一点头,笑意里是见过世面的自持。纺好的泡泡纱做成灯笼袖小裙子,我穿一件粉蓝的,我妹的是粉红的,好不得意。
人人都喜欢工厂,厂门前有了集市,热闹得很,大喇叭里翻来滚去唱“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啰喂……”声震四野。有露天电影,小朋友搬一张小板凳占座位,工厂焊的蓝色小铁椅,可以把红木板凳挤到一边去。放电影之前,常常会播一个短纪录片,叫《黄土高原上的绿色明珠》,说的是临汾。我妈带我们姐妹去动物园时,每次都要提醒“电影里说了,树上的柿子不能摘,掉下来也不要捡,这叫花果城”。
我上中学后,姐姐们陆续失业。之后10年,山西轻工业产值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从将近40%下滑到6%。焦化厂、钢厂、铁厂……托煤而起,洗煤厂就建在汾河岸边。我们上课前原来还拿大蒜擦玻璃黑板,后来擦不过来,一堂课下来脸上都是黑粒子。但我只见过托人想进厂的亲戚,没听过有人抱怨环境—就像家家冬天都生蜂窝煤炉子,一屋子烟也呛,但为这点暖和,忍忍也就睡着了。
我父母也说,要是没有这些厂,发不了工资,他们可能就攒不够让我上大学的钱。
我1993年考上大学离开山西,坐了30多个小时的火车到湖南,清晨靠窗的帘子一拉,我都惊住了,一个小湖,里头都是荷花—这东西在世上居然真有?就是这个感觉。孩子心性,打定主意不再回山西。就在这年,中国放开除电煤以外的煤炭价格。当时1吨煤卖17块钱,此后10年,涨到1000多块钱1吨。煤产业自此大发展,在山西占到GDP的70%,成为最重要的支柱产业。
2003年春节,我从临汾车站打车回家,冬天的大早上,能见度不到5米。满街的人戴着白口罩,鼻孔的位置有两个黑点。车上没雾灯,后视镜也撞得只剩一半。精瘦的司机直着脖子伸到窗外边看边开,开了一会儿,打电话叫了个人来:“你来开,我今天没戴眼镜。”
我以为是在下雾。
他说:“嗐,这几天天天这样。”
我再也不想回山西了。
四
“再也”,这两个字刺目。
2007年,我再回山西。
王惠琴7岁了,剪了短头发,黑了,瘦了,已经有点认生了,远远地站着,不打招呼只是笑。
她家还是没有搬,工厂也没有搬。在省环保局的要求下,企业花了6000万把环保设备装上了,老总带着我们左看右看:“来,给我们照一照。”我问:“你这设备运行过吗?”老总的儿子嘿嘿一笑:“还没有,还没有。”
在临汾时,我曾去龙祠水源地拍摄。水源地只有10亩左右,“最后这点了,再没有了。”边上的人说。
我站在栅栏外面往里看,愣住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山西。
附近村庄里的小胖子跟我一起把脸挤在铁栅栏上往里看,谁都不说话。水居然是透亮的,荇藻青青,风一过,摇得如痴如醉,黄雀和燕子在水上沾一下脚,在野花上一站就掠走了,花茎一摇,细细密密的水纹久久不散。
一抬头,一只白鹭拐了一个漂亮的大弯。
这是远古的我的家乡。
(薇拉拉摘自新浪网柴静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