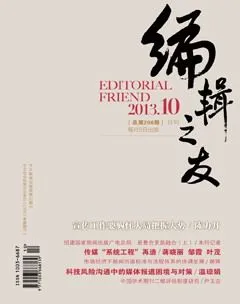科技风险沟通中的媒体报道困境与对策
摘要 随着科技风险对现代社会的日益渗透,促成有效的科技风险沟通成为大众传媒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但是,由于科技风险属性与新闻运作规律之间存在冲突,导致在科技风险沟通的过程中,大众传媒新闻报道陷入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闻真实性与科学准确性之间的差距,二是科学风险的不确定性与戏剧性报道,三是消息来源的多元性与平衡报道。面对这种困境,大众传媒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应对,一是提高报道能力,二是以“公众理解科学”作为指导理念强化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
关键词 科技风险 风险沟通 媒体报道
温琼娟,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武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风险是指事态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及这种不确定性给主体造成的威胁或者伤害。科技风险是由于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给主体带来的潜在的伤害,属于被人类制造出来的风险。尽管科技风险转化为事实的概率非常低,但是只要存在这种可能性,就会引起社会的高度情绪反应,进而转化为危机,而避免科技风险转化为事实危机的主要措施就是针对科技风险预先进行风险沟通。大众传播媒介是科技风险沟通的最重要平台。
一、大众传媒在科技风险沟通中的功能
首先,与传统的外在风险相比,科技风险不可以直接感受,并不属于直觉的范畴。也就是说,如果公众没有被预警、被提醒,有可能完全感觉不到科技风险的存在。正如贝克(Beck)所说:如果没有视觉化的科技、没有象征的形式、没有大众传媒,风险就什么都不是。[1]因此,大众传媒在科技风险沟通中的首要作用就体现在使科技风险在社会中具有“可见度”。
其次,科技风险虽然具有客观依据,但毕竟是预期的,因此它的呈现过程同时也就是一个社会建构过程,它是客观存在与主观认知的结合体。大众传媒在科技风险沟通中并不仅仅只是中介,而是直接参与有关科技风险的知识建构,大众传媒所呈现出的科技风险内容,正是公众有关科技风险知识的主要来源。
再次,与一般的科学传播相比,科技风险沟通有明确的目的,即希望能够整合社会多元力量,共同寻求规避风险的决策,防止风险转变成为事实。这是一个反思、解释、论证、认可和协商的过程,而大众传媒通过展示“多种声音”,使得这个对话的过程得以实现。
二、科技风险沟通中媒体报道的困境
报道与科技风险相关的新闻是大众传媒风险沟通的主要方式。科技风险新闻所呈现出的内容,除了受到科学事实、文化背景、社会环境等多元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新闻规范及新闻价值的制约。
但是,新闻运作规律与科技风险属性两者的相悖之处,最终导致呈现在公众面前的科技风险新闻往往受到科学界的诟病,认为其并不能真正起到沟通科技风险的目的,不仅如此,甚至还有误导公众的嫌疑。新闻媒体也常常被批评为危言耸听、不负责任,又孤陋寡闻,[2]背离了大众传媒科技风险沟通的初衷。如一位著名核物理学家声称:“对核辐射的恐惧已经使公众发疯。我特意使用 ‘发疯’这个词,是由于其含义是‘缺乏与现实的联系’。公众对核辐射危险的理解实际上已经与科学家理解的实际风险毫无关联。”[3]在此,笔者从以下3个方面总结科技风险沟通中的媒体报道困境。
1. 科技风险表述的准确性与新闻真实性之间的差距
对于科技风险新闻内容的要求,新闻界和科学界有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新闻界称之为“真实性”,这是新闻原则的最基本要求;而科学界称之为“准确性”,这也是科学精神的体现。这两者从字面上看,含义比较接近,但是详细考究其内涵,则差异较大。
科学界对准确性的要求,亦即专业期刊论文的准确性标准,是指研究方法、步骤以及实验结果等原始数据资料,能够经得起同行的重复检验,过程详细,结论精确。而新闻的真实性是指,报道对象及事实现实存在,另外,从认识论意义上讲,新闻报道对新闻事实的反映是全面的、正确的。[4]
这两种理念之间的差异,具体到科技风险沟通中,却导致了大量的误报、错漏,以及十分明显的常识性错误,结果不仅误导公众对风险议题的认知,也影响公众对相关议题的态度与行动。
据此,克瑞弗巴姆(Krieghbaum)在《科学与大众媒介》中将新闻界对科技“真实性”的理解总结为大致正确的报道,只需一般性了解科学研究的主题,并对其形成正确的印象与完整图像即可。[5]这同样也体现在科技风险沟通的新闻报道中。
贝尔(Bell)以气候变迁报道为例,列举了常见的错误报道类型,包括不正确的引述、严重的遗漏、夸大扭曲信息等。[6]SARS发生之后,在一次科学论坛发言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首席科学家曾光教授回忆,SRAS爆发过程中,发现媒体报道传递信息不准确,几次令他陷入被动境地。
而导致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在于新闻价值与科技风险的属性存在冲突。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重要性。杨保军在《新闻价值论》中将新闻的重要性内涵概括为“事实影响人的多少”“事实对人和社会影响时间的长短”“事实影响空间范围的大小”“事实影响人们实际利益的程度”。[7]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风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由于科技风险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普通公众必须通过大众传媒的提醒,才能感知到风险的存在。因此,为了使科技风险更加显著,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相关的新闻报道对科技风险进行夸大,并且片面强调其灾难性的后果,以达到耸人听闻的传播效果。一经夸大的科技风险,首先丧失的就是准确性,因此,呈现在公众面前的科技风险,必然和科学界所认为的具有很大差距。
第二,时效性。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科技风险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之中,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同一议题的科技风险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然而,科学的这种发展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很难有日新月异的变化,短期内研究成果之间的差异非常微小。但受制于截稿日期及竞争的压力,记者以新闻价值的时效性作为标准,往往迅速及时地向公众报道最新的科技动向,由于要做到迅速及时,因此,难以把握科学研究中的细微差别,导致在报道中缺乏准确性。
第三,趣味性。由于科技风险议题牵涉到许多复杂的问题,一般公众很难直接了解其来龙去脉及其关联,必须通过新闻工作者的报道来了解真相。但新闻价值要求新闻具有人情味,且具有接近性,因此,记者使用通俗的语言报道科技风险新闻,使之具有趣味性和相关性,以符合受众的阅读习惯。但是,任何科学都是人类对某一问题认识的理论结晶,同时也是科学家个人脑力的劳动成果。而解读者在理解科学时,都要加上自己的想法,很难保持原貌。[8]因此,记者在解读科技风险的过程中难免误读,最终导致新闻报道中的误报。
2. 科技风险发展的不确定性与戏剧化报道
相对于发展比较成熟的科学传播而言,科技风险沟通最大的特点在于不确定性。也就是说,科学界所关注的这个科技问题尚处于未经证实或者证据有限的状态下,科学家之间也很难对某一议题达成共识;对于议题的数据也不完善或者不确定;科学议题所涉及的事件或情况常包含众多变量,且涉及多门学科等,这些因素导致对于风险议题很难从科学上得出一个结论。也就是说,事情到底会怎么样发展、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危害程度有多大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科学界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这种状况加深了公众理解的难度,因此也增加了科技风险沟通的难度。
而在科技风险新闻报道中,一方面记者为了便于公众理解,另一方面记者自身对议题理解并不透彻,常常将复杂仍充满不确定性的科学资讯简化为确定的、立场对立的或者充满戏剧化的答案,这主要体现为报道对科技风险的碎片化、冲突式和私人化处理。
为了引起公众的注意,记者将科技风险中能够令公众感兴趣的个别议题突出展现出来。例如,近年来,对全球变暖的灾难式后果的议题报道,已viLwDhhhlgoTIeKzS472FQ==经成为当今媒体报道的主要论述,但是,全球变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只是这个议题当中很小的一个部分,因此,这意味着大众传媒的论述仅停留在这个议题的表面,并没将该议题引导进入更深入细致的讨论,并且使得受众对这个议题的理解支离破碎,十分片面。同样的问题也体现在我国媒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报道上。自21世纪初期转基因食品进入公众视野以来,媒体表现出间歇性的报道热潮,但关注点始终聚焦在少数几个议题上,报道内容缺乏对该议题的完整呈现。
此外,为了使新闻具有趣味性、人情味乃至可读性,新闻报道将科学观点之间的争议转化成冲突对立式的论战,如将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简化为“致癌VS不致癌”,将全球暖化及气候变迁简化为“预言VS谎言”,复杂的争论变成了几个对立观点的冲突,公众难以从中窥见事件的全貌,形成偏见难以避免。更为严重的是,鉴于科技风险的抽象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理解上的艰涩,媒体报道甚至将科学家个人也卷入科学观点的争议之中,使得科学观点之间正常交流变成一场私人恩怨。这是对科技风险的娱乐化及“去科学化”,完全违背科技风险沟通的本意。
3. 科技风险消息来源的多元化与平衡报道
由于科技风险的影响面大,影响程度深远,关涉各个层面的利益主体,引起政府、企业界、行业界、公共知识分子、相关专家等的关注。这些主体都试图作为消息来源,透过大众传媒表达自己对科技风险议题的态度,甚至试图影响并主导风险议题的发展方向。而且随着科技风险的全球化,这些消息来源的影响甚至跨越国界呈现在新闻报道中。
记者在报道科技风险新闻时,经常要依赖政府官员、业界发言人,或环保团体代表人为主要的信息提供者。然而对消息来源多样性的需求已在逐渐挑战新闻实务。多元化的消息来源的科技风险报道,比只引述政府或者科学界说法的新闻更让公众有兴趣并让他们感觉更可信。此外,新闻报道展现多元化的消息来源,也出于记者从平衡报道的角度来考虑。“平衡报道”思想出自西方新闻学,是西方新闻报道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1729 年,本杰明·富兰克林接办《宾夕法尼亚报》,他提出“当人们各持异议的时候,双方均应享用平等的机会让公众听到自己的意见”。[9]这一主张被看做是“平衡原则”的首次提出。平衡与客观、全面并列在一起作为重要的新闻原则。
但对于科技风险沟通而言,消息来源的多元化或者平衡报道并不必然意味着对相关议题报道的全面深入。如果新闻报道的内容仅仅对消息来源提供的信息的引述及陈列,或者记者刻意保持客观中立,仅呈现各消息来源对议题的争议,对消息来源的信息的正确性不做评价,则很容易误导受众,令受众无所适从,无法做出理性判断。因此,这种比较适用于社会政治议题的报道方式是否同样适用于科技风险报道,尚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三、促进有效科技风险沟通的媒体报道对策
大众传媒在科技风险沟通中的报道困境,一方面源于报道能力不足,另一方面从表面上看是新闻运作规律与科技风险的属性的冲突,但更深层次原因是大众传媒对市场逻辑的妥协。解决报道能力不足的困境和面对来自于市场竞争压力而导致的困境,都要以“公众理解科学”作为有关科技风险沟通报道的目标。
1. 提高大众传媒科技风险报道的能力
(1)培养记者的科学修养:科学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导致科技新闻报道的难度要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新闻。而科技风险沟通又区别于一般的科技新闻,其重要性及争议性增加了新闻报道的难度。
在科技风险沟通中,记者充当解读者和传播者的角色,公众有关科技风险的知识主要来源于记者。记者理解上的偏差,也会带来公众理解上的偏差。欧美大陆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大学专门培养科技新闻传播人才。而在我国,虽设有新闻专业的大学众多,但学生多以文科为基础知识背景,加上从高中就开始文理分科,文科生的自然科学知识欠缺。这种因教育体制造成的问题反映到实践中,便是记者自然科学基础知识普遍匮乏,更缺乏基本的科学思维方法和科学精神,将科技风险报道作为一般新闻报道处理。因此,培养记者的科学修养应当从教育阶段开始,可在开设新闻专业的大学中专门设置科学传播相关专业。此外,记者报道科技风险新闻的过程中,应多与科学界进行深入的沟通,尽量全面完整了解科学议题。
(2)探索科技风险沟通的报道规律:大众传媒有关科技风险的报道,不能仅停留在令公众知晓的层面上,还应当促成公众对科技风险的深层次认知,最终主动参与科技风险的对话。大众传媒是科技风险沟通的号召者、协同者和资源整合者,在大众传媒所构建的这个平台上,政府、行业组织、公众、科学界共同针对科技风险进行沟通,反馈意见,以加深彼此理解,了解各方看法,达成共识。因此,科技风险沟通考验了大众传媒的报道能力,也对大众传媒所遵从的传统的新闻报道的方法、技巧,乃至原则提出挑战,大众传媒不得不改进甚至探讨适合科技风险沟通的报道规律。比如,如何使得科技风险沟通既能满足新闻价值的要求,但又能兼顾科学的准确性、全面性和客观性?如何在面对众多消息来源的情况下,既做到平衡,能使多种声音都有机会在媒体上展示,同时又能保证科学理念的正确性?此外,用于科技风险沟通的媒体报道形式也需要探索创新。由于科技风险的理解难度大,渊源深远,除日常性的动态报道外,相关的深度报道及专题报道是比较理想的报道形式。如何使科技风险议题既有深度又有可读性,使得公众从知晓阶段跨入理解乃至行动,这些问题都需要媒体在科技风险沟通报道的实践中不断探索。
(3)融合多种媒介传播渠道:科技风险沟通的效果也得益于相关报道在公众中的覆盖面。在新媒介加速发展和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传统意义上单一的大众传播媒介已不复存在,新形式的大众传媒以纸质、网络、手机、公共视频等多种载体向受众传播全方位资讯。相对以往单一的传播渠道,这种融合传播渠道扩大科技风险沟通报道的覆盖面,使得具有不同媒体接触习惯的公众都能够接收到相关报道。但是,融合媒介的特殊性同时带来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例如,如何使科技风险沟通内容结合各种媒介的属性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如何利用新媒介的互动特性加强公众的科技风险沟通中的反馈及参与等等。
2. 培养公众理解科学的能力
英国皇家协会于1985年发表的报告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令“公众理解科学”这个概念进入传播学研究视野。英国公众理解科学教授约翰·杜兰特博士认为,“公众理解科学”的概念应当由三方面组成:1. 对科学知识的理解;2. 对科学的研究方式的理解;3. 对科学到底对推动社会发展是如何起作用的理解。[10]前两个方面是第三个方面的基础,而第三个方面不仅包含科学对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的了解,同时也指对科学带来的风险的正确认识。西方研究者进一步认为,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不能局限于对科学知识和科学事实的认知,更应当了解并监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应用。这些理念正好与科技风险沟通的目标相契合,科技风险沟通的目标也遵循“了解”“认知”和“参与”的路径,强调公众在其中的对话能力。
但是,这种理性参与型公众需要通过大众传媒的积极培养才能得以形成。媒体与受众相互影响,媒体以“把关人”的角色对传播内容进行选择取舍,决定公众接触信息的范围和深度。美国学者乔治格伯纳等人提出的“培养理论”也认为,大众传媒对公众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作用。然而,在市场化运作环境下,大众传媒重心过多倾斜于市场和经济效益,以娱乐受众为核心,迎合偏多,引导偏少,更妄谈培养,因此导致公众对科技风险的关注仅停留在“了解”阶段。所以,大众传媒应当以“公众理解科学”作为科技风险沟通中的报道理念,尽量在市场逻辑和社会责任之间寻找一条折中道路。这就意味着大众传媒主动投入更多的力量培养专业科技风险记者,使记者报道内容深入严谨,具有评判科技风险言论的能力等。
大众传媒所倡导的科技风险沟通的目的在于,基于人类文明以追求进步为诉求的前提,在科学传播与风险评估之间,取得一个成熟的科学文化,以确保怀疑的态度不是代表一个僵化的教条精神,而是透过一种批判的态度,试图追求永续发展的人类文明。[11]作为大众传媒科技风险沟通重要手段的新闻报道,其品质直接决定该目的能否达到。新闻报道的品质一方面取决于大众传媒在实践中对报道规律的探索及报道方法的创新,另一方面取决于大众媒体在科技风险沟通中的社会责任意识,大众传媒不仅要强化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同时也要强化社会各界在科技风险中的责任意识。
参考文献:
[1] Beck U.Risk Society:Towards a New Modernity [M].London:Sage,1992.
[2] Allen S.Media,Risk and Science[M].Berkshire,UK:Open University Press,2002.
[3] 谢尔顿·克里姆斯基,多米尼克·戈丁尔. 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4] 杨保军. 新闻真实性简论话语新闻及其真实性[J]. 今传媒,2005(7).
[5] Krieghbaum H.Science and the Mass Media[M].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1967.
[6] Allan Bell.Climate of opinion: public and media discourse on the globe environment [J].Discourse Society January,1994 vol.5.
[7] 杨保军. 新闻理论教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8] 陈建国. 科普工作必须要求科学性与准确性[J]. 高科技与产业化,2008(Z1).
[9] 孙旭培. 新闻学新论[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10] 李大光.对《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解[N]. 中华读书报,2005-04-23.
[11] 苑举正. 科学传播、风险与怀疑论[J]. 现代哲学,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