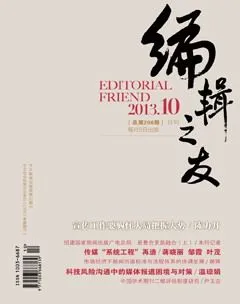元代语言文字政策与多语种出版的繁盛
摘要 元代形成了中国出版史上最为繁荣的多语种出版格局,在中国出版史上绝无仅有。而这一极具时代特色的出版格局之所以会出现在元代,与元代统治者实施的一系列语言文字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畏兀儿字的推行、八思巴字的推广和“国字副之”的语言政策的颁布实施,共同促进了元代多语种出版格局的形成。。
关键词 元代 出版 语言政策
许晋,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王枫,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姜德军,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本文系2011年度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多元文化体系下元代族群的语言竞争与选择”(2011C074)、2009年度内蒙古自治区文史哲基地项目“蒙汉语言接触研究”的中期成果及内蒙古大学“语言与民族文化”创新团队阶段性成果(NSJY0912)。
元朝蒙古统治者统一中原后,建立了大元王朝,他们面临着多民族共存、多种语言文字共存的局面。为巩固在中原的统治,蒙古统治者对新王朝的社会通用语言文字进行确定,对不同族群的语言地位进行规划,并颁布了一系列语言政策与语言法规。这些政策和法规,对中央政府引导和协调各族群间的语言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出版史的角度看,这些语言文字政策和法规的确立,也对整个元代的出版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中国出版史上最繁荣的多语种出版格局。
多民族语言文字广泛用于元代出版业,在中国出版史上绝无仅有。而这一极具时代特色的出版格局之所以会出现在元代,与其统治者实施的一系列语言文字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畏兀儿字的推行与畏兀儿蒙古字图书的繁盛
蒙古统治者最早的语言政策是成吉思汗确立的。他命塔塔统阿教授太子畏兀儿字,首次确立了畏兀儿蒙古字的官方语言地位。蒙古先民本无文字,蒙古国建立后,虽曾使用文字,但多借自其他民族,“行之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行之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则用汉字”。[1]1204年,铁木真在征服乃蛮部落的战争中,俘获了乃蛮太阳汗的王傅兼掌印官塔塔统阿。塔塔统阿生性聪慧,精通畏兀儿文字,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于是成吉思汗“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儿字书国言”。[2]蒙古民族从此有了自己的文字,“以畏兀儿字书国言”也成为蒙古族群历史上第一次有目的地实施的语言文字政策,蒙古族群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文明时期。
有元一代,畏兀儿蒙古字长期通行于国内,畏兀儿蒙古字成为元代出版史上极为重要的出版语言,被广泛用来撰写本民族历史、文学作品或译写其他民族典籍。如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世袭谱册《蒙古秘史》是蒙古族最早的一部用本民族语写成的官修历史著作,其原始版本就是用畏兀儿蒙古文书写的。此外《金册》(蒙古书名为《阿拉坦脱必赤颜》)、《白史》(蒙古书名为《查罕图克》)、《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等也用该种语言写成。此外,被译为畏兀儿蒙古字的佛教史籍也特别多,如《佛说十二颂》《大涅槃经》《楞严经》《乾陀般若经》《不可思议禅观经》等。
二、八思巴字的推行与八思巴字图书的繁盛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 尊八思巴为国师, 忽必烈交给八思巴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制蒙古新字。至元六年(1269),元世祖以诏书的形式正式颁行八思巴创制的文字,八思巴新制的蒙古字由此成为官方法定的文字,后世称之为“元国字”或“元国书”。自元世祖忽必烈始,元朝十一帝都强制推行蒙古新字“八思巴字”,规定省、部、台、院的官方用语必须是八思巴字,例如宣诏的时候,“读诏,先以国语宣读,随以汉语译之”。[3]还设立京师蒙古国子学及各路教习诸生学习八思巴字,任命专门官员负责推广新字。在元代,通晓八思巴字的人普遍受到统治者赏识,这进一步促进了国语的推广,如“(刘敏)习国语,阅二岁,能通诸部语,帝嘉之,赐名玉出干,出入禁闼,初为奉御”。[4]而“今后不得将蒙古字道作新字”[5]的政策更是强化了八思巴字的唯一合法地位。
八思巴字作为元代官方文字应用了80余年,对元代书籍的出版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首先,为配合推行八思巴文字,政府组织人力编写八思巴字识字课本。成宗元贞元年(1259),《蒙古字韵》《蒙古韵编》《华夏同音》《百家姓蒙古文》等书相继问世,其中《百家姓蒙古文》《蒙古字韵》都是当时的识字课本,是八思巴字和汉文对照的双语课本,在元代的发行量很大。其次,设立学校,推行用“国语”课本教学的语言政策,促使大量八思巴字教材问世。如忽必烈屡次下令将治世安邦的历史典籍和有益于修身治国的儒家经典著作,翻译成蒙古新字,《元史》记载:“帝览《贞观政要》,谕翰林侍讲阿林铁木兒曰:‘此书有益于国家,其译以国语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诵习之。’”[6]以使更多的人学习和运用八思巴文字。元代用八思巴字译写的汉文典籍主要有《通鉴节要》《孝经》《孟子》《论语》《千字文》《尚书》《资治通鉴》《帝范》等,它们作为教材广泛用于京师蒙古国子学和各地学校。第三,颁行八思巴字的诏书中还明确要求,用“八思巴字”译写一切文字。从现存八思巴字文献考证,当时很多语言如汉语、藏语、梵语、维吾尔语等语种的图书均被译为八思巴蒙古语。
八思巴字作为国字被广泛推行,给元代出版业带来重要影响。首先,少数民族语言第一次作为官方出版的核心语言登上中国出版史的舞台;其次,少数民族语言图书数量之多,涉及范围之广都超越前代。可以说,将蒙古国字用之于出版,是有元一代最为鲜明的特色。
三、“国字副之”的语言政策与多语种图书的繁盛
元代用于出版的语言文字多达十几种,包括畏兀儿蒙古文、八思巴字、藏文、察合台文、梵文、西夏文、契丹文、波斯文、粟特文、突厥文、叙利亚文、回纥文、阿拉伯文等。[7]这主要得益于元代相对宽松的语言政策。
相对宽松的语言政策主要体现在忽必烈推行八思巴字时颁布的一条法令:“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其余公式文书,咸仍其旧。”[8]“仍以其国字副之”中的“国字”指各地区原来通行的民族文字。不难发现,蒙古统治者在大力推行八思巴字的同时,并没有对其他语言文字实施太强硬的打压。可以说,“国字副之”的政策给元代多民族语言文字共同发展提供了契机。而八思巴字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导致其推行受阻,无法贯彻彻底,这无疑给多语言文字共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因此,元代各地使用各民族自己的语言进行交际的现象广泛存在,正如陈垣指出的:“盖元制文字用途之区别,虽以蒙古新字为主,而不甚通行,有所颁布,须以其国字为副。大抵汉字用于中国本部,畏吾儿字用于葱岭以东,亦思替非文字用于葱岭以西诸国也。”[9]
相对宽松的语言文字政策,为多语种图书出版提供了生存空间,除官方极力推行的蒙古文图书外,有元一代的回回文、藏文、回鹘文、察合台文和西夏文图书出版业也极为繁盛。首先,回回文字,就是波斯文字,是元代除蒙古文、汉文以外普遍通行的第三种文字。早在大蒙古国时,波斯文即在中土流行。回回文图书内容丰富,涉及天文、历法、地理、医药等多个方面,尤以天文对元朝的影响最为深远,如著名的回回数学著作《兀忽烈的四擘算法段数十五部》《叩些必牙诸般算法八部》由元代秘书监收藏。其次,受元代藏传佛教的影响,藏文成为当时除汉文、蒙文、回回文之外使用最多的图书出版文字,藏文图书主要用来弘扬藏传佛教文化,如藏族高僧八思巴著有《道果法明鉴》《密宗行部所说无量寿佛修行法》《大乘要道密集》等藏文图书。第三,元代高昌回鹘地区主要使用回鹘文。该地区回鹘佛教徒把抄写回鹘文佛经视为一种功德或职业,因此,将藏文佛典译为回鹘文过程中,成就了一大批回鹘文佛教典籍,如写本《吉祥轮律仪》《师事瑜伽》。第四,察合台文是指在察合台汗国广泛使用的一种文字。在察合台文通行的几百年中,大量涉及哲学、宗教、文学等方面的察合台文图书得以流传,如《绿洲之颂》《蔷薇园》《辛迪巴书》等著作都由波斯语译成察合台文。第五,元代还刊印了大量西夏文佛经。如元世祖时期主持雕刻河西字大藏经,河西字即西夏文。有学者作了初步统计,有元一代共印一百九十部西夏文佛经,按每部三千六百二十余卷计算,前后共印六十八万七千八百卷上下。[10]
蒙古国建立后,统治者将语言文字政策视为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颁行了一系列语言新政。语言新政在实施过程中,对元代出版形成重要影响,尤其是译书,其文种之繁,数量之多,范围之广,都超越前代。[11]这正是有元一代出版的最大特色。
参考文献:
[1] [宋] 彭大雄. 黑鞑事略[M]. 翰墨林编译印书局,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
[2] [明] 塔塔统阿传. 元史(124卷)[M]// 宋濂,王祎,赵埙,等. 洪武三年(1370).
[3] [明] 礼乐志一. 元史(67卷)[M]// 宋濂,王祎,赵埙,等. 洪武三年(1370).
[4] [明] 列传第四十. 元史(153卷)[M]// 宋濂,王祎,赵埙,等. 洪武三年(1370).
[5] [元] 礼部四学教条. 元典章(31卷)[M]// 编者不详,北京法律学堂,1908.
[6] [明] 仁宗本纪一. 元史(24卷)[M]// 宋濂,王祎,赵埙,等. 洪武三年(1370).
[7] 田建平.元代出版史[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151.
[8] [明] 释老传. 元史(202卷)[M]// 宋濂,王祎,赵埙,等. 洪武三年(1370).
[9] 陈垣. 元西域人华化考[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0] 许晋. 元代多民族语言文字图书形成探析[J]. 中国出版,2013(2).
[11]来新夏. 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