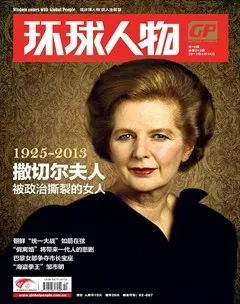谦谦君子木心
最近木心的《文学回忆录》很火。频登各大好书排行榜,报刊上也多有讨论文章。木心最早的一批读者应该记得,2006年国内就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作品《哥伦比亚的倒影》,使他以79岁的高龄及新人的身份现身当代文坛。
木心是谁?香港评论家梁文道说,当木心的作品刚刚在台湾发表时,整个文艺圈都在探问,是不是哪位民国老作家重新出山;而大陆出版他的书后,大家又以为他是台湾或海外作家。木心的文字古典优雅,确实有民国文人的气脉。回头去看他的履历,印象却有不同。
1927年,木心生于浙江乌镇,师从刘海粟、林风眠学习绘画,同时痴迷于文学。他学写意识流,探讨叶芝、艾略特、普鲁斯特。“文革”中被捕入狱,作品被焚毁,3根手指被折断,却还在牢房里偷偷写手稿,在纸上画下琴键弹奏莫扎特和巴赫。“文革”后平反,1982年旅居美国,从事美术和文学创作,逐渐获得声誉。
上世纪80年代,木心以其“迥然绝尘”的文字风格征服了大批海外读者。80年代末,出于对多数“文革”后出国的年轻人对文学几乎什么都不知道的惊讶,木心在美国讲了5年的世界文学史。学生中,就有认真细致做笔记的陈丹青。直到新世纪,木心在一批作家的推介下终于与大陆读者见面。2006年,他的第一本书出版,同时受邀回国定居,在乌镇的一所院落里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岁月。2011年,木心去世,再次掀起阅读热潮,直到2013年,陈丹青整理的听课笔记《文学回忆录》出版,这股热潮仍未散去,反而引发更多关注。
说木心的文字,得从他的外貌说起。他是个爱漂亮的人,宣称“人是可以貌相的”。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木心所有的照片,都衣着体面,器宇不凡。流传最广的一张照片上,他戴着礼帽,穿着长大衣,系着围巾,拄着文明杖,绅士派头不输于明星。《文学回忆录》的封面就是一顶礼帽,因为陈丹青认为这是木心的“符号”。
礼帽所代表的优雅、从容一如木心及其文字。他有着极深的美术、音乐素养,谈起文学来也是打通了说。古今中外的艺术在气质上经常有不谋而合的地方,木心都能敏锐地找出来。他将杜甫的《登高》比作贝多芬、勃拉姆斯的钢琴协奏曲;认为“李商隐如果活在19世纪,一定精通法文,常在马拉美家谈到夜深人静,喝棕榈酒”;“托尔斯泰的《复活》,笔力很重,转弯抹角的大结构,非常讲究,有点像魏碑”。他将通感运用到了极致,把语言和色彩、音乐、气味、味道的相通之处一一点出,却不深入,让人若有所悟,但不能言传,达到“欲辨已忘言”的状态。
木心的《文学回忆录》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不是学院派的文学史,而是他的私人文学回忆录,满是思维灿烂的火花。梁文道说:“大部分一流作者的文学史,其实都是他们的自我定位。”因此,我们看它,看的也就是文学史里的谦谦君子木心。
木心爱陶潜,认为自己与陶潜相似,“文笔、格调,都有风的特征”,轻拂而过,不着痕迹,水面却起了涟漪。读《文学回忆录》,正是“有风自南,翼彼新苗”。2013年的春天姗姗来迟,有股叫木心的清风,吹面不寒,来得正是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