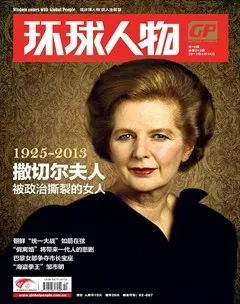林中树 8次进京留住老音乐
从北京入河北廊坊,深入固安县城,再顺着田间道路进入屈家营村,在各个车站间辗转换乘,竟用了4个小时,赶到村口时已近中午了。74岁的林中树正站在村口牌楼下,揣着两手佝偻着背。后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才知道,在尚未转暖的天气里,他不肯到屋里坐着,在村口执着地等候了一个小时。
1986年至今,林中树令濒临消亡的屈家营音乐会得以保存,并发扬光大,成为与西安仿唐乐、湖北编钟乐、北京智化寺音乐并称的中国四大古乐“活化石”。2012年,他还与美国民族音乐学学会创始人布鲁诺·内特尔、青春版《牡丹亭》制作人白先勇以及印度西塔尔琴大师拉维香卡共同获得了首届太极传统音乐奖。
采访前,记者和他通过数次电话,每每在通话结束前,他都会操着浓重的口音叮嘱:“3月28号的屈家营音乐节,一定要来啊。”
从小在悠扬的鼓乐声中长大
“没有老林,就没有屈家营音乐会。”村民们跟外人提起这个音乐会时,都不忘加上这句话。
屈家营的鼓乐源于元明之际的寺院佛教音乐,由管、笛、笙、云锣等传统乐器参与演奏,主要用于祭祀和丧礼仪式。曲子既有北方音乐的古朴粗犷,又兼备南方音乐的婉转清幽,靠着口传心授,已经流传了几百年。每年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这天,屈家营村都要举行盛大的音乐节会。到了上世纪60年代,屈家营音乐节却被认定为“糟粕”。1965年,音乐会戛然而止。
1986年年初,一些乐师找上时任村生产队长的林中树,“我们还想吹,又怕犯法,你这个村干部要是批准了,咱村音乐会就再恢复起来。”20年风流云散,很多老乐师早就去世了,剩下的这些人,最年轻的也年近六旬。
林中树是一个普通农民,1940年出生,没上过学,只是在扫盲识字班里识得几个字,但他从小是在悠扬的鼓乐声中长大的,对乡土文化十分热爱。可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还不怎么开放,“文革”中“破四旧”仍让人们心有余悸。当了多年村干部的林中树也被这事难住了:“我去问问,请示好了咱再吹。”村里、乡里、县里最终没能给老林一个明确的表态,“那干脆我上北京问去!”
老林扛着个包袱,在北京车水马龙的大路上瞎转,一抬头,居然看见了中国木偶剧团的牌子。老林进去跟那里的工作人员比划了半天,那人表示爱莫能助:“我们这是演木偶剧的,您说的鼓乐,我们实在不懂。”老林退出来,心里琢磨,找音乐方面的应该就没错了。他连问带摸索,找到了北京音乐厅。这回,人家告诉老林:“你这个事得找管理部门。”虽然没找对门,但算是给老林指了条路。后来,他又找到北京市文化局、群众艺术馆……还是没什么结果。绝望了一阵后,老林再次来到北京。这一回,他去了当时位于柳荫街恭王府的中国音乐学院。在那里,老林遇到一位名叫冯文慈的教授。冯教授问他:“你能不能给我演一段?”老林急了,他对鼓乐是一点儿不懂。“别着急,你先回去,下周二带着会演的人再来。”到了约定的日子,老林带了几个乐师来了,一吹不打紧,冯教授听后异常兴奋:“你们这不是‘四旧’,不仅不是‘四旧’,还是中华民族艺术的瑰宝。”为了这个结果,老林已前后跑了8趟北京。
走进了高雅殿堂
1986年3月28日,村里迎来了中国音乐学院的考察组。著名音乐家乔建中也在此列,并深感震撼,他在《守望者们的情怀——“屈家营音乐会纪事”》中写道:“在我们翻检‘民国三十七年’的手抄谱、观赏古老的玉制管、双架云锣、传统笙,特别是聆听农民乐手们奏出大曲《普安咒》的一刹那,惊奇、震撼、兴奋之情充溢于每个人的心间。所惊奇者,数百年前的民间音乐,竟然这般完好地保留在这个并不封闭的普通的平原村落的农民乐社中;所兴奋者,虽屡遭劫难,但国宝犹存,乐在民间。”
为了感念中国音乐学院对屈家营音乐会的认可,林中树与村里人决定将3月28日这天定为和中元节等同的音乐节。“起初叫‘明白节’,代表从这天起我们明白了音乐会不是‘四旧’,而是‘国宝’。后来又改叫‘复兴节’,寓意着我们的音乐会名正言顺地走向复兴了。”老林对音乐会的每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
随着前来考察和观摩的人越来越多,2006年,屈家营音乐会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一时间,这个原本空旷的村庄,竟也显得局促起来。“那时候,路可不像现在这样,”老林指着脚下平整的水泥地说,“都是土路,又窄,不好走。”那几年,老林没少为修路的事情奔忙。现在,不仅柏油路铺到了村口,村里还建了一座四合院式的音乐厅,并保存了迄今所能收集到的所有屈家营音乐会的历史文献和古乐器。
1987年,屈家营音乐会古朴优雅、明晰隽逸的乐声在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厅响起,这是屈家营音乐会第一次走出村庄,走进高雅殿堂。而这仅仅是个开始,1989年,音乐会又获邀到“北京大观园庙会”演出;1990年,音乐会献演第十一届亚运会;2012年,他们更是获邀赴台,让古老的乐声抵达海峡对岸……“这些活动都是老林给张罗安排的。他不是一般人。”一位乐师这样告诉记者。

用奖金建个基金
2013年3月28日,记者看到的已是第二十七届屈家营音乐会。木质的雕梁画栋之间,玫瑰色的金丝绒幕帘高高垂下,衬出几分古朴庄重。一米来高的舞台上,一字坐开12位乐师,他们身着宽袍广袖的金黄色衣服,头戴仿古高帽。《普安咒》鼓声响起时,是这一天的正午,那庄重的乐声徐徐而出,时急时缓,强劲的鼓点直击心灵……再细看那些乐师,12人中,大半 是60多岁的老人。
“传承难哪,眼看着就没人了。”林中树耷拉着眼皮叹了口气,顺势吐出一口烟,袅袅不散。音乐会一结束,记者到了老林家,他从里屋抱出两大沓古谱集铺开。那纸已经泛黄变脆,边沿只能勉强粘连在一起。老林翻页时极其小心,“这都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有年头了,你说不传下去咋办?”
这话说的是老林的心声。在纯粹靠田吃饭的过去,秋后一挂锄,村里人便有整个冬天的闲暇,音乐会里的授徒活动就在这时展开。一个老乐师跟记者讲:“那时候,我们去师傅家学,一吹就是好几个小时,也不是为着钱,就是个喜欢。到了晚上,师傅家管一碗菜汤。”随着老一批乐师们相继离世,现在乐队的构成,60岁以上的占一半,年轻的占一半,但是凑起“半棚”(12人)还可以,凑齐“满棚”(24人)还真是难了,靠着口传心授存活的技艺眼看后继无人。
“招些在附近厂子里上班、每天能回家的青年人,晚上教他们乐谱和演奏乐器。长此以往,一代代新人就能培养出来。”林中树这样计划着。于是,他叫上音乐会现任会长胡国庆,登门去做工作:“下了班来,不耽误白天挣钱;学点东西,艺不压身,还有机会到处去演出见世面……”去年冬天来学的那几个年轻人,最后都出去打工了。不过,老林并不气馁,今年他打算再招些年轻人。
“还是得想办法让这个事有个支撑。我想用我得太极音乐奖的那30万元奖金建个基金,再向社会募集一点儿,至少每天晚上能管学徒们一顿饭。另外就是看能不能把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下来。”在他那刀刻般的皱纹里,看不出太多表情,但每说上一句话,他的声音里都是沉重的喘息声,“这不是也有脸回去见祖宗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