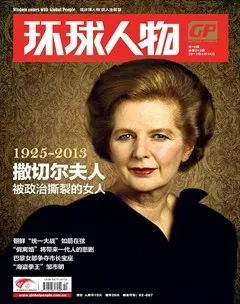教育不公平为何屡拖不决
微博上,一张房地产中介的价目表正在广为流传。因靠近一所全国重点小学,北京五道口的一处37平方米学区房,竟挂出了“10万元1平方米”的售价,被网友评价为“住不进学区房,上不起重点校,秒杀了未来梦”。
而因尘肺病打了3年维权官司的矿工蓝田忠,几天前刚刚拿到7.3万元补助金。他的话让人心酸不已:“我的命换来了娃娃们上大学的机会,至少他们不用再跟我一样了。”
教育,公平,梦想,未来……这些词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牵动着人心,给人希望,又让人焦虑,更加道出了现实的严峻、政府面临的挑战。
就在今年两会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宣布,“教育公平是我们国家这5年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情”。的确,5年来,无论是惠及1.6亿学生的免费义务教育,还是每年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近8000万人次,抑或是让3000多万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吃上免费营养餐,在解决教育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上,政府的投入力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但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最好”,是建立在过去欠债太多的基础上;这样的“最好”,正因为优质教育资源市场化、权贵化而稀释。实现了“让每个孩子都能接受义务教育”后,在教育资源的公平享有方面,鸿沟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
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次记者见面会就提及一个例证:名校里的寒门子弟比例,在这30年里不断下滑。“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那么,教育领域的不公平为何屡拖不决?
初看上去,这似乎归咎于个人和家庭的“客观”因素:条件不好,收入有限,上不起各类兴趣班提高班,进不了重点小学、中学,知识结构相对单一,无缘各种加分特长,自主招生的考题也是闻所未闻……然而,这些因素里,有几项与寒门子弟自身的智商、能力、勤奋有关?这些“客观”里,何尝不是中国现下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的直接反映?靠父亲拼了老命才换来7万元钱勉强上得起学的农家孩子,如何与一个买得起10万元1平方米的学区房、进得起全国最好小学的孩子竞争?在流行“拼爹”的时代大背景下,教育公平成了底层孩子遥不可及的梦想。
这样的现象无法让人漠然置之,因为它危及的是整个中国梦的实现。今天,人们公认“美国梦”的吸引力,羡慕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可以凭借个人奋斗获得地位、财富,但恐怕少有人知道,“美国梦”后面,发生过一个著名的教育平权运动。
1964年,美国国会通过《公民权利法》,规定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在招工、入学、企业竞争中受到“优先照顾”。这项政策甚至让白人学生认为受到了“反向歧视”。1972年,被加州大学拒绝的白人学生艾伦·贝基发现该校当年录取的16名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学生中,大部分人成绩不如自己,他一怒之下把加州大学告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虽然判定加州大学必须录取贝基,却认为大学“有权实行一些使学生来源多元化的政策”。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更是指出:“美国黑人的经历与其它族裔群体的差别不是程度上的,而是本质上的。”弥合这种差别,就必须让强势群体将自己的一部分利益让给弱势群体,在激烈的自由竞争中,“让落后者先起跑”。
中国的国情与美国当然不同。但同样面临教育公平,同样需要“让落后者先起跑”。从效率的角度看,一个社会越能唯才是举,这个社会就越有竞争力;从公平的角度讲,教育的公平给了穷人靠自己奋斗改善生活的机会,自动缓解了贫富分化,从而减少了政府救助的必要。
卢梭说,“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最伟大的工具”。当年,大量农村学生通过接受教育,“鱼跃龙门”,看到了向上的希望,成为支持改革的最坚定力量,也成就了活力四射的中国。现在,梦想在召唤,改革再出发,用好教育公平这一“伟大工具”,将再度激发这股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