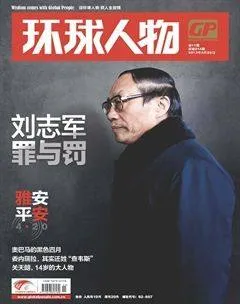北京H7N9患儿一家:我们没那么害怕


4月17日下午,北京地坛医院新闻发布厅,里三层外三层的长枪短炮围成了半圆形,近百名记者严阵以待——北京市首例确诊的人感染H7N9禽流感患儿圆圆已治愈,将在这天出院。
“最佳表现奖”
门口,圆圆正走进来,忽然,小小的身子顿了一下——连日住院让她习惯了身边充斥着陌生人,但今天这阵势,显然让7岁的她有些胆怯。她本能地看向身后的父母——夫妻俩拉住圆圆的手,给她鼓励。一家三口都戴着口罩,但从眼神来看,圆圆满是好奇,而父母则在微笑。
“为什么还戴口罩?”有记者问。“出于对孩子隐私的保护,大家一致决定全家戴口罩出席,既满足了媒体的知情权,也不会让孩子完全暴露在公众视线下。”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钟东波解释说。
不约而同地静默了数秒后,记者们开始按动快门。一瞬间,闪光灯连成一片。
“现在感觉怎么样?”
圆圆用很清脆的声音说:“好多了。”
“圆圆,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奖状。最佳表现奖。”这是陪伴圆圆数日的主治医生和护士们为她做的。“圆圆是个开朗懂事的孩子,这么小就知道要好好配合治疗。这是为了表扬她!”一直守护在圆圆身旁的杨护士告诉记者。
或许是被闪光灯闪了太久,圆圆低下头,拼命揉眼睛。所有闪光灯又在一瞬间,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
“现在最想干什么呀?”有记者蹲在圆圆面前和她聊天,语气里满是怜爱。
“回家。”
“回家干什么呢?”
“玩。”
童言无忌让人群爆发出一阵欢笑,圆圆的眼睛也成了两个小月牙。
3分钟不到的见面会一结束,圆圆便跟着父母走出了报告厅。走进地库,坐上车,圆圆的爸爸姚先生吐了口气,这是一家人几天来头一次独处。“咱回家喽!”他大声吆喝了一嗓子。
快,成了治愈的关键
坐车回家的路上,姚先生不时朝后视镜看看——女儿依偎在妻子怀里撒娇,妻子则摩挲着女儿的头发。回想过去的几天,简直像一场梦。
4月11日早上6点,跟往常一样,姚先生叫女儿起床上学,妻子正忙着做早餐。圆圆却懒懒地不肯起,“爸爸,我难受,没劲儿。”
姚先生摸了摸孩子的额头,不烧,但确实是看着没精神。圆圆经常感冒发烧,一般就在家吃点药,烧得厉害了再去医院。但这回,姚先生不敢大意。姚先生一家三口住在顺义区后沙峪镇古城村中心街一间20平方米的门脸房,以贩卖活禽为生。连日来关于H7N9的报道让他多了个心眼,但内心还是存着一丝侥幸,“觉得这事不会落到我们头上”。
8点,夫妻俩把孩子送到了地坛医院,并向医生说明了自家贩卖活禽的情况。一个小时后,圆圆出现了发烧症状:38.2℃,之后逐渐加重,中午12点被推进隔离病房。夫妻俩作为疑似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也被送进病房接受观察。
与此同时,各项化验紧张有序地进行。当天,医生两次对圆圆采集标本进行检测,并发现第二次检测时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12日凌晨1点50分,医院上报朝阳区疾控中心,3点,标本被送至疾控中心。10点,朝阳区疾控中心确认阳性,并送至北京市疾控中心进行复核检测。下午3点半,北京市疾控中心检测发现阳性,再将样本送至国家疾控中心进行复核检测。13日凌晨,圆圆被最终确诊为H7N9病例。
地坛医院第一时间发布了这一消息,全城哗然。处于隔离状态的姚先生也得到了这个消息。一位医生告诉他:“确诊了,但是别害怕,我们对这个病有信心,你也要有信心。”牵挂,成了最重的思绪。为此,护士们当起了“信使”,给一家人“传纸条”。圆圆在纸上写道:“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给圆圆回信:“宝贝,听阿姨的话,过几天我们就回家了。”
“其实,我们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害怕。当时,圆圆已经在医院了,身边都是医生护士,我觉得他们比我还紧张。而且全社会都关注这个事,好像分担掉了我的一些压力。”姚先生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说。
病房外的气氛则紧张得多。“患儿病情是比较重的”,呼吸科权威专家、此次救治专家组组长童朝辉事后回忆说。圆圆入院后的最高体温达到了40.2℃,呼吸急促,肺炎症状,淋巴细胞检测显示她的免疫功能已经降到了很低的程度。
发病的第十五个小时,圆圆用上了抗病毒药物达菲,以及银翘散、白虎汤等中医治疗方法,病情迅速得到控制,各项生命体征趋于稳定。两天后,圆圆彻底退烧,转入普通病房,之后两次检测结果均显示阴性——这意味着圆圆已经达到了治愈出院的标准。
直到新闻发布会前几分钟,圆圆才从病房出来,一看到爸爸,就搂着他的脖子哭了。
父亲心里最大的顾虑
车进入古城村中心街时,圆圆开始兴奋起来,扒着车窗朝外望。就在几天前,街两边还是卖菜、卖肉、卖水果的小摊,非常热闹。圆圆被确诊为H7N9病例后,这里的小摊都被清理了,显得有些冷清。一张张“莫惊慌 要关注”的宣传广告随处可见,每天按时喷洒的消毒水味道弥漫在空气中。
车子拐进小路的时候,已经可以看到家的大门。家门前,还守着三四个保安,圆圆得病以后,就有几个人天天坐在他家门口,不让外人接近。不过这会儿他们的装束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口罩没有了,制服也换成了便装。姚先生一直盼望着女儿能平安回家;可真的回来了,女儿的处境,又成了他最大的顾虑。“人家说点儿啥,咱大人都过得去。但小孩不一样,你不知道班上的孩子会怎么对待圆圆,圆圆对那些话是不是能接受。”
他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此前,南京市一名H7N9感染者许某的丈夫希望卖房救妻,然而,许某的姓名、住址以及发病和治疗过程被人在微博上公布,他们全家因此遭受歧视,“30多万买来的房子1万元也没人要”。还有一户患者的家属更是遭到了小区邻居们一致、自觉的隔离和排斥。
所幸的是,这样的事没有在圆圆一家身上重演。圆圆所在学校的校长和班主任来了,他们告诉夫妻俩,学校会做好保护措施,尽最大努力避免对圆圆不利的事情发生。
房东和左邻右舍纷纷来家里看望圆圆,而让这一家最感动的是:他们都没戴口罩。“人家不排斥你,不防着你,还愿意和以前一样跟你亲近,对我们刚经历过这件事的人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姚先生再次表现了他的乐观,“事情就是这样,要是你觉得很多人在帮你,和你一道儿想主意,那就真不害怕了。”
当地政府送来了米、面、油,圆圆家的生活暂时不用发愁。但这场目前尚无定数的禽流感,让他们赖以生存的营生彻底陷入遥遥无期的搁置中。整个古城村503只存栏活鸡被扑杀,涉及51户村民。未来何去何从,不仅是圆圆家,也是不少人要面对的问题。“我这几天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决定留在北京,圆圆就是这儿出生的,她最习惯这儿。不过,我以后不做这个生意了,盘算着做点儿别的。”姚先生顿了顿,“总能想办法过了这关,养家糊口应该没有问题。”
“说到钱的问题,我想起个事。我还得问问医院,圆圆治病的钱是多少,谁给付的。当初问医院,医院说这事不用我们操心。但是我想着,我们至少得知道,是谁帮了我们这个忙,人家花了多少。”姚先生很坦诚地告诉记者。他或许还不知道,4月17日,北京市卫生局拨付了人感染H7N9禽流感防控救治专项经费,其中市疾控中心300万元、北京地坛医院200万元、北京佑安医院100万元,主要用于购置救治工作所需物资及垫付患者救治费用等。
此前,南京、安徽患者家庭为看病倾家荡产引发了公众的讨论:H7N9是个人卫生事件,还是公共卫生事件?用公共财政为患者治病是否合情合理?最终的解决方案是,把H7N9加入医疗保险的报销行列,同时,医疗合作基金也提供相应的保障。在抗击H7N9中碰到的实际问题也在倒逼制度改革。
回家的第二天,圆圆一家三口的生活似乎回归了平静。下午阳光很好,圆圆时而跳到门前,围着父亲撒娇玩耍,时而跑出去,还踢起了毽子。不一会儿,父亲又赶紧唤她回屋。
10年换来从容不迫
“我是从圆圆确诊开始,每天就守候在医院了。”在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位同行告诉记者,“对我来说,在圆圆出院时看看她,已经不再是从职业角度考虑了,而是让自己心里有个安慰——亲眼看到孩子好好地出院,好像心里才踏实了。”无疑,圆圆以及其他治愈出院患者的平安健康,对于一个家庭而言是圆满,对于仍在接受治疗的病人而言是希望,对于公众而言则是一种自信的力量——正视疾病,并战胜它。
回顾过去的一个月,H7N9如一团乌云,笼罩在每个人的心上。
2月19日,全国首例H7N9患者、上海87岁的李某发病住院;2月26日,疾控系统进入临战状态,展开对新型病毒的检测工作;3月1日左右,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确认不明病例“是甲流,但不是任何一种已知甲流”;3月10日,H7N9被初步捕获;3月22日,上海市疾控中心将标本送至国家疾控中心;3月29日,国家疾控中心完成病毒基因测序,确认新型病毒;3月31日,卫计委向社会发布疫情。
之后的日子里,每日疫情通报、接治医院新闻发布会等制度化的措施,保证了信息及时公开;4月2日、10日,卫计委相继制定印发两版《人感染H7N9禽流感诊疗方案》,治疗方案得以及时更新;在达菲等抗病毒药物外,4月5日新药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上市……
“与抗击非典时的慌乱无序相比,中国政府抗击H7N9做到了从容不迫。”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项目部主任刘远立说。
人类与疾病的抗争,永远都是一个从无知到有识的过程。回望10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初春,非典肆虐。消极慌乱的应对措施,最终造成上千人感染,数百人离世。
也正是因为非典,及时透明的信息公开、制度化的程序应对成为这10年来公共卫生事业最显著的变化。2003年5月7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颁布,标志着中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纳入了法制化轨道;2006年1月,《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发布;2007年8月,《突发事件应对法》出台;同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今天,我们在应对H7N9禽流感疫情的从容有序,无不有赖于制度的保障。
10年来经验的积累,对防控H7N9的有序进行帮助很大。杭州上城区疾控中心副主任叶俊杰以口罩为例做了个对比,“10年前非典疫情时,经常可以看到有些工作人员将两三个口罩叠在一起戴;但10年后的今天,我们会使用专业的N95防护口罩。”
不可否认的是,仍有不少地方值得我们反思与改进。媒体人邓海建指出:“首先是权威指导不能语出多门。10年前神乎其神的板蓝根,而今焕发‘第二春’,这是科学理性的尴尬。疫情当前,政府怎么说、专家怎么讲,很可能是重塑抑或撕裂公信的分水岭。其次是疫情之下的成本核算与危难救急问题。家禽养殖户的巨额损失,商业保险等如何常态介入,眼下是个值得思考的契机。”
1957年,美国公共卫生专家勒罗伊?伯尼曾说:“如果流行病没有发生,我们都很高兴。如果发生了,希望我们能说,我们已经在现有科学知识与行政程序的极限下,做了所有的事情并做了所有的准备,以求达到最好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0年间,我们一直在进步;而未来,挑战一直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