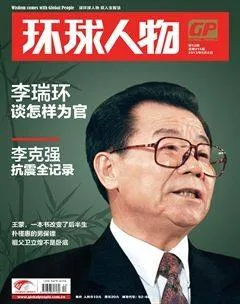记者刘易斯,比法官还懂法律


《一九八四》的作者乔治·奥威尔把“自由”一词解释得浅显易懂,他说,“自由,至少意味着这样的权利:别人不想听,你照样可以说。”这是一种文学性的表述。意大利著名学者布鲁诺·莱奥尼对“自由”的定义则是:“自由是、并且可能首先是一个法律概念,因为自由必然涉及一整套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对“自由”的讨论几乎是当代学者的永恒命题——不思考这个命题,似乎就显不出多么有深度。但事实上,对此真有独到见解,并能精准地阐述出来的,实属凤毛麟角。
4月底,由国家图书馆发起的文津图书奖揭晓,安东尼·刘易斯的《批评官员的尺度》(副题:《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赫然上榜。作为“新闻自由的里程碑”,“《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一直是大学新闻系和法律系课堂上无法跳过的经典案例;而作为一本翻译于2011年的书,它至今仍是中国读书界的阅读热点。
一开篇,刘易斯就先讲了这家百年老报的危机:1960年,南方民权运动正在紧要关头,马丁·路德·金的支持者们在《纽约时报》刊出了一份政治宣传广告,指责官员们正采取非法手段破坏民权运动,但文中对事实有所夸大,增加了金被逮捕的次数,修改了虐待事件的具体细节。
这则广告没有指名道姓,但还是激怒了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局负责人沙利文,他认为这则政治广告极易让人认为他就是其中所指的“南方违宪者”,并起诉《纽约时报》有诽谤罪,要求赔偿50万美元。
陪审团只用了2小时20分钟就做出了结论:判定《纽约时报》败诉。而这次审判的连锁效应更为可怕:南方其他政府官员纷纷提起上诉,赔偿金额无法估算。两审失利后,已到绝境的《纽约时报》,不得不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1964年3月9日,9位大法官对“《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以9票对0票一致通过裁决,宣布“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维护了媒体、公民批评官员的自由。
刘易斯是美国新闻界的“老兵”。1948年进入《纽约时报》工作,历任编辑、记者、主任。1964年,最高法院审理“《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时,37岁的刘易斯正好是《纽约时报》驻华盛顿的跑线记者,专门负责与最高法院事务有关的报道。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站在媒体立场上,渲染绝对的新闻自由,而是结合案件后续发展,对现代媒体的角色进行了全面反思,甚至是自我批评。
作为一名勤于思考的媒体人,刘易斯赢得过两次普利策奖。1955年,因报道一起海军雇员受“麦卡锡主义”迫害事件,刘易斯第一次获得普利策奖。这名雇员也因为这则报道复职。这段故事后来还被好莱坞改编成了电影。
在做了负责报道最高法院的跑线记者之后,刘易斯专门去哈佛学了一年法律。在他之前,负责最高法院报道的都是没有法律知识的记者,写的文章缺乏法律推理与背景知识。刘易斯改变了这一局面,他的敬业让最高法院大法官弗兰克福特都感到难以置信,称赞说:“在最高法院里,能达到刘易斯那样对案件的把握和理解水准的法官,不超过两个。”1963年,他因为对最高法院事务的出色报道,再度获得普利策奖。
2013年3月25日,86岁的刘易斯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的家中去世,最后一刻,他依然在打字机前。
《批评官员的尺度》一书的译者、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何帆说:中国需要自己的刘易斯。的确,刘易斯给新闻界带来的是一种理性的营养——既有理想和激情,又有理性和审慎。他让无数人同他一起思考。
今天的中国适逢微博时代,人人都在其中,有一个问题也许是人人都需要回答的:“给你自由,你能干什么?”
(此书在环球人物杂志淘宝官方商城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