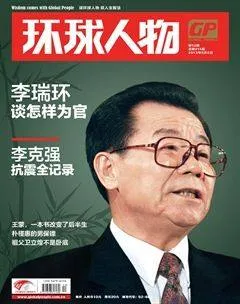郝南,救援队背后的“高参”


4月19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通过微博与卓明地震援助信息小组的负责人郝南取得了联系,他爽快地答应了采访。没想到,第二天四川芦山县发生了7.0级地震,采访被迫中断。
22日,记者再次拨通了郝南的电话。“凌晨3点行吗?我只有那个时候有时间。”“你不睡觉吗?”记者问。“我已经两天没睡过觉了。”记者不忍心郝南如此劳累,采访再次推后。
26日,震后第六天,记者终于采访了郝南,时间是凌晨2点到5点。震后的6天里,郝南只睡了15个小时。
震后一分钟开始工作
“我特别想跟你说说这几天我们做的工作。”电话一接通,郝南就用极快的语速抢占了话语权。后来,他解释说,之所以这么做,是希望采访的重点是他做的事情,而不是他本人。
在郝南的回忆中,芦山地震发生后的一系列快速反应被重现。4月20日8点03分,睡梦中的郝南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电话是卓明地震援助信息小组在四川广元的一个组员打过来的:“地震了,震级至少在6.0以上!”郝南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他迅速通知组内的其他成员在网上集结。
8点18分,卓明微博就发布了一条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4月20日8时02分在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北纬30.3度,东经103.0度)发生7.0级地震,震源深度13千米。”而其他关于地震的微博多是在8点20分以后。
与此同时,更多的组员也参与到工作中来。卓明的核心骨干有10多人,大多是“80后”,分散在全国各地乃至国外。“地震初期运用最多的就是地图,其次是网上收集的各种信息。我们要首先了解当地到底什么情况,初步判断造成的影响有多大,分析如何开展救援,等等。”
正在这些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时,郝南接到了中国民间救援蓝天救援队队长张勇的电话。咨询了芦山震后的基本情况后,张勇问:“蓝天有没有必要赶赴灾区?”“去,一定要去,越快越好。”郝南回答。8点26分,蓝天救援队四川分队就已经集结完毕,准备出动救援。
很快,“免费午餐”发起者邓飞也和卓明取得了联系,“我们是否有必要去灾区?去了之后能做什么?什么时候去?”邓飞得到的回复是:建议“免费午餐”可以在灾后第三天进入。因为震后脆弱的道路系统将是救援的致命伤;陆续奔向灾区的救灾者或将多于受灾者,物资也可能供过于求;3天后,政府的救援物资已经到位,“免费午餐”可以侧重解决没有当地户口、没有身份关系的灾民的吃饭问题。事后的情况证明,卓明的预判是正确的。
中午12点50分,卓明微博上发出了第一期救灾简报,并立即发送给了已经到达或正在前往灾区的救援队员们。之后的日子里,郝南和组员们一起,每天发一期简报。记者看到在最新一期简报中,几千字的文章分成灾情、村组、进程、天气、需求、政府、民间7部分,全面介绍了灾区的最近情况,其中常常标有“已核实”、“信息有效期”等字样。“全是干货,费了好大的劲。”
作为国内目前唯一以专业处理地震救援信息为工作内容的民间志愿组织,卓明的快速和专业广受好评。“这是我们反复演练的结果。”郝南说,“自从汶川地震之后,国内5.0级以上的地震,国外6.0级以上的地震,我们都会发布信息,5年的经验积累才保证了今天的效率。”
信息整合也关系生命
《历史的细节》的作者杜君立这样写道:“在一个信息过剩时代,对信息的梳理和整合非常重要,做一个信息整合者比一个信息创造者更有意义。”5年前,郝南开始意识到这句话的重要。
2008年汶川地震后,众多志愿者赶赴汶川,其中就有26岁的北京大学医院口腔中心医生郝南。在飞往成都的航班上,他问其他志愿者想去哪里帮忙、怎么帮,但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到灾区后,郝南发现,当地根本不缺志愿者,这些都是灾区内外信息不对称所致。
于是,郝南开始了地震信息协调工作。他自己掏钱在成都租了一间房子,作为志愿者驿站,还组建了一个“5·12地震信息QQ群”。
“我是一名医生,本来想最适合干的是救助,没想到却干起了信息整合的活,而且越做越觉得这个事太重要了。”在郝南看来,他们的工作就像搭一座桥。比如,一个企业想提供棉被、食品和水,但他们不知道哪里需要。“我们设法实现这些信息的交换,并保证信息及时有效。”
和之前的几次地震相比,芦山地震后各种求救和寻人启事在第一时间经由微博、微信等各种网络平台散播出来,这既让信息的搜集工作变得简单,又让信息的核实工作变得更加繁琐。4月21日,微博上有大量转帖称龙门乡五星村物资缺乏,蓝天救援队马上送去了一批足够村民消耗两天的物资——郝南他们估计,两天后,该村庄连接外界的公路会抢修好,更多的物资将会输入。不过,这条信息并未在五星村得到救援后停止传播,还有很多网友在连续不断地发帖呼吁,后来郝南等人不得不花费大量气力来一一排除这些无效求助。
在公益的道路上狂奔
如今,郝南的本职工作仍然是北京大学医院口腔中心的一名牙医,最近因为一个项目被派驻到合肥。但一下班,他就成了志愿者。“忙起来你会通宵熬夜,影响第二天看病吗?毕竟你是个医生啊。”郝南笑答:“对一名医生来说,临床就是一线。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在一线注入最充沛的注意力。”
从普通志愿者到公益信息平台的负责人,郝南对自己的行为有独特的认识,“其实就是做了点我该做的事”。“信息整合这块政府方面没有专门在做,我们有点经验,就做起来了。这就比如扫大街,机器再好,也要有人在后面扫边角。”
在郝南看来,“在中国做公益非常尴尬。一方面,它的门槛很高,社会公众对志愿者的道德要求非常苛刻,不允许有任何污点;另一方面,它似乎又没有门槛,任何人想做就做,缺乏引导,而国外对志愿者有严格的要求。”
就在芦山地震的当晚,郝南和一个准备前往雅安的志愿者吵了起来。那名志愿者不愿意参加新人培训,迫不及待要去前方。郝南坚决不同意,“没有经验又不接受培训,去灾区就是添乱!”而在四川当地,郝南的一个组员劝返了1000多名志愿者,累得嗓子都哑了。
记者采访中,郝南接到正在国外学习的妻子徐诗凌的电话,她将会回国短期停留。“我们已经半年没见了,这次排除万难也要见!”郝南开心地笑起来,这是震后最大的好消息了。这对小夫妻是在做公益过程中认识的,2012年,在公布婚讯的微博中,他们这样写道:“各位亲友如赐礼金请转赠玉树、舟曲、望谟、岷县、泸沽湖、涞源及今年其他省二级以上自然灾害灾区重建项目。”
“你现在是一种什么生活状态?”采访临近结束时,记者问。“狂奔,在公益的道路上狂奔。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很多。”郝南热情的声音中带着疲惫,刚刚过去的又是一个不眠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