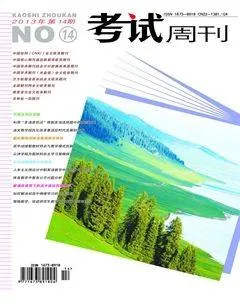语文教学改革刍议
各地的教学方法研究和推广活动层出不穷,但不可否认的是学生对语文课的学习积极性并没有明显提高,我认为教改效果不明显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力度不大。要提高学生对语文课的兴趣,不能仅仅改进教学方法,还应该对教学管理及教材的编写和运用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因为教育改革是一个整体性改革,光改一项是绝不可能成功的。
首先教学管理改革在教改中应当先行一步。吕叔湘先生说:“语文水平的提高主要得益于课外阅读,而不是课堂学习。”由此可见,我们应建立“大语文”教学观,不仅要用好教材,还要跳出教材。但当前课文课上教学内容基本上是以教材为主,因为考试有时也会考到教材中的内容(这一点中考的文方言文阅读特别明显)。即使像高考那样几乎完全不考教材中的内容,教师也必须把教材当做经典,一篇不漏地精讲细练,因为几乎所有学校在开学前都要求教师们制订好教学计划,每学期不定期地对教学进度和内容进行检查,看是否符合计划,并把这种检查作为考核教师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样的束缚下,大部分教师只能以教材为唯一教学内容,以学会教材、解决教材中的问题为教学目标,陷于教材的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学生也亦步亦趋地堕入“迷信教材”的泥潭。于是,教师“死教教材”,学生“死学教材”。如果学校的管理方式不改变,教师就很难摆脱教材的束缚。
教学管理改革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学生的评价机制。现阶段的教育评价仍然是一试定终身,中考和高考往往成为人生的分水岭,在这样的重压下,许多人平时成绩再好而仅仅中考或高考一次考试甚至是一门课的考试发挥欠佳都有可能导致十年苦读毁于一旦,这很明显是不公平的。另外,中考或高考都以总分决定是否录取,许多学生仅仅因为一门课程不好而落榜,这其实是很不公平的。韩愈在《师说》一文中说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人才不一定都是全才,学生精通一种技艺或一门学科也是人才。如当年朱自清在1916年考北京大学时,数学考了0分,最终被破格录取。著名史学家吴晗,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原北京市副市长。这位清华的高材生当年却是被清华破格录取的,并被称为“清华三大才子”之一,可有多少人知道,文史和英语都拿到100分的吴晗数学只考了0分。前不久刚刚去世的钱伟长先生也属于“偏科生”,在考清华大学时历史与国文成绩最好,历史竟得满分,但物理仅得18分。但最终仍然被录取,并且成为物理学巨人。而这与当前大学录取时很多人成绩很好,但只因为一门选修课考了B或C而与“一本”失之交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评价机制使多少在某一门课程上具有特殊天赋的学生对学习失去信心。对全才的追求,使我们痛失了多少人才。
此外,现行的教学评价机制对语文中的“说”重视不够。语文课具有听、说、读、写四大功能,现阶段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对“读”和“写”都非常重视,“读”和“写”所占分值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五甚至百分之百(如上海的高考试卷)。这使大部分语文教师在上课时直接忽略“听”和“说”能力的训练。以前我们曾批评中国的英语教学是哑巴英语,但现在英语中考考口语,高考考听力,英语摆脱了哑巴英语的称号,而语文却走上了这条老路。不少学生家长反映:“小时候很会讲的,人越大越不肯开口。”情况的确如此,据了解,很大一部分孩子在进入初中后,开始不愿或不善表达。以课堂发言为例:小学生最踊跃、初中生寥寥无几、高中生根本不回答,以至于很多高中教师在教学中根本不设课堂提问这一环节。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学生不愿说,老师就不问,老师越不问,学生的表达能力就越差。15岁是孩子语言能力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很多15岁前能说会道的孩子,15岁后变得腼腆而不善言辞。语言专家称之为“15岁现象”,并明确指出这种现象并非完全因为青春期造成的,而是孩子在语言上的“转型期”发展滞留问题。15岁之前,孩子的语言状态处于自然表达,他们无所顾忌、思维活跃,想到什么说什么;15岁后,孩子开始懂得说话应有所顾忌,却掌握不了正确的表达方法,造成了在一些场合常常语塞的现象。专家指出,如不抓紧这个时机培养引导,将可能影响孩子未来的人际关系,甚至求职就业。
学生对语文课兴趣不高的另一个原因是教材问题。教材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教材内容陈旧,与生活脱节。当前的评议教材报选的内容仍然主要是散文、议论文、说明文、小说、文言文和诗歌。其中大部分散文和议论文、说明文内容较为枯燥,篇幅又比较长,学生对此缺乏兴趣,而学生比较感兴趣的小说则篇目很少且以老的经典篇目为主,缺乏当代流行的武侠、言情和玄幻等体裁,电影剧本也很少,小品等曲艺类完全没有。二是结构安排不尽合理,内容枯燥,实用性不强。在不少中学生中,流传这样一句话,学语文“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部分鲁迅杂文思想性虽强,但中学语文课文的主要功能应该是帮助中学生打牢字、词、句、章、语言、修辞、逻辑、作文八方面的基础,这些“投枪和匕首”显得有些过深,适合晋级而不适合打基础。加上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原本就饱含“微言大义”的鲁迅杂文,更容易被“卸用八块”成一堆堆七零八落的“知识点”,令疲惫不堪的学子们因目无全牛,而对这些课文产生畏惧和逆反心理。学生的另一怕是文言文难度较大(主要是语法考得太细),我认为文言文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但像英语一样,现实生活中却很少用到,花这么多时间学是否有必要呢?其实现在绝大多数经典文言文都已经被译成现代汉语,这些白话文版本在网络上随时可以查到。此外,当前中学语文教材对应用文体的写作重视不够,以致许多高中生连请假条、申请书等常用文体都不会写。
总之,教学改革是艰难的,为了探索这条改革之路,我们付出了太多的代价,但只改革教学方法是不够的,更要改革教育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