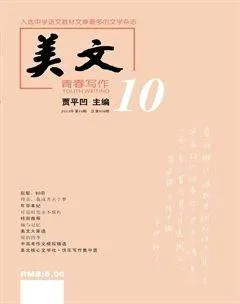走进童话丑小鸭

何杰,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中国语言学会会员。1996年至1998年赴拉脱维亚大学讲学、任教。同年于波罗的海语言中心讲学。1999年应邀赴德国汉诺威参加世界汉语教学研讨。2008年参加第九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2009年论文入选美国布莱恩大学语言学会议。2010年应哥伦比亚大学邀请赴美交流学术。
长期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及语言学研究。出版语言学专著《现代汉语量词研究(增编版)》等三部;出版教材、词典多部。发表及入选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论文三十余篇。
1972年开始发表小说。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论文和文学作品均有获奖。出版散文集《蓝眼睛黑眼睛——我和我的洋弟子们》。
入选《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中国语言学人名大辞典》《中国专家人名词典》等。
1998年获评天津市级优秀教师。2006年荣获全国十佳知识女性。
“一定得去柴西斯(Cesis)。我就不信不会拉语,就不能旅游!”
“校长”(我爱人)跟赌气一样,把吃喝一样接一样地塞进旅行包里。
我也说:“谁怕谁呀?走,去柴西斯!”
柴西斯城很小很小,历史上却是拉脱维亚最悠久的古城。在欧洲都很有名气。那里至今保留有中世纪的城堡、中世纪的露天歌舞场、中世纪的房舍……许多历史记忆。
可是话说回来,语言却也布满了沼泽荆棘。在城里都总走丢,这可是出城啊!柴西斯距首都里加90多公里,得坐火车。而我们拉语一点儿都不会,太难学。
哦,插一句,拉脱维亚国虽小,可语言复杂。使用的语言大部分是俄语和拉语,此外还有德语、波兰语、瑞典语、立陶宛语、乌克兰语……官方使用英语。语系又不同:俄语属斯拉夫语系,拉语属印欧语系。使用语言的心态也不同。说俄语吧,也不知谁是俄族人,谁是拉族人。跟俄族人说俄语,人家高兴;跟拉族人说俄语,人家反感。
那时我最强烈的感觉是,出国教师只懂一种外语,绝不能走出语言窘迫区
再说,俄语吧,倒还会的不少,可大多没用。“校长”就记得:
“己急切皆打死克(俄语音:到黑板前来)!”
“斯大林乌拉(万岁)!”
我还能背歌词:“瓦斯多克,咋瓦裂了(东方红,太阳升)。”
可是跟银行、车站这样的国家单位交流,当然得说拉语——人家的国语。
晕菜啦!
最后,猛翻了一阵汉俄词典,又翻俄拉词典(没有汉拉词典)。抄了一个小条,连写带画,再带上了证件。
豁出去了。出发!
天上掉下一个小毛茸茸球
第一关,自己买车票。
售票员从窗口把我递进去的小条推出来。
“怎么没有去柴西斯的票呢?”
我惊奇地回身瞧着校长,“校长”惊奇地瞧着我。我举起小条叫他看。“校长”没来得及看,他身后露出一个毛茸茸的头。毛茸茸的小帽边露着毛茸茸的一圈卷发。我们身后排队的一个小姑娘跳着脚“嘶——”很麻利地把条抻过去了。抻过小条,她看了看,便和小窗子里的人“巴里巴拉”一阵拉语,回身,笑开了。接着对我也一阵“巴里巴拉”拉语,我摇头。她又改为“叽里咕噜”一阵俄语,还不时得意地带上几句英语。
嚯,好不简单。我明白啦。我的小条画了两个并排的小人,抬着脚去cesis。
小条横着给她看的,我的画技又不高,售票员以为我要买卧铺票。
我和“校长”都笑了。毛茸茸球一样的小姑娘帮我们买了票,得意地递给我们。火车票是打印出来的纸条。一张票才1.86拉特。高兴!便宜!姑娘要过我的小条,在我那两个小人的对面,又画了两个小人朝回走,呀!是往返票。一趟票才相当人民币7块钱。便宜!小姑娘表示这还是涨了一倍。贵多啦!
拉脱维亚正在变革之中。我到拉,市内电车票0.14拉特(人民币2.24元),姑娘说以前0.07拉特。(现在是O.40拉特,合6.8元人民币)不管怎样,我们还是高兴。更高兴的是,小姑娘一直把我们送到去柴西斯的进站口。要知道,那可是一个大通道,有许多进站的拐口,不认识拉语。拐哪个口?
唉,不知道那些文盲怎么活着。刚想对小毛茸茸说声谢谢,小姑娘却转身往回跑。干什么去?
我只看见小毛茸茸球的两条小细腿,飞快地闪动着(她穿筒靴)。
“我忘买票啦——”
小毛茸茸球是个小天使
小姑娘跑了,留下一阵温暖。
我们看着小姑娘的背影。这时候,走过来一个胖大婶也跟着我们驻足巴望。拉脱维亚人可不像“我们那疙瘩”屁大的事都好奇,总是一脸冰霜,目不旁视。
胖大婶凑什么热闹?
不管怎样,第二关总算顺利。多亏了小姑娘。
进了站台,这里可不像国内的车站那么热闹,竟没几个人。没有检票口,没有检票员。社会主义的自觉,在这里充分显示。自己找车上就行了。整个站台冷冷清清,只有一列好像我国五六十年代的火车。
老旧的车厢。老旧的车门。还有我久违了的五六十年代的人心……
上了车,我俩猛嘀咕,对吗?这是去柴西斯吗?心正吊着,蹿上来了一个小姑娘,小毛茸茸球!真是好人自有天相。小毛茸茸“叽里咕噜”一阵俄英混用,像老朋友相见。毛茸茸一样的头晃了一晃,那意思:
别担心,我包了。老朋友!
小姑娘放下书包,坐在了我们对面。她叫我们放心,她也去cesis。悬浮的心终于也落了座。
天使是个小丑丫头
坐定。我开始细细打量小姑娘。小姑娘顶多十二三岁。穿着一件灰色短大衣,蹬一双半高的筒靴。和我在电影看到的苏联女孩装束一模一样。只是那大衣袖子有点短,有点尜尜的感觉。靴子也旧了。家里一定拮据。
小姑娘摘去她那毛茸茸的小帽。一个金发小刷刷辫子,“喯”弹起来,蹶蹶在脑后,像举起的小墩布。小脸一露出:呦——这个小丑丫头哇。圆脸庞上,鸭子一样的小撅嘴。没开口也像“呱呱”。
整个一个丑丫头。
小丫头一双蓝眼睛,可惜还有点斗眼。不过这个“小丑鸭”倒一点也不害羞。说话办事,“干巴利落脆”。此刻,她正在公开打量着我们俩。眼睛里跳动着一股狡黠的光点。
不知是我们俩有从教的职业特征,还是因为我们心里还对这个孩子盛着感谢。小丫精准又得意地猜:
“你们,中国人。温暖。爷爷说中国人好。”
我们点头。小丫神采飞扬接着猜:
“你们慈爱。你们是老师。”
不过小丫说,她不愿当老师。她现在有好多顶要紧,顶要紧的理想。譬如:她要当品尝师。吃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唉,他们不富裕)。小丫还想当送生婆。我光听说过“接生婆”,没听说过“送生婆”。
“哼,我那个送生婆可不怎么样。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把我送给了一个瑞典妈妈。”
我知道,历史上,瑞典也占领过拉脱维亚。我去瑞典时,同船就有瑞典籍的拉族人,拉籍的瑞典人(这个乱乎)。拉脱维亚不仅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欧洲人也不少。你根本分不出来。拉的历史、国情、人情都很复杂。
小丫的鸭鸭嘴,一会儿就把她不想告诉任何人的秘密,都“呱呱”给我们了。
丑小丫也住在冰河
苏联解体前,小丫的妈妈在一家俄罗斯人的企业工作。苏联解体,俄撤走了,妈妈没了工作,回瑞典了。小丫爸爸在爱沙尼亚的一个锯木场。爸爸不去瑞典。他们“切奶酪”了(大概是分手了)。
多好的比喻词。奶酪比喻婚姻:经过多长时间的混合,发酵,酿造。有酸,有甜。最后凝聚成香甜,意味无际的一体。
你们不知道那小姑娘说话用词有多么生动!神情有多么可爱。
“哼,瑞典有钱。我爸爸没钱。”
“谢尔盖,那个干棒槌。说我是斗鸡眼,我妈不要我了。呸——”
小丫冲着窗外,狠狠地“呸”了一声:
“干棒槌,你妈才不要你呢。”
“爷爷说,我就在拉脱维亚。我是拉脱维亚的丫丫。”
小丫晃着脑袋向上拔着身子。说完。小姑娘忽然像瘪了气一样,一脸痛苦:
“我想妈妈。妈说,以后等我长大点,不怕疼了,给我治眼睛。”
真心痛这个孩子。我们忙拿出苹果给她吃。可她说什么也不要。她说,她最爱说话了。老师都总叫她闭嘴。看来小姑娘憋了一肚子气。
“干棒槌叫我‘斗鸡眼’。哼,奶牛屁股蹭了他的嘴。奶奶说,叫牛牤叮他。我才不理他呢。
“干棒槌,烧火棍,什么都不会。考试就看人家的。我都是5分(5分为满分)。
“干棒槌他们还叫我‘牛屁股插管子——爱吹牛’、‘话罐子’,说我是从鸭妈妈那捡来的,一天‘呱呱’没完。
“就我爷爷奶奶说,我是他们的宝贝。”
我们立即确定:
“小姑娘,你真的是宝贝。不单是你爷爷奶奶宝贝,也是拉脱维亚的宝贝。”
小姑娘像打足气的气球一样,浑身来了力气。小鸭鸭嘴“呱呱”地更有劲了。
我们很快就知道了,女孩是里加一所技术学校的学生。13岁。专业手工编织。拉脱维亚有许多这类的技术学校。陶艺、木雕、琥珀制品、编织。他们有非常漂亮的手工艺术品。小姑娘脱下大衣叫我们看她的毛衣。她说,那是她的作业。真的,那图案很有民族特色。色彩鲜明,很像我们云南的编织。小家伙太棒了。才十几岁,就能织出那么漂亮的毛衣。可有机会给小丫一点鼓励了。我们连声称赞她,给她鼓掌。
小丫却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垂下长长的睫毛,连比带画地说。说的可是我从没听说的。
冬天是寒冷的
苏联解体了。他们学校的产品原来可以卖到俄罗斯,现在人家不要了,而且动不动就制裁他们。这次就是停了卡斯(天然气)——拉脱维亚的天然气都是由俄罗斯供给。现在分家了,人家想停就停。我在拉大也赶上过,睡觉连椅子都扣过来当压脚被。你在国内有过这样的感觉吗?冻得连胃里的吃喝都觉得变成了冰块。
“学校冷得上不了课,放假一周。这样的事好几次了。”
小丫说,大家一听说放假,特别高兴。可第一天高兴,第二天高兴,第三天就想回学校了。
我正说着,小姑娘的话像断了闸,眼睛也一下盯着眼前的什么,骤然不转了。我忙回头,看见来个卖面包的。
我在邻居的孩子们那里见过这种眼神。如果你不到那里,你一定不相信。国内的孩子们,巧克力都不屑于理。而在这儿,我真的看见了,那绝对是食品不足造成的效应。
我说,小姑娘一定没吃早饭。她有气无力地点点头:
“我的钱只能买一样:要不面包,要不车票(学生半票)。”
我心里忽然一下热起来。觉得眼前这个小丑丫头真的怎么这么漂亮!因为我知道,有的人并不买票——没人检票。那真的都是靠社会主义的自觉。他们只是偶尔有查票的。小姑娘忽然害羞起来,她低下头小声说:
“如果我回家,我知道有烤胡萝卜,烤土豆等我。我一定买票。
去学校,没有面包时……”
小姑娘用她的靴子尖涂着脚下的车板,不好意思再往下说了。
可爱!
“校长”捅我,我立即明白了。赶紧掏出包里的糖馒头,托在手上,慢慢伸到她的眼前。小姑娘伸着头,盯着那白馒头,在胸前画着十字,嘴里“咕哝”着什么。后来我才弄清:
“善心,一定有面包相报!”那大概是他们的俗语。
我赶紧又掏出我们的自制腌蛋。来时,还犹豫半天,多亏最后带上了。那可是我去乡下过夏至节,被评出的最佳中国奶酪。拉脱维亚没有腌蛋。
孩子大口地吃着。那天,我们俩看着,都觉得特别的香甜。我们告诉她,中国人也有句俗语:“好人好报。”
丑小丫真的是只小天鹅
“好人好报”,可有时也有危险。不信,往下看。
说着,高兴着,忽然来了个卖报纸的胖大婶。她“叽里咕噜”地嚷嚷着什么,上前就要去抓小姑娘。小姑娘直躲。
丑丫头怎么招惹人家了?
胖大婶掏出一双毛手套,举着。“叽里咕噜”地更厉害了。小姑娘丢了手套了吧?
小姑娘推脱地说:“不用了,不要了。”
我们莫名其妙。
胖大婶还没完没了。
小姑娘又说:“是我的。是我的。”
我也忙向那个大婶证明。小姑娘是个好孩子。还把孩子帮我们买票的事告诉了她。
胖大婶又摇头,又点头,继续“叽里咕噜”。反正,折腾了半天,糊涂半天。最后弄明白了。
一次大雪天,哈口气就能冻个冰雕。一张嘴,舌头都冻得不转了。胖大婶卖报,举着报纸晃,却没戴手套。手指豆儿,真的会冻掉的!
一个带毛茸茸球帽子的孩子给大婶塞下了一双手套。胖大婶,脸都没看清,孩子就消失了。
今天可找到了!
孩子不好意思地推托着。胖大婶一边“欧琴欧琴,普利牙疼哪(非常高兴)”叫着。只见她一只胳膊夹着报纸,一只手搬着孩子的头,狠狠在孩子脑门儿上亲了一口。又使劲地一把把那小豆芽一样的孩子,搂进她那胖胸脯里。
天啊!我站起身来,“校长”也站起来。胖大婶挺着的可是有两个棉花包一样的胖胸脯!
说实在的,真怕胖大婶把这个小芽芽给憋死。那可是只小天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