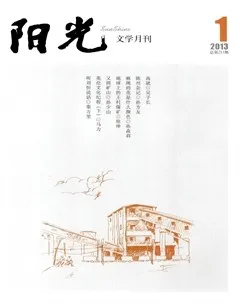陈州杂记
商 幌
商幌,又称望子,一种在商店门外表明所卖货物之招牌或标志物,俗称“招牌”,其来源甚早,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中说:“宋人有沽酒者……为酒甚美,悬帜甚高。”可见当时的商人已经开始运用广告宣传所卖的货物了。商店悬望子,是古老的商业风格,最初特指酒店的布招,即酒旗,别称很多,又叫酒招、帜、酒幌、酒望、布帘、酒子等。以布缀于竿头,悬于店铺门首。有些大商号为显示其资金雄厚,特用金箔贴字的招牌或黄绸招牌,称之为“金字招牌”。招牌是商家致富的命根子,看得和生命一样珍贵,因此有“招牌是命”之说。“招牌砸了”这是商界最严重的事,商店倒闭了,信誉没了,致富也就无望了。
商家需要商幌,制商幌的行业也就应运而生。陈州最早给人制招牌的是“永昌斋”,店主姓倪,叫倪飞,年轻时在上海求学,专攻工艺美术,回到陈州,就开了“永昌斋”,后改为“世缘斋”,专给人制招牌。
永昌斋制招牌大致分三类,一是文字幌(在长方或正方形木板上书写、镌刻文字,有的涂金或贴金以示壮观);二是形象幌(用所售商品模型);三是象征幌(采用商店的象征物)。永昌斋除去给人制招牌外,还可帮新商号起店名。如当年陈州的茂恒、汇昌、永盛兴、志合兴、步步高、谁不居等,大多出自永昌斋。
倪飞因当年在上海求学,见多识广,而且脑瓜儿活,办事很具创意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会策划。民国初年陈州建起第一个电影院,放映《火烧红莲寺》,当时电影还是无声影片,影院钱经理请倪飞做广告,倪飞拟的广告词为“观看的人太多太多,最好您别来”,然后画出巨幅广告画,放在繁华处。据说连放一个月,场场爆满,连乡下人都赶车前来观看,使得陈州城热闹空前。
陈州影院的钱经理是位女士,叫钱莹,上海人,因为倪飞在上海求过学,会说上海话,二人很有共同语言。所以钱莹才让倪飞为她搞策划。由于策划成功,又加上陈州是第一次放电影,钱莹赚了不少钱。赚了大钱的钱莹就很感激倪飞,常请他看电影下馆子。当然,有关影片宣传这一块儿,也全包给了“永昌斋”。
由于接触频繁,一来二去,二人就产生了感情。
只可惜,俩人都是结过婚的人。只是钱莹的丈夫远在上海,管不着,而倪飞的妻子就在眼前,俩人的频繁接触自然会引起她的警觉。加上钱莹长得漂亮,又是南方人,在陈州城很招眼,不少纨绔子弟都想打她的主意。由于自己没捞着,让倪飞小子捡了便宜,就十分忌妒,专门派人跟踪倪飞和钱莹,然后再向倪飞的妻子递信息。倪飞的妻子根据信息去捉奸,一捉一个准。抓住了就要大闹一场,不久就闹得满城风雨。
倪飞的妻子姓穆,叫穆菁。其父穆少奎是祥和店的老板,也算陈州城的“大亨”,有钱有势,担任着陈州商务会的副会长。如此有头脸的人物,门婿做出此种伤风败俗之事,自然很丢面子。穆少奎为了帮女儿,派人去上海叫来钱莹的丈夫朱阿福。不想朱阿福是个无能的男人,听说夫人与人私通,非但不恼,反而很高兴。他来到陈州见到钱莹,张口就向钱莹要钱,并以此敲诈。夫妻二人在价钱上争来争去,最后钱莹以五万元就搞定了朱阿福,买了个自由身。朱阿福得到五万元之后,高高兴兴地回了上海,临走时还专到穆府一趟,表示感谢穆老先生传递给他发财信息。穆少奎望着这个不知廉耻的无赖,差点儿气晕过去。
万般无奈,穆少奎只好劝女儿向倪飞提出离婚。
穆菁虽然恼恨丈夫有外遇,却从来未想过离婚。不离婚的原因是因为她太爱倪飞,并且已有了孩子。当年倪飞追穆菁时,倪、穆两家的门户根本就不相对。穆家的祥和绸庄店是陈州数得着的大商号,而倪飞的父亲只是开个刻字店。后来是穆菁非倪飞不嫁,穆少奎才答应这门亲事。令穆菁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倪飞会半路爱情转移。这真真使她伤心透顶。但尽管伤心到如此地步,她仍是不大愿离婚。她认为倪飞只是一时糊涂,通过自己的努力他一定会回心转意的。可是,尽管她到处跟踪捉奸,倪飞和钱莹仍是约会不断。又由于她情报准确,越闹越厉害,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倪飞越来越恨她了。
终于,倪飞向她提出了离婚。
穆菁一下傻了!
穆菁哭了一天一夜,从此不吃不喝,以绝食抗议倪飞的离婚要求。她认为当初自己能下嫁倪家,已是对倪飞的高抬。这一生,唯有她向倪飞提出离异才是正常的!而现在,竟是倪飞首先提出,很让她面子上过不去。她原想用绝食吓唬倪飞,唤起他的良知。不料那倪飞像是铁了心,置她的死活于不顾,竟与钱莹公开同居了。这一下,不但穆菁没了辙,连穆老先生也束手无策了。
最后,穆少奎决定撵走钱莹。
可是,想赶走钱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钱莹有着南方人特有的聪明,不但会经营,还会摆平各种关系。她来陈州不久,已将地方长官和驻军头目全部买通,就连穆少奎这个商务副会长,当初也接受过人家的礼物。后来赚了钱,她更注意打通各种关节,很快挤进了陈州上流社会。再加上电影是个新事物,很受人们的欢迎。钱莹像是看中这步棋,听说是准备买地皮建个人影院。如果她真的如此,怕是想动她更非易事。
为了女儿,穆少奎想到了暗杀。
这当然是无奈之举,但为了女儿的后半生,穆少奎不得不走这步险棋了。
令穆少奎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正当他要寻人暗杀钱莹时,钱莹却在当天夜里被人杀害,尸首抛进了城外湖里,是被一个打鱼人发现的。
顿时,陈州城一片哗然。
穆少奎更是大吃一惊,原以为是女儿找人干的,可一问穆菁,穆菁摇头不止,而且听到钱莹的死讯后,先是惊愕,然后三呼万岁,披头散发地奔跑出去,高喊着要去寻找倪飞。
殊不知,倪飞那时候已走进了陈州法院,控告穆少奎暗杀钱莹的罪行。陈州的大街小巷里,舆论四起,没有人不相信是穆少奎害死了钱莹。
此案涉及几多要害人物,陈州法院自然极其慎重,动用了几多侦探,结果却令人大吃一惊,凶手竟是远在上海的朱阿福。原来这朱阿福是个破落子弟,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钱莹初嫁时,朱家还可以,后来家道中落,钱莹便凑钱来陈州发展。倪飞与钱莹的桃色新闻公开之后,朱阿福觉得有机可乘,上次来陈州诈得五万元之后,很快挥霍一空。后听说钱莹要在陈州筹建电影院,便起了歹心,决定利用穆家这一错觉,先杀死钱莹,然后再继承钱莹的遗产。不料陈州侦探也不是吃素的,没出十天就将其揪了出来。
事情本该结束,岂料那倪飞觉得破镜难圆,坚持与穆菁离了婚。由于没有了钱莹,穆菁的情绪缓冲不少,便答应了倪飞的离婚请求。
令人遗憾的是,二人离异后都未再婚,穆菁带儿子回了娘家,倪飞将“永昌斋”更名“世缘斋”,又开始重操旧业。陈州人都说“世缘斋”是倪飞为纪念钱莹而起,倪飞也不否认。
倪飞和穆菁都长寿。他们的儿子长大以后,可以互递信息,来回走动,但至死二人未能复婚,成为陈州一奇。
脚 行
脚行,顾名思义,是靠力气吃饭受雇于人的行当。周口出现“脚行”这个行当,可以追溯到清朝前期,由于当时没有火车、汽车,运输主要靠船只和人推马拉的木轮车。周口地处豫东平原,河道纵横,陆路四通八达,水陆交通都极为便利,因此贸易兴旺发达。由于大批出口进口的物资都需要搬运,所以“脚行”就应运而生了。
清末民初年间,仅周口这一个地方单以搬运粮食为主的脚行班就有七八个,工人近千名。这些脚行班大都聚集在粮行、粮坊集中的街道,并都和大陆陈行店挂了钩,各班都有自己的店主,每天按照店主的要求去完成本班的搬运任务,互不干扰,互不侵犯。那时候周口有大型行店二十多家,粮坊一百多个,坊子里的粮食一经行店收购,全由脚行班用木轮车集中到栈房,单等上船外运。当时搬运的最笨重的货物,除了粮食之外还有食盐。一般体力弱的工人,是不敢当卸盐工的。那时候盐由“官商”经营,所以也叫“官盐”。“官盐”全由水路运来,每来一次盐船都有二三十只,领头的船上插着黄旗,敲着铜锣,不停地吆喝:“盐船来了,两边让道!”如此高喊的目的,一是叫密集的船只让开水道,二是通知脚行班做好卸盐准备。西新集有一个班子,专管卸盐,听到盐船来了,便奔走相告,立即集中到“三道沟”西边的一个码头上,严阵以待。当时装盐用的不是麻袋,而是用芦苇席打的盐包,每包重五六百斤,需四个人抬一包,从船舱抬到岸上的堤根边。堤上有五六个人用一个“滑子”把盐包往上拉,拉到堤上后,再由四人抬起到盐场上垛。这个专门卸盐的码头,既窄又陡,砖石砌的护岸像城墙一样陡峭,此码头被人称为“盐路口”。
西新集的脚行班班头儿姓吴,叫吴大,六尺高的个头儿,体重有二百斤左右。在脚行班当头儿,与其他不一样,要论力气。吴大一人扛过一个盐包,众人皆服,便推举他当了班头儿。脚行这个行当,当了头儿并不比别人少干,相反还要处处带头,只是每次分账时,给他多提一块或两块。吴大力大,饭量也大,一顿能吃七八个馒头。他最拿手的技术是垛盐垛。无论多高的盐垛,他都能垛得整整齐齐,所以每次卸盐,都是他在垛上,严把外线。所谓外线也就是最边的那一排。这不但要眼力,也需力气,可里或可外一点儿,他一个就能挪得动。盐包“死沉”,如一块巨石,砸在身上不要命也要断骨头,所以码头人皆称盐包为“盐老虎”。“盐路口”码头上,几乎每年都要伤人。
脚行班班头儿除去每天多领一两块钱外,还有个特权,那就是可落些扫舱盐。所谓扫舱盐,就是卸过盐之后船舱里打扫出来的盐。这盐当然很脏,需要先化成盐水,再重晒。
吴大是个光棍汉,母亲双目失明,没那工夫。他每次得了扫舱盐,就攒在一起,然后卖给酱菜店。
这一天,吴大正在吃饭,突然有一个年轻人来找他,说是要吃扛脚饭。吴大抬头一看,来人二十五六岁,长得眉清目秀,身材瘦弱。吴大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笑道:“你长得像个书生,怎能受得了这苦?”那人施礼道:“吴班头儿,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在下吃得吃不得卸盐之苦,试一试不就得了?”一句话,倒说动了吴大。他又望了那人一眼:“请问贵姓?”那人说:“免贵。鄙人姓阮,叫阮一达。”吴大不再多问,说:“那好,你既然想吃这份儿苦,那就上码头吧!”
第二天,赶巧有盐船来,阮一达随吴大上了码头。卸盐数下船最苦。吴大为试阮一达,特派他抬包下船。盐包重五六百斤,四个人抬四个角,然后再沿两块跳板横着抬到岸上,每个人不但需要分担一百多斤的重量,还得有在窄窄的跳板上挪步的技术。四个人要佝头看跳板,口喊着“一二、一二”朝下抬。由于是从高处向低处走,抬外杠的两个人要高个儿,抬里杠的要矮个儿,这样有所平衡,不易损着哪位。阮一达个儿高,自然是抬外杠。不想这精瘦的阮一达倒像个行家里手,下跳板迈脚步,很是和谐,一连卸了五日盐,并不见叫苦,只是皮肤晒黑了些。吴大就觉得这阮一达不是一般人,更觉得让其干这种苦力有点儿屈材料。等卸完船之后,吴大特领阮一达进了一家小酒店,要了两个小菜一壶热酒,边喝边细问起阮一达的身份来。阮一达开初只喝酒不搭言,吴大问急了,才笑着说:“吴班头儿,实不相瞒,我是芜湖人,家父就是大盐商,只不过他也是装盐工出身,为让我掌好家业,特让我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干脚行,等干够一年,再回芜湖。”吴大一听阮一达是大盐商的儿子,惊诧得张大了嘴巴,怔怔地问:“你说的当真?”阮一达笑了,说:“我骗你有何用?若不是你问,我是永远不给你说这些的。”吴大这才信了,说:“你说你父亲也是扛脚出身,最后怎么成了大盐商?”阮一达沉吟片刻,说:“吴大哥,说来怕你不信,我爹发迹前和你一样,也是脚行的头儿,不过,他要比你精明得多。你们这里卸盐,我们那里是装盐——就是将盐包装进船舱里,难度要比卸盐大得多。没装船之前,他先与船主讲包价,讲妥了,先暗扣一些,然后再召集人装舱。几年下来,便有了些积累,开了个小盐行,慢慢就闹大了。”吴大听得瞪圆了眼睛,不解地问:“克扣劳力的工钱,那怎忍心?”阮一达笑了,说:“这就看你的本事了,家父说干大事者必须从细微处着手,任何事情都有机可乘。家父对工人非常关心,也就是说,会收买人心。他所扣的那部分并不是工人应得的,而是从船主那里多要的,只不过是借了工人们的力量而已。”吴大越听越迷惑,怔然地问:“怎么是借了工人的力量?”阮一达笑道:“你想,任何船主都是不愿多掏钱的。由于家父威信高,先率领工人们罢卸,船主们耽搁不起,就暗地向父亲许诺,这不就是借了众人之力吗?”吴大这才恍然大悟地“啊”了一声,双目直直盯着一处,好一时才说:“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阮老弟,亏你指点,才使我茅塞顿开,这样吧,趁你在此,帮我一把,咱也来个罢卸,让船主涨价钱。”
第二天,吴大率领西新集的卸盐工开始了罢卸。可令吴大料想不到的是,他们罢卸不到半天工夫,船主却找来了另一帮卸盐工,价格比他们的还便宜。吴大惊诧万分,急忙找阮一达想办法,岂料那阮一达早已没了踪影。这一下,吴大傻了眼,他做梦也没想到会是这种结局,急忙又去找船主央求复工,船主借机压价,吴大深怕众人丢了饭碗,只好打掉牙往肚里咽,认了。
盐工们无不抱怨,第二天就罢了吴大的职。吴大很苦恼,正欲寻阮一达问个明白,不料阮一达却派人偷偷给他送来了五十块大洋和一封信。原来这阮一达果真是少老板,他不但是盐商,还是个总船主。为减少装卸费,他用此办法深入沿途码头,一下使装卸费减少两成,光这一项开支,他每年就能省上百万大洋。
鳖 厨
旧世道儿,陈州这地方称妓院为“鳖窝”,称妓女为“鳖”,给“鳖”做饭的女人称“鳖厨”。当时这种活儿于世人眼中是极下贱的,虽然月薪高,但极少有人去干。
陈州南有条颍河,颍河上游有个周家口,下游有个界首。界首有个花子街,周家口有个万贯街。花子街和万贯街上都是妓院,相当于现在的“红灯区”。尤其是周口万贯街,很有名气。内里不但有南方的苏杭美妓,也有“燕瘦赵肥”的北方妓女。万贯街上最有名的是万贯楼,任你腰缠万贯,只要去过万贯楼,慢慢会让你自己把钱掏干。
姚二嫂就在万贯楼内当“鳖厨”。
姚二嫂家很穷,为了生计只好不顾名声来万贯楼为人当厨。姚二嫂的丈夫叫姚二,很老实。姚二嫂去妓院当厨,姚二就在家照看两个孩子。每到月底,姚二就领着两个孩子去周口,姚二嫂悄悄从后门溜出来,将薪水交给姚二,亲亲两个孩子,然后挥泪而别。
这一年,豫西土匪路老九打下周口,抢占了万贯楼。土匪们把妓女一个个用苇席围起来,标上价码,任人挑选。交款之后,再让你看人,丑俊皆不得退还,一切认命。姚二嫂也是女的,也被土匪当妓女抓了起来,尽管姚二嫂一再解释,土匪们还是把她用席筒子圈了起来,标上价码,卖了。
买走姚二嫂的人姓焦,叫焦大。焦大是个纤夫,给一个姓钱的老板拉商船。这次从漯河往蚌埠运京广杂货,路过周口,听说妓院卖女人,便取出多年积蓄买了一个。焦大雇了小土牛车推着姚二嫂朝码头上走,姚二嫂一路哭哭啼啼,向焦大诉说自己的不幸。焦大一开始不信,最后见姚二嫂哭得伤心,便问:“你说你是厨娘,让我如何信你?”姚二嫂说:“接客的女人整天擦油抹粉,浑身透着香气,我一天到晚在灶房里,从未打扮过,你一看不就看出来了!”焦大想想也是,就贴近姚二嫂闻了闻,果真没一丝香气,这才信了,说:“事到如今,我也不强迫你,你既然有丈夫有孩子,那你就赶快给我五十块大洋,别误了我再去买一个。”姚二嫂哭着说:“这位大哥,我一个月才挣两块大洋,还要养家糊口,你让我去哪儿弄五十块大洋呀?”焦大说:“那这事儿就麻烦了,我为能买一个女人几乎用尽了前半生的积蓄买了你,你不从我不强求,但你也不能让我拿钱买个空呀!这样吧,你先随我到船上,我托人给你丈夫送个信,让他找钱把你赎回去如何?”姚二嫂听焦大把话说到这一步,想想再没别的办法,只好随焦大上了码头。
到了商船上,船上人都为焦大买个漂亮娘子而高兴。焦大自然高兴不起来,哭丧着脸向众人说了实情。焦大这边说着,姚二嫂那边哭着,哭声惊动了钱老板,钱老板就从上舱走下来,问焦大说这女人哭哭啼啼怎么回事儿,焦大又向钱老板诉说了姚二嫂的不幸。钱老板走过去,望了望姚二嫂,叹了一声,对焦大说:“这样吧,我先给你五十块大洋,先把这女人救下来,你再赶快回妓院买一个如何?”焦大一听,急忙给钱老板磕头,然后就接过五十块大洋急急上岸去了万贯楼。
焦大到了万贯楼,见妓女已剩不多,急忙交钱又买了一个,打开一看,却是个老妓,比自己还大了几岁。焦大心想这大概就是命,姚二嫂年轻漂亮,却是有丈夫的女子,这个倒心甘情愿跟自己从良,却是个老女人。焦大正在叹息命苦,突见姚二带着两孩子来找姚二嫂。姚二见人就问,一脸着急。焦大一听是找姚二嫂的,便急急走过去向姚二说了实情。姚二如遇恩人,拉过两个孩子就给焦大磕头。焦大说:“我先领你们父子去船上见见你家娘子,然后再想钱的办法如何?”焦大说完,就带着老妓女和姚二父子三人去了码头。不料到河边一看,河里已没有了商船的影子。
姚二和两个孩子号啕痛哭。
焦大一见商船没有了踪影,心中已猜出是钱老板从中使了坏心,便宽慰姚二说:“钱家商船是个楼子船,这条河道里没几家楼子船,他们经常从下游朝上游运山货,你只要在这儿坐等,不久便可等到的!”说完,焦大便带着那老妓女回老家重谋生路去了。
果然不出焦大所料,那钱老板见姚二嫂有几分姿色,而且长年当厨娘,身上养得丰满瓷白,又不是青楼出身,就动了歹心。当那焦大一上岸,他就命令开船。因是下水又顺风,帆篷一拉开,船便如箭般离开了周口。姚二嫂自然不从,几次要投颍河寻死,都被拦住了。最后经不住钱老板百般规劝,只好哭哭啼啼进了洞房。到了蚌埠,钱老板谎说已派人给姚二送去了钱财,然后将姚二嫂领回家中,并给她另买了一处宅院,又配了丫环和老仆,让姚二嫂一下就过上了富太太的生活。
几年以后,钱老板带姚二嫂去漯河玩耍,一天路过周口,船靠岸装货,姚二嫂回到久别的家乡,心中自然有着另一番滋味儿。她让丫环陪同,专去万贯街故地重游了一番。她深怕熟人认出自己,还戴了副墨镜。那一天,她玩得很尽兴,直到半下午才回到码头。不想就要上楼子船的当儿,突见一老乞领着两个小乞站在了她面前。姚二嫂一愣,下意识地捂了鼻子并朝后仰了一下身。这时候,那个老乞和两个小乞已向她伸出了脏兮兮的手,可怜巴巴地叫道:“太太,给我们一点儿吧!”姚二嫂听到那老乞声音耳熟,仔细一看竟是姚二带着两个孩子沿街乞讨,顿时如傻了一般,不知如何是好了。丫环见她打怔,忙问她怎么啦,她只觉双目发热,急忙掩饰地遮了脸,一副嫌脏的样子,细声对丫环说:“多给他们些银钱,打发他们到别处去讨要吧!”
奇 诊
伍先生是个专治疮的先生,祖传,能治各种疮,尤其是对妇女生孩子后长的那种奶疮,更为得手。很早的时候,伍家就会用手术治疗,只是当时全是土办法,连消毒的酒精也没有,将手术刀在火上烧,加热杀菌,也挺管用。伍家自配的一种药粉也很奇效,敷上后极少发炎。只是伍家的医术传男不传女,除去手术技术外,最保密的就是这种药粉的配制秘方。
伍先生是众人对伍家人的尊称,从清末到解放初期,伍家已出了好几代“伍先生”。我认识这位伍先生叫伍单。所谓“单”,为单传之意。伍单的父亲就是那个老伍先生叫伍传。据说伍家过去还可以,只是有一年给一个小孩子割疮动了筋管伤了性命,患者家属将伍家告到官府,被罚破了产,日子越来越穷了。由于穷,伍传娶的女人非常丑陋,而且有狐臭。伍传极不喜欢她,婚后就一直不与她同房。到了四十岁那一年,伍传的母亲也就是伍单的奶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儿子不与媳妇同房,这传宗接代就成了问题,所以就请了不少人去劝伍传,说是粪堆里也能生出灵芝草,女人丑并不代表她不会生儿育女。袁世凯的母亲是有名的大脚丫环,不也生出个总统来!如果不生儿育女,伍家就没了后人,祖传手艺就没人继承了。伍传脾气很犟,认死不答应。那个丑陋的女人对婆母说,这种事儿是劝不醒的,别强求他了。我们夫妻之间的事还是由我们自己来解决吧!当天夜里,她就跪在了伍传的床前。伍传看到她很气愤,一脚将她踹了几尺远。可那丑女人很顽强,又站起来跪了下去,并对丈夫说:“我愿意让你休我,怎奈伍家已不同过去。过去你们家积攒的还有些钱财,休了我你还可以再娶。可现在你休了我,怕是再难找到女人了。我虽丑陋,但我毕竟也是个女人,是女人就应该有做母亲的权利。换句话说,我想丑吗?我何曾不想长得漂漂亮亮?这是命运!我恨不得一死了之!到阴曹地府跟阎王打一架,换上一副好面容,到来世再侍候你……”女人说着哭着,伍传终于动了恻隐之心,才与女人同房,才有了这个伍单。
伍单三十岁那年,其父伍传离世,伍单正式出诊行医。伍家住在镇西街口,三间房,门楣上方吊着幌子,是一串菱形木板上画的膏药标志。诊所占一间房,内里有一张木床,药橱里全是瓶瓶罐罐。伍先生身穿长衫,很规整地坐在一个木凳上与人就诊。长疮患者虽然不是太多,怎奈伍家名声大,每天总有那么一两个患者登门就医。有时候伍先生也出诊,身背一个破药箱,样子很急地从大街上穿过。街风舞动着他的长衫,将他那瘦弱的身材裹得似一根活动的电线杆儿。
这一天,伍先生正在坐诊,突然外面来了一辆马车,说是请先生出诊。伍先生问车夫:“贵府距此多远?”车夫说:“有二十余里路。”伍先生一听路途不是太远,略做些准备,拎着药箱便上了马车。
马车为轿车,上面有车篷,车篷里有靠背,靠背上铺着坐垫,一看便知是大户人家的装备。伍先生一上车,车夫就将门帘放了,然后一路狂奔,直走了几多个时辰,仍不见停。这下伍先生禁不住有点儿心存疑窦,问车夫说:“师傅,二十里路如何走了这么多时辰?”那车夫说:“这条路直走二十多里,只因直路泥泞太多,我怕脏了车子,所以才绕了些路程。先生甭急,一会儿就到了!”伍单一听是绕了道,这才释然,心情一放松,睡意袭来,不一会儿便昏昏欲睡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那车才停下。车夫掀开车门帘,对伍单说:“先生,到了!”伍单被唤醒,伸头朝外一望,天已大黑。四下再看,全是漆黑一片。他顿然有些害怕,问车夫道:“师傅,这是什么地方?”那车夫笑着说:“这就是你所说的贵府,快下来,我家主人有请!”
伍先生下了轿车,抬头一望,面前黑黑的一大片,慢慢隐约出一处宅院。伍单心想,如此富豪之家,为何连个门灯都不点?正愣神,车夫已叫开了大门,唤他上台阶。伍单摸索着上了台阶,进了院子,又随车夫走了好长一段黑路,才走到像是后庭院的一个地方。
直到这时候,伍先生才突然看到高处亮了一下,然后又急促地暗了。趁顿然一亮的刹那,他看出面前是一座阁楼,估计有两层高。有声音传来,少顷,便从阁楼上下来一位女子,与那车夫小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就领伍单上阁楼。二层楼是三间房,像是绣楼,出厦走廊,全是木制。主房为三间,两间为厅,一间为卧房,很大方。那女子领伍单进了厅,厅内也无灯,只从卧房门帘里透些光亮。伍单这才看清接他的女子是一身下人装束,猜想她定是丫环无疑了。那丫环让他坐下,然后才对着卧房里说了一句:“太太,先生来了!”她话音落了一会儿,才听有人在里边说:“让先生进来吧!”那丫环听到命令,就对伍单说:“先生,请!”
伍单拎药箱掀门帘进卧房,烛光闪烁,只见床帷紧闭,有一老太婆坐在床沿处,向他微微颔首,然后命令丫环说:“再点一支烛!”
丫环奉命又点了一支烛,室内顿时明亮了不少。伍单这才看清老太婆并不很老,大约不过花甲,穿金戴银,一脸富贵。再看床帷里,隐约能看到床上躺一人,从长发上可猜出是一女子,只是用布包严了脸,看不清模样。老太太撩开床帷,又轻轻掀开大红缎被一角,露出一个很肿胀的女乳。伍单一看便知此乳是生了奶疮,而且已熟,必得动手术清脏物消炎。伍单望了那老太太一眼,老太太示意他近前。伍单从药箱里取出一只很薄的手套,戴上,然后才捏了捏乳房肿处,对老太太说:“已熟透,必得手术!”一听要动手术,床上女人动了一下,痛苦状隔着蒙布溢出来。老太太望了望床上人,又望了望伍单,问:“不动刀子行吗?”伍单摇了摇头说:“乳上筋多,离心又近,不动刀会一直烂下去,危险!”老太太听得此说,眉毛拧了几拧,无奈地叹了一声,叮咛伍单说:“你可要小心!”伍单说:“那是自然!”言毕,便急急打开药箱,取出刀剪,让丫环又点了一支烛,开始用火消毒。紧接着,又让丫环去楼下取些白酒和棉团,然后将所需药物、术具全摆在桌子上,命丫环打下手,非常小心地给床上的女人动开了手术。
床上的女子很坚强,不喊不叫,头上汗珠儿浸透了脸上的蒙布,湿了一片。老太太不忍看又担心,一会儿捂着眼一会儿放开,大约忙了一个时辰,手术完毕,很成功。伍单在刀口处给那女子下了捻子,安排老太太说:“太太,七天以后,我再来给病人取捻子换药。千万记着,这些天千万不要让她吃发物。”说完,将刀剪药瓶儿装入箱内,又对老太太说:“太太,马上就要天亮了,我要告辞了!”那老太太看了看伍单,恳求说:“伍先生,我们既然请您来了,最好在这里住几天,等给病人换了药再送你回去怎么样?你放心,老妇不会亏待你的!”言毕,也不管伍单答应不答应,就支使那丫环说:“你快领先生去备下的房屋,让先生休息!”
伍单一看难以推辞,只好随那丫环下了阁楼。那丫环领他转了好几个弯儿,才走进一幢大房子里。大房子角处有一个小门儿,丫环打开了,又走了一条很长的窄走廊,才走进了又一个屋子。内里有床有桌有灯,被褥齐备,干净又整洁。伍单正发怔,只听那丫环说:“先生,你休息吧!”丫环说完就出门关门,脚步声渐遁后,一片死寂。
这时候伍单已很累,心想既来之则安之,便放下药箱,朝床上一躺,“呼呼”睡了过去。一觉醒来后,天已大亮。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住的是一间暗室,唯有一处见光,很高,是一个碗口大的孔,像个月亮。光柱很强地射下来,室内就亮了不少。这时候,只听门响,见那丫环用竹饭盒拎来饭菜,打开了,对伍单说:“先生,吃饭吧!”
伍单问:“姑娘,这是什么地方?为啥让我住在这暗室里?”那丫环望了伍单一眼,小声说:“先生,别太声张。你住在这里有吃有喝,只几天时间,熬一熬就过去了。到时候,我家主人又不亏待你,何乐而不为呢?”伍单说:“我若几天不回,家人会挂念的!”那丫环劝道:“不就几天嘛!等他们找不到你急得不行的时候,你突然回了,才会给他们更大的惊喜呢!”
就这样,伍单在暗室里一连住了几天,到了第七天夜里,那个丫环才领他走出暗室,又上了那幢小阁楼。还是那个卧室,还是那个老太婆和躺在床上的蒙面女人。老太太望望伍单,一脸谢意。伍单为床上的蒙面女人去掉了在刀口里下的捻子。那乳已经消肿,恢复了它原有的很挺的模样,很美。伍单对老太太说:“太太,已经没大碍了,过几天伤口就长严了。”老太太感激地对伍单说:“谢谢先生!这几天委屈先生了!请你不要见怪,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说完,让那丫环端出一盘大洋,对伍单说:“请先生笑纳!”伍单望着那盘白花花的大洋,傻了一般,连连地说:“用不得这么多!用不得这么多!”老太太笑笑,让那丫环将大洋一下子倒进了伍单的药箱内,然后才让她领伍单下了楼。
还是那个车夫,还是那辆马车,还是午夜时分,阔大的宅院里还是无一丝灯光。伍单在黑暗中离开了那座宅院。从头至尾,他不知去了什么地方,进了哪座府第,给谁治了奶疮,留在脑际里的印象大多是漆黑一片,像做了一个梦,一切全不真实!
但大洋却是真实的。伍单发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财,日子比过去好过了不少。
从此以后,伍单就将此次出诊当作了最美好的回忆。
试 堂
黄慎,原名盛,字公懋、菊壮,曾用艺名江夏盛。康熙六十年得知南海居然有位同名同姓的画家,遂更名黄慎。雍正四年改字恭寿,取别号瘿瓢山人。并用木瘿刳制瘿瓢,腹沿刻草书“雍正四年黄慎制”七字,口处沿尖端镌小八分书“瘿瓢”二字。此瓢现仍藏扬州商宝松家。画家亦用过东海布衣、苍玉洞人、糊涂居士、放亭等别号,均有史书记载。
瘿瓢山人,少孤。父巨山客死于湖南商途时,黄慎年甫十四,其弟刚满三岁。家徒四壁,可谓一穷二白。其母独力撑柱,夜勤女红,无膏火,拾松枝燃照,或走附月光,严冬风霜,犹著苎布裙,手指皲裂无完肤,且以所成命子操入市易米,进二老。而糠秕做羹,偕子女共食。可见孝顺至极。
“慎之寄于画,非慎志也,为谋吾母之甘旨。”“慎非画,无以养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频年饥馑,无从得食,慎大痛,再拜别母,从师学画,年余,已能传师笔法,闯荡乡间街巷,鬻画供母。
黄慎一生善写人物,多取材于神仙传说、佛像和士大夫生活,也画樵子、渔翁、纤夫、田父、绩妇、漂母、算命盲叟,多是些小人物。据说还画过《群乞图》。说是雍正帝要御封一名宫廷画师,同乡雷铉有意举荐。黄慎进京应试,其他人都呈歌功颂德之作,唯独他画了幅《群乞图》,“道旁饿鬼嗤嗟来,摇尾乞怜殊碌碌”,描写的是灾荒年月家乡寿宁桥头饥民惨景。皇帝龙颜大怒,掷画于地。为此,黄慎差点儿掉了脑袋。后人分析当时黄慎除有为民请命之心外,可能还怀有出奇制胜的妄想。怎奈雍正并不像三百年后电视上那个被美化了的雍正,所以黄慎之妄想自然要破灭。
大概就是这次进京,这瘿瓢山人曾路过陈州并小住,与陈州名书家“不堵笔”有过一段交往。据《陈州县志》载,当年黄慎在陈小住时,不但交往了“不堵笔”,与当时的知县宋典也十分投缘。那宋知县还曾为他写过一个小传:
山人落拓,性耿直,然绝不作名家态。画时,观者围之数重,持尺纸更迭索画,山人漫应之,不以为倦。虽不经意数笔,终于俗韵。画已辄睡。颇嗜果饵。睡久不起,撼醒之,贻以时果,则跃起弄笔,神举益壮旺。每题画毕,必凭几掉头,往复吟哦,不能自已。
宋典字长文,山西运城人,颇有文采,喜书画。黄慎在陈州的那段时间里,他常去“不堵笔”府上拜望。“不堵笔”姓孔,名宪邦,字朵颐,由于书画在陈州一带名望大,人送雅号“不堵笔”。这“不堵笔”当年曾在淮北居住过一段时间,与黄慎算是故友。不料宋典与黄慎也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二人相熟之后,宋知县就为黄慎写了这个小传。黄慎看后甚喜,禁不住摇头晃脑念了一遍,然后又让孔宪邦高声朗读,并要求亦做摇头晃脑状。三人嬉闹,如孩童般。读到高兴处,“不堵笔”激情迸发,顿感技痒,挥笔将传文写一遍。宋典和黄慎一看“不堵笔”笔力苍劲,字体潇洒如舞,皆赞叹不已。宋典也心血来潮,对黄慎和孔宪邦说:“如此妙笔,我定将其刻于碑上而扬之!”
等送走黄慎进京之后,宋知县果不食言,当下就请来了石匠,要将自己写的传文和“不堵笔”的鸿爪刻于碑上。
不料,石碑刚刚刻好,黄慎得罪皇上的消息就传到了陈州。宋知县闻之大惊,生怕自己给黄慎写的小传泄露,也要陪着黄慎掉脑袋。因为他知道这个雍正干起文字狱来比他老子还厉害。一个堂堂知县为何要给一个穷画师写小传,而且将其写得憨态可掬,是不是你也见过《群乞图》,很赞扬他这种以画进谏的精神,所以才为他树碑立传?如此一分析,宋知县头上直冒冷汗。左思右想觉得应该先将碑砸烂。于是,他便命人将石碑砸了。砸过石碑之后,他仍觉得不踏实,又将自己的手稿和“不堵笔”的“鸿爪”也一齐焚烧了。烧过之后,他还觉得不踏实。心想虽然碑已砸了,底稿也烧了,可若有人告发此事,皇上一定会派人追查。若皇上追查起来,不但自己遭殃,还会连累“不堵笔”,怎么办?自己丢官事小,而陈州少了“不堵笔”事大。想来想去,觉得应该先见见“不堵笔”,将此事告之,与他思考出对策为妥。当下宋典就去了孔府,将黄慎进京遭遇向孔宪邦说了一遍。孔宪邦一听很是惊诧,对宋典说:“这个瘿瓢,在陈时也不向我们说他进京干什么,更没把《群乞图》让我们看一眼,如我知道他要向皇上献这玩意儿,我定会劝阻他的!”宋典说:“事已至此,抱怨也晚了!当今皇上很忌讳这个,如果他老人家动怒,肯定要一查到底!现在不是保黄慎兄的问题,而是要保你我!”“不堵笔”望着宋典,想了想说:“这事儿与咱们有什么事儿?”宋典说:“尊兄不知,眼下人心险恶,如果黄慎真的有事儿,肯定会有人借机陷害你我。尤其我还写了个小传,你又书了一遍,我还刻碑以扬之,若有人借此做文章,这脑袋说掉就掉了!”“不堵笔”听得这话,方知宋典所说不是戏言,吓得脸色都变了,好一时方说:“你给菊壮兄写的小传,除去咱三人别的很少人知晓,若皇上派人来查,你我皆不承认有此事不就得了!”宋典说:“尊兄不知,只要皇上钦差一到,会先把你抓起来!只要一将你抓起来,肯定要审问,你开始不招,但一过大刑,就怕你招架不住了!”孔宪邦望了宋典一眼,笑道:“贤弟所言差矣,我孔某还不至于那般软蛋吧!”宋典摇了摇头说:“不是我不信你,你肯定过不了关的!在那大堂上,多少壮汉都招了,何况你一介书生!”“不堵笔”看宋典对自己不但不放心,而且还有些瞧不起的意思,很是生气,禁不住赌气道:“你若不信,这样吧,我就先到你的大堂上试一试!”宋典一听这话,忙说道:“不可不可,万万不可!若是假试,你自然受得住!若是真试,怎好让你老兄受那种皮肉之苦!”不料孔宪邦却很坚决,不在乎地说:“过堂就是真过,哪个要你假试不成!”接下来,宋典越劝,孔宪邦越是认真,而且过堂以试自己的决心越来越迫切。万般无奈,宋典说:“既然是过堂,总得有个理由呀!”孔宪邦说:“嗨,你身为知县,想个理由还不容易!”
宋典这才施礼道:“那就别怪小弟无理了!”言毕,深深给孔宪邦鞠了一躬,然后急急回到县署衙,以孔宪邦犯有谋反罪将其抓到大堂,先让衙役们重打了他三十大板,问其招是不招!孔宪邦有言在先,自然不招。宋典见其充硬,便让其上老虎凳……如此几个回合没过,一介书生孔宪邦就被活活“过”死了!宋典看孔宪邦如此不经打,很是悲痛。为掩人耳目,他只好模仿着孔宪邦的笔迹写了一幅反诗,呈报上去,算是结了案。
不料,刚刚整死“不堵笔”,从京城又传来消息,说是皇上只是将黄慎绘制的《群乞图》掷于地下,最后并没治他的罪。宋典听后先是一怔,最后长出一口气,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说:“宪邦兄,你那般认真,何必呢!”
作者档案
孙方友:男,1950年生,河南淮阳县新站镇人。1968年毕业于淮阳县第七中学,1978年参加工作,历任淮阳县新站乡文化站站长,淮阳县文联秘书,河南省文化厅干部,《传奇故事》杂志编辑,现为河南文学院专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