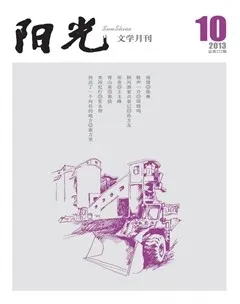难忘的故乡情结
在众多忘年交的中青年作家中,我与徐迅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不仅在文学方面,在政治理论方面,也有很多共同语言,仿佛没有“代沟”的感觉。我们同住北京,却又不能经常聚会畅所欲言——他太忙,也太累!
我常常面对着他那厚重的几部散文作品,还有其他作家赠我的许多作品,陷于深深的自责之中,一种负债似的自责!我总是把同他们的接触和阅读他们的作品,当是一种精神的享受。
他那清瘦、单薄、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形象告诉你,他不是从矿井里“爬”出来的作家,他是现代文学大师张恨水先生的小同乡。
如同许多矿工作家走向社会受到欢迎一样,作为著名散文作家的徐迅,同样受到煤矿的欢迎,并被推举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兼秘书长,还担任《阳光》杂志社的社长兼主编。他既完成了对张恨水的研究任务,出版一部厚重的《张恨水家事》;同时对煤矿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发展、对矿工作家队伍的成长和崛起作出了应有的奉献。于是,我总奉承他“比张恨水幸运!”既没有像鲁迅当年告别故乡“异地谋生”的悲凉感,也没有像张恨水那样到处漂泊流浪的苦恼。他的心情坦然、平静而自豪!
但是,他同鲁迅、张恨水一样,深深地怀念着他的故乡!
收录在《某月某日寻访不遇》这部集子里的短篇小说,每篇都在两千字左右,是以一种散文化的舒畅笔法,展现了他的故乡——皖西南丘陵小县的风情景观、人情世故。所以我把它们定位为“散文式的小说”。虽然由于篇幅所限,故事显得片断,人物形象也只取其一个侧面;但却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对生他养他的故乡、故土怀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怀念。而且故事里的人物、情节、细节都那么生动传神,语言精炼简洁,并适当地使用了方言土语。具有浓重的地域特色和历史特征。是一部接地气的作品。
故事的时代背景,发生在上世纪末,国家经济转型时期,工商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农业由“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向“分田到户”转轨。作品深刻地揭示了在这社会变革时期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人性、人情的变与不变的矛盾冲突。
一
老一辈,对传统美德思想阵地的坚守和对儿孙后代的期盼,担心日子过好了后代出“败家子”。
看了《九十老奶》,很自然联想到鲁迅小说中的“九斤老太”,她总是唠唠叨叨夸耀自己的男人生下来就九斤重,而下一代却是八斤或者七斤半,结论是一代不如一代。——毕竟时代不同了,九十老奶对新社会充满爱慕和欢欣,她要发挥自己的专长和爱好,为促进社会的和谐做一点儿有价值的奉献(升华一下,也可以说是“九十老奶美好的人生观”),她把嫁妆留存下的丝线,做一些绣花丝带,肚兜、围裙、童鞋等物件,分送给邻居。却被“干部们”批为“拉拢人”,她惊惶失措,“洗手”不干!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这些小物件被称为工艺美术品,可以换钱了,她很高兴,不计价格,给钱拿走,只求一个乐和。却又被退休的儿子指责为“丢丑”,甚至把她困在屋里不准出门。九十老奶左右为难,抑郁而死,谁之错?——“极左”。
曾经是红军英雄的《焦二奶》,因部队失散流落异乡,新中国成立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因“来历不明”被批斗、管制;但她革命意志不变,忍辱负重,始终密藏着红军暴动时那面红旗。直到弄清她的身份,落实政策,承认她是“老革命”。她却拒不接受,她悲伤、她寒心,她暗暗地唱红军歌曲以示发泄。她把红旗深深地埋在地洞里,埋在心里!她发现儿子偷走红旗卖给文物贩子,大骂儿子是“败家子”,倒吸一口冷气,栽倒在埋红旗的地洞里——一个飒爽英姿的女红军战士的形象,久久地耸立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留给后人的是无尽的伤感和悔恨!
《涅槃》中的外婆,是“土改”中的一面旗帜,丈夫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作为老烈士“五保户”,受到全村人的敬重;唯独负担“五保”的三户人家,多方刁难、虐待和谩骂。外婆总是以宽厚仁慈应对,劝告愤愤不平的外孙不要激怒,要谅解“家家都有难念的经”,要感谢公家的照顾。外婆用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感支撑自己的后半生,用所有的母性与亲情的爱浇灌了外孙的人之初,也用这种荣誉感教育外孙的成长。
年逾古稀的奶奶,在儿孙的心目中是个“凶煞神”。她总是气势汹汹地教训儿孙要勤俭持家、要节约朴实,不然没吃的要喝西北风。最让儿孙们刻骨铭心的是,她面对着孙子的双卡收录机,撕心裂肺地哭诉家史:她七岁死了爹娘,哥嫂养不起,做了童养媳,砍柴、下河、挨打受骂、吃不饱穿不暖。那年日本鬼子来了,抓走你跛子大爹,奸杀了你大姑奶奶,刺死你小姑,我用手挖坑把她埋了——儿呀儿,如今日子过好了,你们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做童养媳时哪像你们!——奶奶在忆苦思甜,奶奶在进行传统教育。《奶奶不死》,奶奶的精神不死!年届不惑的孙子还深深地记得,十岁时,奶奶为了维护家族的声誉打他那一巴掌。
二
改革开放,给人们提供了各尽所能发家致富的机会,却引起“致富”和“妒富”的矛盾冲突。妒者不惜“嫉人”于死地,而能者则于“死处”求胜。
《瞎爷》原是公社的生产队长,分田到户他不要;他眼力不好,却会说书,什么《薛仁贵征东》《哪吒闹海》《白娘子》,讲古聊白,吐沫星子乱飞。给人以乐,自得其乐。外出一年,人累瘦了,腰包却鼓起来了。于是,眼红的便向上告状,说他宣传迷信“诈钱”。于是,他被关进乡政府的“小房子里”,于是他气急败坏病而拒医,于是抑郁而死!
《辣子嫂》丈夫肺痨病无力种田,她风风火火进省城学会养蘑菇,县里扶持,银行贷款,成了养殖专业户,赚了钱盖起新房。“长舌妇”们的流言蜚语跟踪而来:说她能贷款是因为给银行“放骚”。偏在这时银行催她还贷,因管理不善,杂菌感染,蘑菇霉烂,丈夫听信谣言,向怀孕的辣子嫂施暴!辣子嫂难以忍受这精神的屈辱,羞恨交加,投塘而死!
《孝女》因年幼无知,除夕夜缠着父亲要钱买花衣,父亲人穷志短,感情脆弱,羞愧难当,投皖河而死。于是孝女便被人骂为气死父亲的“扫帚星”。村里姑娘纷纷出嫁,她却成了“剩女”。但她不气馁,挺身而出办起“淘沙场”,不到一年,竟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户”,带动全村以至满河满汊都出来淘沙。于是孝女乘机张罗成立淘沙公司,众人仍嫌她是“灾星”,不予理睬。孝女一怒之下,考上“新世纪新星歌舞团”,“长舌妇”们又骂她“不是正经货”。几年之后,乡亲们从电视里看到一个“红歌星”——不过她不叫孝女,而叫“婉女”了。
中国是几千年的农业大国,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有勤劳朴实的一面,也有狭隘自私愚昧落后的一面,嫉妒,就是愚昧和自私的衍生物。他们的思维逻辑就是:只准我富,不准你富;我穷,你应该比我还穷;你富我就整你,甚至用“舌头压死你”。他们主张“你有我有全都有”的绝对平均主义,这就是农民的劣根性,是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从不平衡到平衡,受穷可以“齐步走”,致富就必须让一部分(能)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然后共同富裕。靠《树神》吃供品的阿Q式人物“五佬”和不种田吃救济的“憨伢”,只有人嘲笑,却无人嫉妒。于是故乡便演绎出一幕幕悲剧、闹剧和传奇,作者把那个年代故乡生活的真实演变成艺术的真实,读来别有一番滋味。
三
面对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最是骚动不安的是那些青年男女,他们对爱情、婚姻、前途、事业的追求和向往,心情的惆怅、彷徨和沮丧,是那个年代农村生活的一大特征。作者怀着亲切的同情,为他们呐喊。
高考落榜的《王银亮》,回乡当民办教员,与女青年彩彩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很自然地进入爱河;但好景不长,县里下了文件:“1978年以后招收的民办教师一律辞退。”原来看重王银亮的彩彩爹,对他们的爱情断然拒绝。王银亮心灰意冷,惶恐焦躁中竟然要带彩彩私奔,并放火烧了彩彩家的茅房,于是,王银亮进了派出所。彩彩蔫了,王银亮傻了!
在《绿太阳》沐浴下成长起来的沪子是幸运的。他凭自己的品行和才干竞争上岗当上护林员,身穿警服成了英雄。虽然遭到辣子娘的嫉恨,却赢得美丽善良女子荷莲的爱情和全村人的尊敬。
火热的太阳晒得人火燎燎地疼,害着严重肺痨病的老黑,气喘吁吁地扶着犁把和大沙牛一起痛苦地挣扎着。大声地吆喝儿子“你滚回去看书去”。老黑决心要儿子考大学,以改变古老的谚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但儿子不忍心耗尽父亲的心血圆他的大学梦,他猛然夺过犁把,“不学ABC,一样干革命”。显然,儿子要在农业战线上干出一番事业,为自己、也为国家争一份光荣!
许多青年人都希望走出去,走出自己的老屋,走出脚下这贫瘠的土地,走向社会,开眼界闯事业;事实上,走出去也不可能《一路平安》,但是“我”必须走。“我”已经是在地方国家机关拿上公文包的人了,虽然心情忧郁沮丧,但要守纪律,要尽职尽责。走,不能性急,那年月要等待的事情太多:在冰天雪地里等那招手难上的破汽车或小三轮,食堂里排队等买饭,锅炉房等开水,恋爱等对象,结婚等房子……身材瘦弱、一脸斯文的张文,心情烦躁想《找人打架》,结果被人打得鼻青脸肿,眼镜脱落,遭到医生的一顿奚落,仍然愤愤不平!令人懊丧的是狡猾的老鼠也以张狂的姿态欺侮人,偷吃他的口粮,啃坏他的图书,咬破他的蚊帐,于是,他忍无可忍,愤起《抵抗》,结果又闹出许多笑话。
作者以同情和怜悯描述了这些生活琐事,给读者的是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寓教于乐”吧。
四
酒,是中华民族饮食文化之珍品,也是中医药文化之精品。但在社会变革,经济转型时期,它的价值、命运和声誉也随之变化。智者可以用它激励心灵,创造传奇:古有“李白斗酒诗百篇”“曹操煮酒论英雄”;今有国宝学者、九十高龄的季羡林以酒为长寿之友。在社会的人际交往中,以酒作媒,也可成就一番事业。但是,如果为愚人所用,特别当它登上官场的餐桌,就会变成奢侈品,甚至毒品!在人民群众中声名狼藉,遭人唾弃!
《等人吃饭》在这些短篇中是最长的,也可以说是思想性艺术性俱佳之作。它没有直露地描绘官场餐桌上那种推杯换盏、猜拳行令、呼天嚎地,丑态百出的场面。而是通过乡办主任杨和尚“等人不遇”的生活经历,巧妙地揭示了一个乡政府机关贪污腐败的内幕。乡政府驻地面临国道,于是由国库开支沿国道建起一些可以吃喝、住宿、打麻将的饭店。南来北往的上级机关官员常到附近钓鱼玩乐,自然也就是饭店的常客。杨和尚的父亲曾担任过乡政府“计生委”干事,这是个肥差;好烟、好酒、好礼品来者不拒,“革命小酒天天醉”。并通过向上送礼,使杨和尚由一个小学教员荣升为乡办主任,一个响当当的股级官员。他唯一的任务就是迎来送往,陪客吃喝。国道上车来人往络绎不绝,但他要等的“小车”却一天未见。于是他为官员们准备的酒席,便由他的狐朋狗友饱餐一顿。
杨和尚洋洋得意,经常夸耀说:“我的肚子像国库一样,吃了空,空了吃;国库吃不坏,我的肚子就吃不坏。”杨和尚这句话可以视为贪者的“经典”。当时官场上就流传着这样的谚语:“不吃白不吃,白吃谁不吃……”
杨和尚跪在奄奄一息的父亲床前,等候遗嘱,父亲垂死挣扎,挤出两个字:“酒,酒。”旁观的亲友们都笑了,“这死鬼喝酒把肝都喝坏了,临死还要喝酒。”随后,父亲用最后一口气接着说:“你,不,要,喝,酒。”头一歪,闭上了眼睛。
还是母亲的结束语语重心长:“喝一生的酒,丢一生的丑。”
改革开放三十年,徐迅的故乡像全国一样,肯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期待他第二部具有故乡情结的小说集出版。
成善一:88岁抗战老兵,原煤炭部政工干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上百篇政论和文学作品发表于各大报刊,出版有《活着,不要辜负生命》《活着,要有点精神》等多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