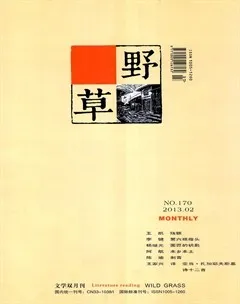本乡本土
对一次笔会的回忆
十数年前,我刚刚练习写作不久,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参加了县文联本年度的石门洞笔会。那次笔会的人数估摸十多人,大多为年轻的男女,只有一人例外,那人姓徐,已六十开外。这姓徐的先生人长得精瘦,头发斑白,平时不苟言笑。我因为是最末一个抵达的,便被安排与徐先生同宿一室(他人均不愿意与之同房)。
石门洞是处消暑的好地方,我们那次笔会持续了十天时间。记忆中好像我们喝了许多啤酒,吃了不少溪鱼。天气实在是太闷热了,众人皆说这日子只能喝喝啤酒聊聊天,那爬格子的苦差事是没法干的。这里照样又是那位徐先生是个例外。他不喝啤酒也不与他人聊天,每日里关在房间里勤学苦练。徐先生写作时的身姿我至今尚记忆犹新。他盘腿坐于床沿,弓着背,旁若无人地在那儿写呵写。有时候实在是热得他喘不过气来了,他就脱了那件形同鱼网的白汗衫,只留着个北京蓝的大裤衩——依然是写个不停。徐先生的肋骨历历可数,锁骨深陷,都可以盛两调羹水了。我对他的这种吃苦精神,是有所感触的,但私下里却又认为:这是何苦呢!
我和徐先生同宿一室个把星期了,但我和他还是如同陌生人。我们两人基本上没搭过话,就如同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般。我每天一睁开眼就往外跑,一直到夜里很晚了才回房间,躺倒即睡。在我的印象中,徐先生始终是以一种姿势盘腿坐在桌前,不停地写作和抽烟。因为当我躺下睡觉时,徐先生仍点着蜡烛(那地方夜里11点钟就停电了)在那儿写,而当我一觉睡醒起床时,他却因了“闻鸡起舞”的古训,早就起来又写了。所以在我和他同房的十余天的时间里,我是从未见他躺在床上睡觉过的。
大概是第七天吧,他那篇日夜兼程写着的稿子杀青。这天我见他将笔狠狠地往桌面上一掼,咳出一口浓痰。我还是不敢问他这缘于何故,提了脚尖往外走。我来到地区来的叶编辑房间里,想拉他出去散步。徐先生推门进来了,他的两眼布满血丝,整个人的神态却是容光焕发。徐先生中气颇足地说道:“叶老师,我的小说脱稿了!”叶编辑是位戴深度近视眼镜的中年人,有三分书呆子气。他反问道:“什么小说?”徐先生嚷道:“就是我上次对你讲过的呀,‘阿花偷西瓜’呀……我终于把它写出来了,替老实人出了一口气!”叶编辑不耐烦地说道:“我们要出去走走,什么‘阿花偷西瓜’再说吧。”徐先生说:“你就先给我指导指导吧,我肯定还要修改的,你先给我说说,我好开窍!”叶编辑接过徐先生那迭稿纸,翻得哗啦啦响。“写得……还不错,不过嘛,还要补充一些,加强力度。”叶编辑话还没讲完,就已将稿子塞还给徐先生了。徐先生眼球暴突,大声嚷道:“叶老师你是好眼力哩,你这话讲到我心上去了,我自己也觉得这文章写薄了,对不起老实人啊!”叶编辑厚镜片里头的一对眼睛一动未动,“什么老实人?”徐先生道:“就是我小说中的主人公呀,阿花是个泼妇,老实人是个好人,我要惩恶扬善,替老实人出这口气!”叶编辑无可奈何地晃晃脑袋,拉上我往外走。
在江边渡口,我和叶编辑见徐先生拎着人造革黑提包火急火燎地赶过来。出于礼貌,叶编辑问徐先生哪里去?徐先生嚷道:“还哪里去!我要回家拿材料,非让老实人这个形象有血有肉不可!”叶编辑知晓和徐先生没法缠清楚,就问他家离这儿有多远?徐先生答说很近的,就二十里地。叶编辑又问有车吗?徐先生捋上衬衫袖子,紧着牙关说道:“我会爬拖拉机的。”
我和叶编辑在江边徜徉,时间于不知不觉中滑走。对岸有人扯开喉咙喊渡船快快过来!我们抬头一瞧,却是那徐先生回来了。叶编辑笑道:“这徐先生也真是神速呢,怎么已回来了啊!”我也笑着附和道:“这老先生简直就是个少先队员嘛。”这边的船老大嫌那边只有一个人,懒得马上就摆渡。这可急坏了岸那边的徐先生了。但见他拎着那只黑包一边在江边来回疾走;一边高嗓子喊渡船快快过来。他见这边仍纹丝未动,一焦急就摞上裤管往江水里趟。在阳光下,徐先生犹如一匹烈马直奔过来,水花四溅,真可谓有几分悲壮的意味了……
一天夜里,我正在熟睡,徐先生将我搡醒。徐先生压低嗓子对我说道:“我有点事要问你哩,阿花她偷了西瓜,反倒诬陷老实人调戏她,生产队里罚老实人放了场电影。老实人堵着这口气回到瓜棚,这时天上雷电交加,下了一场暴雨。老实人那晚的心情,你是知道的,非常地难受,所以那雨用‘掉’下来是不是太轻了?我想用‘砸’这个字,你认为怎么样?”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得叫徐先生拿稿子来过目。原来徐先生这篇没日没夜操劳的稿子仅两千余字。写的是农村里一个叫阿花的刁钻妇人,佯装大肚子(在衣裳里塞进些许茅草)跑到老实人看守的瓜田蹲下撒尿,然后掏出茅草塞进西瓜走人,屡试不爽。老实人苦于瓜田的瓜老是被偷,受生产队长的训斥。后来老实人终于搞清楚问题的症结是出在阿花身上——阿花大肚子是假,偷瓜是真。有一天阿花又蹲在瓜田里小便,掏出茅草装进西瓜时,被老实人逮了个正着。可阿花猪八戒倒打一耙,扬言老实人脱她裤子要强奸她。生产队长不问青红皂白,骂老实人原来一肚子坏水,居然会起花心,罚他在村里晒谷坛放一场电影给村人看。是晚老实人回瓜棚时,为了烘托气氛,徐先生着意写了一场暴雨袭下来。我草草看过全文后,觉得徐先生将“掉”改成“砸”字是有道理的,便如是说了。徐先生在房间里兜着圈子踱步,一拳击在掌中嚷道:“就这么定了,用‘砸’字!”
后来我和徐先生有过一次交谈,知晓他本为书香门第出身,解放后因成份不好遣返回乡务农。他说他从读中学时代起就埋下了那颗文学的种子,多年来在乡村一直边种田边笔耕,但从未有过一个文字变成铅字。在文革时期,他曾经有一篇稿子被某家杂志社看中,对方写信来叫他去公社开具个人简历证明。在那个年代,出身不好的人是不能发表文章的,故此事也就黄了。徐先生藏着那封编辑给他的信。他那天火急火燎地回家去取所谓的“材料”,那其中就包括有这封信。多年以来,这封绝无仅有的“编辑来信”,一直像盏海上的灯塔,指引和鼓舞着徐先生在文学这条道上走下去……那封已经发黄的某杂志社的编辑来信,徐先生郑重其事地拿出来让我看过,实在是很平常的一封“编辑套话”信函。说真的,那天和徐先生“推心置腹”地交谈过后,我的心情颇为沉重。
最末一天,笔会组织者置办了两三桌酒筵,算是善始善终的意思吧。大伙坐齐后,惟独不见徐先生的影子。县文联的主席说我们只管开始吧,徐先生那人反正不会喝酒的。话音未落,便听得楼梯口一声大叫:“谁说我不会喝酒!”原来徐先生手拿稿子从楼上下来了。那时节徐先生的形象,真可以用“鹤发童颜”这个词来加以形容了,神采奕奕尚有几分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意味。徐先生款款而来,拣了位置坐下,让人给他倒了一海碗啤酒。众人皆有些惊异,纷纷问道徐先生你也会喝酒的?徐先生有板有眼地说道:“我非但能喝酒,而且酒量无边,不敢跟李白比,但在座的诸位,嘿嘿,我是一点不怕的!”叶编辑嘴边挂着讪笑,问道:“徐先生,你是不是替老实人那口恶气出了?”徐先生端起那只海碗,移步至叶编辑身旁,先将那稿子递给了他,然后说:“叶老师,我们干一碗吧,老实人的气替他出了,这篇稿子,就交给你啦!”叶编辑推了一下眼镜框问道:“你这稿子交给我干吗?”徐先生将叶编辑从上至下地打量了一番,“不是说……我这稿子好么,我给你们杂志发呀……”叶编辑说:“徐先生,你都一大把年纪了,怎么还会像小孩一样不明事理呢,我那是敷衍你几句的呀!你这种稿子能说是小说吗?充其量只能算是则民间故事罢了,我们的杂志可是本纯文学杂志,你说能发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吗?!”徐先生那平端着碗的手,眼看着一抖一抖地往下沉,——他终究没将碗掉落在地,一句话没说回到自己的座位。徐先生将那碗酒一仰脖子喝下肚去,没碰筷子就上楼去了。
吃过饭后我上楼时,但见徐先生在整理自己的东西。我问:“今晚就走?”徐先生抬起脸来看了我一眼,嘴巴张了两张没出声。徐先生就像散了骨架似地摇摇晃晃地提上行包从房间里走出去。片刻后,我扑到窗台上目送徐先生远去。适时周围静悄悄的,昏黄的天层下微风拂动,徐先生跨过那座石拱桥,身影消失于树林之中。
夜晚我回到房间时,推门进去里头黑咕隆咚的,这让我有些不习惯。因为在这十余天里,我每次回房间时,里头皆会点着灯,有个精瘦的老人趴在桌面上的剪影在那儿摇摇晃晃。我打燃打火机,找那支蜡烛——点燃蜡烛时,我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那被徐先生用作烛台的一块马粪纸板上,结着一块形同倒扣的白壳碗般大小烛渣。徐先生他每次都是未等蜡烛燃尽就将一根新蜡烛插其上头的,九个夜晚下来,竟然结成了这么一大块!好像古人有将这烛渣形容为“烛泪”的说法,这么说来,徐先生他在这九天里该是淌下了多少“烛泪”啊!
想象之地
如果没有记错,我对奇云山的最初印象来自于照片。照片为本县老一辈摄影人拍摄的黑白照,《奇云山天然牧场》。几头牛迎着朝阳或夕照,徜徉于茅草地上,十分地空旷和邈远。这幅画面长久地停留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召之即来,让我浮想联翩。后来梅王平兄等人上山露营,天高皇帝远地高谈阔论,营造些许小磨难,而后吃饱喝足围拢火堆眺望天幕星辰。他们拍了片片,同时写了文字。我通过网上看了片片读了文字。文字感染力一般,而直观的片片,让我对奇云山好感加深。我想象的世界中,出现了钢蓝色的夜空,星星金属般闪烁,非常地富有质感。奇云山因至今尚未通公路,所以要想上去是有点难度的——正是由于这点难度和距离,奇云山对我而言扯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有过几回上山的打算和安排,皆不了了之。有时候我纳闷,我这个好山水之徒,足迹差不多已踏遍全县的角角落落,怎么就迟迟没登上在本地小有名气的奇云山呢?距离肯定不是问题,问题恐怕在缘分上。我与奇云山的相遇时间大概还未到吧。有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那就是我此生必定会登上奇云山的,只管顺水推舟即是了。而且,有那么一座山让我想象着,丰富着,并非坏事啊。同时,我心里也是有一个想法的,那就是趁所谓的“开发”尚未运作前去趟奇云山吧。这就有点紧迫感意思了。以往的事例或者说教训,值得人警醒一些。同样是在方山乡,当年原生态的龙现村,豁然开朗、柳暗花明、鸡犬相闻,均搭得上边的,让人沉醉,让人暂且与尘世隔离开来偷偷吸口仙气。但随着一系列的紧锣密鼓,硬化工程亮丽工程和形同公厕放大无数倍一般的大屋拔地而起,接地脉的农耕文化气息荡然无存。这个时候我除了怀念,再就是庆幸了。我是在龙现村没成“田鱼村”之前去过那村落的,我脑子里头有它原初的影像。这是养心的。本地另一座颇具名气的山是金鸡山。金鸡山现时正在造延伸段的公路,遍体鳞伤。我搞不明白,我们人类面对自然界的时候,怎么就没一点点敬畏之心呢?本来公路造到停车场那位置,花上半小时拾级而上,既维持住了主峰的气场,又让人得以锻炼脚力及享受一番沿途风光,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非要把汽车开到那巴掌大的主峰上呢?上苍赐予我们人类的自然面貌,不可再生,一旦毁坏是永远不能恢复的。
初冬的日子里,我登上了奇云山。我去奇云山当然是为了游玩,同时也是为了一睹“庐山真面目”。说不定用不了多久,奇云山的真面目就要走样了,因为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上山和下山分别走了两条道。上山的路陡,视野不开阔,不过到一定高度后能鸟瞰方山全乡面貌。方山是个好地方,群山环绕,形成天然屏障,形成小气候,形成别样的风土人情。梦溪就曾说过他很喜欢方山。在他眼中,“方山”俨然是一种气韵,一种灵动,可以在具体的女孩儿身上得以形象化体现,说不清道不明但却能体察与感受。说来有趣,由于“锅底”地貌的效应,我在距离底下村庄很远的山上,却能清晰地听到来自下头市井的声音——卖肉噢——卖肉噢——。我对一块儿歇脚的小文友说,真静啊!
奇云山的特色是高山湖,还有高山草甸。高山草甸其实就是湿地。也就是说奇云山是座水资源丰沛的山。我对一座孤零高山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水的问题感到困惑。一文友说他的理解这儿是个火山口。另一位则说,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静谧的湖水映照着蓝天,两相衬托,是一种冷冷的蓝,单纯的静。真不忍心打扰它啊。湖水里长似睡莲水草,比睡莲叶子要小许多,根须老长,弯曲于明澈的水中。我想象,月亮当空时辰,此地该是何等景观啊。抬头看天,天空湛蓝,虽说没我想象中的那种钢蓝色,没那般凝重,但同样让我战栗。山上没有高大树木,哪怕稍稍高点的植物都没有。松树老气横秋,灌木丛里手指头粗细杂柴,恐怕都有十数年的树龄了。俗话说树大招风,山高更为招风了。严酷的自然条件下,树木没法长大长高,树皮呈黑色,坚硬如铁,诉说着生长时期的不容易。据方山乡的陈乡长介绍说,奇云山上共有三十六处高山草甸。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也是一个诱人的数字。当今有许多人都已知道,湿地对环境的调剂作用,是其他任何物体所无可替代的,故而权贵们喜欢居住或者度假于湿地周遭。这无可非议。问题是像这种生态环境,是极其脆弱的。人类如若盲目地进入和占有,必将破坏自然界的平衡。
秋季已过,初冬的气象难免几分肃清。奇云山上的高山茅草,失去明丽的色泽,失去了金灿灿的色感。枝杆上的淡白色花绒,黯然无光。不过在一望无际的蓝天下,在明媚透气的阳光里,它们依然是美丽的。满山遍野的高山茅草,闪闪烁烁,在风势的运行下左右摇晃,让人眩目和迷离。山坡舒缓,山道染苔衣,山顶屹立巨大怪石,天幕是那般地近在咫尺,太阳如一圈白色球体。这是我们在下山的另一条道上所见到的景致。我想起一些古时场景,不由得脱口而出道,剑侠箫心!
【责任编辑 黄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