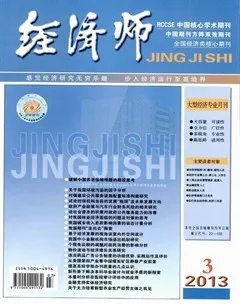离婚案件夫妻共同债务举证责任分配的立法缺陷及实践问题
摘 要: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施行,弥补了我国原有的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一些漏洞,增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许多明显不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这又诱发夫或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伪造债务,侵吞夫妻共同财产等严重问题;而且有关立法内容较笼统,不详尽,不能适应复杂的社会现实需要。所以,现行婚姻法的夫妻债务认定制度亟待完善。文章对我国现行婚姻法的夫妻债务认定制度作了现实和理论上的探讨,分析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立法的不足,提出了从立法和司法上完善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的建议与设想。
关键词:夫妻共同债务 立法缺陷 司法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3-070-03
一、立法有关举证责任的规定
关于离婚案件中夫妻共同债务举证责任的分配,依据《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即债权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如果夫妻另一方不能依据两个“除外”规定,举证证明这一债务是夫妻个人的单方债务则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此规定可见,夫妻另一方(指非举债方)存在两种证明责任:一是能够举证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指实际举债方)已经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二是能够举证证明夫妻双方采取的是约定财产制,且还能证明债权人知道该约定的。所以,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对夫妻一方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的证明责任,实际上强加给了夫妻另一方即非举债一方。
二、立法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缺陷
从理论上来说,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是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举证责任分配问题的简单化处理,容易产生错误的利益衡量。公平正义原则是分配举证责任的最高法律原则,它是分配举证责任最初的起点和检验分配是否适当的最后工具。{1}依据婚姻法解释中关于举证原则的规定,实际上是免除了债权人证明债务为夫妻共同责任强加给了债务人的配偶,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公平的,但是,从深层次上看,这样的举证责任分配对债务人的配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1)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担原则,债权人主张权利,仍应就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以及自己权利产生的事实、理由承担举证责任,并且有实际举证的能力。因为债权人在债务发生过程中,掌握了选择、决定是否与债务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的主动权,并且可以在债务发生前采取要求债务人提供担保或者要求债务人夫妻双方共同签字认可等一系列措施,以保证债务实现,减轻风险,也有为以后发生纠纷时准备充分证据的能力。所以,按照公平原则及有关举证责任的一般法理,债权人都应当要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2)在证明“债务人与债权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问题上,夫妻一方与债权人约定的个人债务发生纠纷后,这个债务的性质就成为夫妻另一方与债权人争辩的焦点。根据推定规则,债权人无须证明,而债务人配偶却要证明债务人与债权人在争议之前达成了关于“个人债务”的书面约定,但如果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不承认的情况下这种证明很难,也很不现实的;并且很多人在离婚时,为了达到多分财产的目的,想尽办法故意伪造债务,就算是之前有约定,债务人肯定也不会承认了,而债权人为了自己利益,为了更有利于债权的实现,也不会实事求是地承认是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3)在证明“第三人知道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得财产为各自所有”的问题上,债务纠纷发生后证明债权人知道夫妻双方实行约定财产制的事实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债权人坚决否认自己知道实情,要想证明债权人明知的主观想法对债务人的配偶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债务人的配偶想证明的是与自己利益完全对立、冲突的相对人的主观想法,这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综上所述,推定规则将举证责任强行分配给债务人的配偶是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也是极不合理的。
三、立法缺陷引发的实践问题
现代社会,夫妻财产关系日趋多元化,立法对举证责任规定的不足越发显现出来,导致在离婚案件中,出现了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难度大、举证难、取证难的问题。实践中举证难主要表现及原因如下:
1.受害人法律意识淡薄,怠于收集证据。正常情形下,夫妻双方因为感情融洽,相互信任,一般都不会想到离婚,对离婚时的债务分担问题缺乏危机感。并且中国的家庭现实是婚姻当事人一旦结婚,一切以“家”为主导,忽视了个体利益和保护意识。因此,在主观上不会保持警惕意识,在客观上也不会收集和保存一些证据,一旦夫妻关系恶化,另一方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否认应当承担的债务,甚至伪造债务,企图侵吞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受害方“举证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受害方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更为典型的是,很多受害人甚至在受到侵害之后,还不会意识到要收集相关证据,而是以道德观念认为事实本身如此就是最好的证明,无论跟谁理论,都是不会改变的事实,不需要书面证据。因而导致在一方或者债权人提起诉讼后,往往因无法向法庭提供有效的证据而导致败诉,承担不利后果,后悔晚矣。
2.夫妻一方因个人原因擅自举债,另一方举证困难。1993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规定:“下列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一方以个人财产清偿:(2)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资助与其没有抚养义务的亲朋所负的债务。(3)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从此条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夫妻一方因个人原因擅自举债,属于个人债务,不纳入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在实践中,尽管有司法解释为依据,却没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此规定对弱者的权利起不到根本保护的作用。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一般情形下,一方从事经营,另一方不参与或很少参与对方的生产经营活动,对对方的财产状况了解甚少,在主观上也不会意识到在貌似正常的家庭氛围背后存在夫妻财产纠纷的隐患,直到夫妻离婚时债务承担对自己不利,才恍然大悟,却已无能为力,只能迫于没有掌握证据得不到法院支持而承受不应承担的不利后果。因此,在债务纠纷出现时或离婚时要举证证明经营一方是“擅自举债”、且“用于个人需要”是很困难的事情。
3.对债权人是否和债务人约定为个人债务,也很难举证。随着夫妻独立性增强,在很多时候,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发生举债行为,仅仅是举债方的个人私事,另一方并不知情更无法控制,出现纠纷时,根本没办法证明他们约定为个人债务了。据统计,每年各地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离婚后财产纠纷案占很大的比例,而原告撤诉的占很大一部分。据法官分析,撤诉案件大多数是因为证据不足,拿不出证据,其权利就无法得到保护。所以,一旦发生纠纷,该项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还是夫妻个人债务一般很难认定,未参与举债一方也很难拿出证据证明债务人的借款为个人债务。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则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4.经营性债务难以举证。随着经济发展,夫妻双方或单方举债进行经营活动的情况大量增加。大多情况下,夫妻间参与经营的只是夫妻一方,另一方并不参加。而且,因经营所形成的债务,即便一方独自以其个人财产进行经营而且收入归己没有与家庭发生任何关联而形成债务,夫妻另一方一般很难举证所经营的资产不是夫妻共同财产,而且也没办法约束经营一方的经营行为和非经营行为。而根据《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未经营一方须承担举证责任,在未参加经营的情况下,却要承担举证经营财产不是夫妻共同财产且经营收入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违反了消极事实无法举证的原理,有失公平。
从以上对举证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实中的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是十分复杂的,简单地说由主张个人债务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或由主张共同债务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其实都是不科学的。总结起来,笔者认为:应该区分不同的情况分配举证责任,在以夫妻名义共同举债的情形下,要求主张是个人债务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若不能举证,则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在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的情况下,要尽量保护举债方配偶的利益,要求举债一方举证,否则就认定为举债人的个人债务。这样综合考量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才是比较合理的、公平的。
四、完善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的对策与建议
1.设立夫妻大额债务共同签字制度。在离婚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夫妻一方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对方财产的现象成为法院审理离婚案件中的难点,且这种现象在缺少法律规制的情形下越来越严重。
推定规则容易助长夫妻一方恶意举债的故意,容易引发债务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虚构债务的危机。此类债务纠纷大多发生在婚姻走到尽头之时,感情一旦不存在,夫妻间的财产争夺战就显得冷酷而残忍。{2}为了获取更多了利益,离婚的双方当事人常常不惜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欺骗法院和其配偶,从而达到其想要获取更多的财产、取得更多的非法利益的目的。为防止一方恶意举债而引发夫妻共同债务与夫妻个人债务之争,立法应当对夫妻单方大额举债行为进行规范。因此笔者建议立法规定:大额举债要经过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后由夫妻双方共同签字认可。否则,夫妻任何一方单独举债的,可以推定为其与债权人已约定为其个人债务,除非有证据证明该项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夫妻另一方事后予以追认的,也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一般而言,大额债务是应当排除在日常家事代理范围之外的。债权人作为善意交易人应持谨慎交易的态度,其在出借大额款项或进行大额交易时,应当征询债务人配偶的意见,否则可推定其认可该债务为个人债务。对债权人为追求高利贷利益而盲目借款或为追求高额利润而不谨慎交易的行为,其自身本来就存在过失,56917821ea81f73185836e9ecea8e47ad2f09ec7effa433def255738e4bb349b所以应承当风险。
2.完善离婚案件中夫妻债务处理的规则。
(1)废除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明确规定了夫妻共同债务推定制度。而这一推定规则在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同时,存在严重损害夫妻另一方的合法权益的可能性,并导致了当今诉讼欺诈现象的日益泛滥。而且,从理论上说,其一,“家”不是一个民事主体,夫妻个人举债即使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也不能说是“家”与债权人有债之关系。{3}家庭成员有其独立性,每个个体仍为私法上最基本的行为主体,毕竟个人责任自负是民法的基本原则。每个人得根据自身意思自我负责地形成其社会经济生活,此为私法自治的集中体现。人们在从事经济交易、进行社会往来时,关注更多的是交易对象自身的信誉和资质,而非其配偶如何、背景怎样。{4}其二,在交易之初,由于债权人拥有交易选择权,他完全可以通过让夫妻另一方对债务进行确认来规避这种交易风险。这种规避交易风险行为的成本,比诉讼中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强加给夫妻另一方所导致的反驳成本要小得多。{5}
我国法律规定离婚时分割财产的基本原则是适当照顾女方、子女以及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公平处理共同财产及债务。但司法实践中,往往是法律无法保护婚姻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无过错方以及子女的权益,反而为他们增加了不合理的债务负担。因此,应当废除夫妻共同债务推定制度。当然,废除该推定规则,可能会出现客观真实上系夫妻共同债务,但债权人因无法获得夫妻之间内部信息而举证不能,导致案件事实与客观真实不符。但我们可以通过立法和司法其他方面的途径加以补救,力求平衡婚姻关系双方及债权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各方的合法利益。
(2)充分运用法官的个人经验法则,灵活适用法律,平衡各方利益。目前“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己成为全国各地法院审理夫妻共同债务案件普遍适用的规则,在立法上还没有对其完善的情况下,法官应充分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对夫妻个人利益和债权人利益进行充分比较权衡,并灵活适用法律,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司法的公平与正义。
首先,应采用体系解释的方法对《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适用范围作限制性理解。体系解释也称逻辑解释、系统解释,是指将被解释的法律条文放在整部法律乃至整个法律体系中,联系此法条与其他法条的相互关系来解释法律。{6}其目的是为了全面、完整地把握立法精神和法律含义,防止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失却法律原意。《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是对现行婚姻法的解释,其应忠实于现行婚姻法,并限制在现行婚姻法的框架内,不能超出立法本意。其次,充分运用法官的个人经验法则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法官审理案件时,应在兼听双方当事人述辩的基础上,综合分析案件的事实和证据,利用自己的经验法则,选择适用法律规则,对具体案件作出合理公正的判断,这样的判决结果会更符合客观事实,更趋向于实质正义。最后,变通适用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的关键在于“日常家事代理范围内”,但因为婚姻法相关解释缺失对夫妻共同债务范围的规定,加之我国又没有对日常家事代理权作明确规定,法官若直接适用该制度易引起当事人的非议。对“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可采用两个判断标准:一是夫妻双方是否存在共同举债的合意,二是夫妻双方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7}尽管这两个标准表述不是很科学,但我国实务界在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时,此标准已居主流地位,可将之与日常家事代理联系起来分析,日常家事代理范围内的个人负债可推定为夫妻合意,认定为共同债务。而对于一些争议较大明显超出日常家事代理范围的巨额债务,则应从严审查,不可轻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3.明确夫妻个人债务与共同债务之争的举证责任。我国《民事诉讼法》确定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证据规则,使得很多情形下明知是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却无法维护自身的权益,给法院裁判及当事人利益都带来很多困扰。如前所述,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夫妻一方要举证证明另一方个人举债非夫妻共同债务难度极大,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情况下根本无法举证,依据法律规定却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终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按照我国的立法精神和立法目的以及社会的传统观念,法律侧重于惩罚婚姻的过错方,但事实上过错方往往是事先有所准备并刻意隐瞒其所作所为,甚至故意制造假象蒙蔽法院,蒙蔽配偶他方,其主动坦白过错的情形是很罕见的。正是由于无过错方在诉讼中的举证不能,使得本该胜诉的受害方往往难以提出有利证据得到法院的支持,亦使得法律保护无过错方合法权益的立法精神难以实现。因此,我国《婚姻法》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上应当确立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实行夫妻债务认定举证倒置规则,由夫妻参与举债一方当事人证明所举债务确实是夫妻共同决定,或确实是用于家庭共同生活需要的,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否则,按举债一方个人债务处理。这种举证规则比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在诉讼中将举证责任强加给夫妻另一方的成本要小得多,也更具有可操作性。
4.增补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在婚姻生活中,日常事务琐碎繁多,夫妻确有相互代理的需要,这种日常家事代理权是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推定,同时也符合婚姻当事人的本人利益,这一制度有利于维护简单民事交易的安全,方便日常生活。这一制度早己成为大陆法系国家通行的制度,英美法中也有相应的规定。《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虽然只是对夫妻互有日常家事代理权予以间接承认,这已经是对原有婚姻法理论的重大突破。{8}但直至今日日常家事代理权并没有得到立法上的明确规定,因此建议在婚姻法中引进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并且明确限定日常家庭事务的合理范围,这对于维护家庭生活的稳定和民事交易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范围应严格把握,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不宜扩大。完善我国的日常家事代理制度首先要将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权限和范围规定清楚。如史尚宽先生所说,“就家事之规模及其外部的生活样式”确定家事代理权的范围。因为“日常家务之范围,依各夫妻共同生活之情事及因为其行为之目的而有不同,由外部正确判定,甚为困难。然如依内部情事而定其范围,不独有害于第三人,结果反有碍夫妻共同生活之经营。”{9}即有了生活样式外观的日常家事代理权,可以类推适用表见代理的规定。
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权限和范围清楚之后,对于非属于日常家事代理事项的处分就应当征得夫妻双方的同意和确认。笔者认为应规定为:一方若设置不属于日常家事范围内的债务,须经另一方的同意和确认,否则应当视为个人债务,由举债方自行承担债务后果。但该债务负担若符合民法表见代理的外观而使债权人有理由相信的,不足以对抗债权人。
注释:
{1}丁巧仁.民商事案件裁判方法[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103.
{2}唐雨虹.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的缺陷及重构[J].法学论坛,2008(5):110.
{3}杨斯空.论我国法定财产制下的夫妻共同债务制度[J].法制与社会,2007(4)
{4}郑磊.王海栗.夫妻共同债务认定[J].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3)
{5}唐雨虹.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的缺陷及其重构[J].行政与法2008(7)
{6}曾宪义等.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G].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51.
{7}夏侩军主编.婚姻家庭审判实务与典型案例评析.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240.
{8}占清.夫妻债务制度研究.陈苇主编.家事法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59.
{9}史尚宽.亲属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18.
参考文献:
1.伍蓉玲(导师:梁立霞)离婚案件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研究.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11.1
(作者单位:伍蓉玲,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阮芳,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广州 510000)(责编:若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