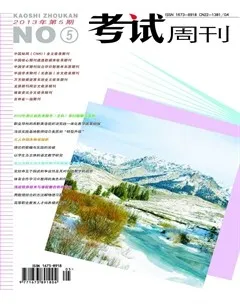谈《兰亭集序》的历史性和现代性
摘 要: 王羲之在永和九年,以会计内史的身份主持文人集会,以此为契机,留下了千古美文《兰亭集序》。文章高尚的思想和精辟的语言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对死亡的理解和思考,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对生的留恋,对美好生活的恋恋不舍和生死不能由命的、不能如愿的苦闷,在当时也是发人深省的,对功利高于一切、浮躁的现代社会,也具有很好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兰亭集序》 历史性 现代性
《兰亭集序》: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不管选择怎么样的生活方式,总会有两种体验:欣于所欲,快然自足;所之既倦,情随事迁。人在美好的时光中总会感到“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而在事过境迁之后,又不免感慨横生。生活中总有些美好的事物,让人产生生之留恋,但是人总是要死的,作者有两件痛事“向之所欣,已为陈迹;修短随化,终其于尽”,自然而然地提出了“死生亦大矣”的观点。“死生亦大矣”语出《庄子》,道是主宰万物,不随外物而变。东晋是名士流的时代,士大夫们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大谈玄理,不务实际,思想虚无,放荡不羁,及时行乐,蹉跎一生。后文“一生开死”“齐彭殇”出自庄子《齐物论》,原话是:“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王羲之反对清淡,尖锐地提出了“一死生为荒诞,齐彭殇为妄作”的观点。王羲之也想在“立功”上有所建树,因此一直颇想有所建树,施展济世安民的政治抱负。他曾诏拜右将军,积极地提出治国措施,如纳谏求贤、限制豪强等,但没有被采用,悲愤政治的黑暗之际,于永和十一年毅然辞。但论操守见识和议论口才,整个东晋时期没有几个人能够比得上王羲之,但王羲之终不能立于时代之外,道家怡养生年、顺其自然,清静无为、力求“守生”的思想及不务实际、一切达观,消极玩世的玄学清谈风气对王羲之也有或深或浅的影响。他也有些许出世思想,不愿意被人使唤。因此“功名成就,无一可言”。辞官之后王羲之跟浙东的一些朋友一起,结伴游山玩水,捉鹰钓鱼,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这和陶渊明有几分相似之处。
虽文章中也不乏“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低沉调子,但正是对死亡的悲观感慨和生的焦虑体现了五羲之对自古以来人的生存困境有关照。王羲之在这篇《兰亭集序》中所表现的生之焦虑源于对死亡意识和整个人类悲剧性命运的敏感,唐王勃的《滕王阁序》、宋苏轼的《赤壁赋》等都异曲同工地表现了生死这一人类难以回避的哲学命题。尤其是快节奏的今天,人沉浸于物质的追求中,似乎没有驻足看天、看地、看自己的时间。一个命题就出现了:人人都该生如夏花之绚烂吗?历史发展到今天,理想在实现中能否找到立足之地呢?王羲之的眼光之高远,胸怀之宽广在此处便得到了彰显,古往今来,这篇文章慰藉了无数空怀壮志、无处施展的仁人志士,可能以后会慰藉更多的生灵,使他们在死亡的恐惧中看到生的意义、在生的焦虑中看到生之美。生命是短暂的,但庆幸的是一生中还是有很多安康的晨昏,正如当代诗人邹荻帆在《秋歌》中所写:“秋天,什么也没有留下,只留下一个暖暖;留下一下暖暖,一切都留下了。”即使是今天这个时代,应该也不乏王羲之的知音,每一次读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总会讶于情感的惊人相似。短短几十行字,却代表了生死命题的深度和高度,穿越古今,可知遇见了不可知的未来人类生命的悲剧性。
《兰亭集序》超越了那个时代,即使在当代也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际价值。首先,其全文夹叙夹议、情与景浑然一体,结构严谨,语言自然洒脱,读来如信手拈来、酣畅淋漓。在文学式微的二十一世纪,它的确是一篇非常有价值的立意。当下的文章尤其是诗歌,诗人数不胜数,但缺乏好的诗歌,问题主要体现在语言和深层意味上。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富有文采又兼备情理,的确是当代文学文者可以潜心学习的一篇美文。其次,文章中所流露出的对生的焦虑和当代人的“若合一契”。虽是相隔一千多年,但生的焦虑似乎比魏晋时期有增无减,这便催生出更多关于生和死的思考,这样更多的读者便能在对文章的解读中,产生一种共鸣。人类的命运或许从一开始就是注定悲剧的,但王羲之在文章中对生死的陈述,揭示了生命源于死亡意识的一种悲怆的美丽。
王羲之关于生死的观点使生活在喧嚣和焦虑中的读者在共鸣中获得一种对生更深层的理解,同时,王羲之对二十一世纪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人来说也是精神的导师。王羲之超越了那个时代,在崇尚骈俪文风的魏晋,他以清新质朴、澄澈通透的笔调写出了《兰亭集序》;在玄学、清淡之风盛行之际,以对人的生存困景的关照和思考,实现了对儒家的反叛和对道家生死关的深化;王羲之超越了他自己,理想抱负得不到施展的时候,他远离庙堂,游山玩水,写字讣闻,饱经沧桑,且多困惑于矛盾的灵魂,终于在山水之间找到一丝恬静。绝禄退隐成就了他的传世美文——《兰亭集序》。他的旷达和超越,激励那些苦闷的焦虑的人去调节自己,发现自己,人不可以决定自己的生命的长度,但是可以决定生的深度。像王羲之这样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甘心情愿地对待一切人、一切事情,生命才会有意义。
参考文献:
[1]宗白华.论《世语》与晋人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