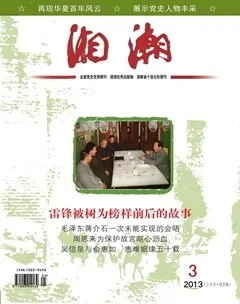毛泽东与新中国之三:万方乐奏
在毛主席纪念堂二楼大厅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这就是由著名画家刘宇一创作的《良宵》。画面上,毛泽东等共和国缔造者与各族代表欢聚在皓月明媚、宫灯高悬的中南海庭院中,或吟诗写字,或品茗倾谈,欢乐祥和的景象令人神往。
《良宵》描绘的正是1950年新中国第一个国庆节的情景。当时,共有159位少数民族代表和222名各民族文工团员应邀赴京参加国庆活动,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10月3日晚,少数民族文工团员在中南海怀仁堂表演了精彩的节目,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晚会。
为纪念这次晚会的盛况,毛泽东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词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第一首词作,他以领袖的气度和诗人的情怀,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团结的序曲。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下设的第三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由周恩来任组长。经过两个多月的辛苦工作,周恩来于8月22日将《共同纲领》草案初稿交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仔细阅读后,提出了一个关于民族问题的重大修改意见。
原来,草案初稿在结构上分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两大部分,具体纲领部分有解放全中国、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国防、外交侨务6个方面,并未把民族政策单列为一个方面,而是在条文上一般地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民族自治区。
毛泽东认为民族问题至关重要,有必要上升到国家结构形式的层面来考虑。他提出:要考虑到底是搞联邦,还是搞统一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看来恐怕还是不要搞联邦。
毛泽东关于民族问题的考虑有其历史和现实的依据。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对中国各民族的剥削和压迫,给各少数民族造成了极端贫困和伤害,也在中华各民族之间造成了很深的民族隔阂和民族矛盾。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问题获得了根本解决的可能,但彻底消除民族隔阂和矛盾,实现民族团结仍是十分艰巨的任务。而且,在西藏及新疆南部,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在支持所谓“独立”的分裂活动猖獗。
毛泽东清醒地看到: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而言,要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必须解决好民族问题。而要解决我们的民族问题,必须首先做出重要抉择。是学习苏联实行联邦制,还是走自己的路?
毛泽东就此征询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意见。李维汉经过深入研究,认为中国与苏联的国情不同,不宜实行联邦制,建议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自治地方制。他具体分析说:苏联少数民族人口与俄罗斯民族大体相等,而我国少数民族只占全国总人口的6%。苏联经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许多民族实际上已经分离为不同国家,因此不得不采取联邦制,作为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我国则不同,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平等联合进行革命,到平等联合建立统一的人民共和国,并没有经过民族分离,始终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完全同意李维汉的分析和建议,认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更有利于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完整统一。在对《共同纲领》草案的修改中,也相应地增加了“民族政策”一章的内容,并向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进行了解释。
9月21日至30日,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期间,各民族代表、各党派各团体代表就这一国家结构形式问题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商讨,确定在中国只能建立单一制的人民共和国。大会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
从这时开始,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就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本制度和基本国策确定下来。这对于后来在任何复杂情况下,都始终保持整个国家的完整统一和各民族的大团结,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
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幅毛泽东1950年6月的题词手迹——“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这是毛泽东当年送给各少数民族的一份礼物,而不远千里替毛泽东把这个礼物送到的,就是中央民族访问团。
1950年初,毛泽东提议组建中央民族访问团,深入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宣传新中国的民族政策,疏通民族关系。中央通过了这个提议。6月,第一个访问团——中央西南访问团刚刚组建,毛泽东就接见这个团的120名团员,并亲笔题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
此后的两年多时间,中央民族访问团分成数个分团,跋山涉水,分别到达西南、西北、中南等地,足迹几乎遍及全国所有少数民族地区。他们也把毛泽东的题词翻译成各种民族文字,带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还通过表演歌舞、放电影、办展览等多种活动,在感情上拉近与少数民族群众的距离。
在多数地方,中央民族访问团受到了当地各族群众的热烈欢迎。人们奔走相告:毛主席派亲人来看我们了。许多人是风餐露宿几天,从百里之外赶来,就是要看看毛主席派来的访问团,听听毛主席的代表说些什么。
解放初期,民族地区卫生设施还十分落后,瘟疫时有流行。毛泽东和党中央十分关注这种情况,卫生部先后向西南、西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40个卫生工作大队。1952年,一支中央民族卫生工作大队来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这里老百姓得病的很多,但他们治病的方式就是到庙里打卦。卫生大队很快“入乡随俗”,把医疗工作做进了喇嘛庙。据时任中央民族卫生工作大队大队长叶干运回忆说:“我们每到一地,就到喇嘛庙去拜访活佛。我们给他献哈达,然后说明来意,就是为老百姓看病治病,为群众谋福利。以后和活佛关系搞好了,一般老乡有病还是先到庙里打卦。一打卦,活佛就说,菩萨说了,你这个病要到民族医疗队去看,他们那里有好医生、好药。他们就信了,就到我们那去治病。病很快治好了。当地老百姓都传说一句话:“活佛的卦真灵,而毛主席派来的医生技术和药真好。”
解放初期,民族地区物资匮乏的情况也很严重。中央民族访问团带去了一些当地紧缺的药品、绸缎、布匹、食盐、茶叶、针线等物品,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极大欢迎。后来,在毛泽东的关心下,中央又派出多支专门的民族贸易工作队开赴边远地区,完全按照市价与少数民族群众进行交易,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消除了民族地区沿袭千年的不公平交易。
访问团、医疗队、民族贸易工作队,成了毛主席和共产党在民族地区的形象代言人。他们走到那里,就把歌声和欢乐带到那里;他们走到那里,哪里就掀起民族团结的高潮。
在北京学府林立的海淀区有一所特殊的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过去叫中央民族学院。说它特殊,一方面是学生大多来自少数民族,另一方面是多年来一直享受着特殊的待遇。自1951年6月成立以来,毛泽东曾10多次接见这所学校的毕业生。这令其他学校的学生羡慕不已。
解放初期,少数民族地区不仅经济、文化落后,而且人才不足,干部缺乏。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能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政策工作,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广大群众。”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11月通过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的试行方案》。中央民族学院一成立,就汇集了众多当时全国知名的一流学者,如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林耀华、翁独建等。在当时,中央民族学院的师资力量达到了全国高校的一流水平。
此后,又陆续建立了西北、西南、中南等9所民族学院,帮助各少数民族培养自己的政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连当时人数最少的赫哲族也有了自己的大学生。
一批批的少数民族学员,把知识和技术带回到自己的家乡。经过实践的锻炼和有针对性的重点培养,他们中很多人逐渐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发挥骨干作用,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改变少数民族地区落后面貌做出了重要贡献。
有一首歌在彝族地区被广为传唱:“哎……大雁大雁你慢慢飞,你是不是要飞到北京去,要是你见到毛主席,你就说,我们彝家实行了民主改革,分到了土地和牛羊。”
解放后,一些民族地区还保留着过去的旧制度,如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就保留了奴隶制,四川藏区和西藏则保留了农奴制。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民族上层的自治,而是自治民族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治。因此通过民主改革解放劳苦大众,是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必由之路。
1955年12月,四川彝族、藏族地区相继发生了武装叛乱。事件发生后,当地一些干部对是否继续执行和平改革政策产生了疑问。这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56年7月,中央统战部邀请四川省有关负责人和部分藏族、彝族代表到北京,专门研究四川的民主改革问题。会议由李维汉主持。会上,对民主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大家畅所欲言,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7月22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听取李维汉汇报有关情况。在如何处理藏族地区寺庙财产问题上,有人主张应予没收,有人不同意,认为藏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寺庙财产不能没收。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州长、藏族干部天宝持后一种意见。
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天宝的意见,他说:我们还有一条,就是少数民族自己管自己的事。所以天宝一说,我们就听他的,把我们都压倒了。
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意愿,慎重稳进,是毛泽东在民族地区社会改革问题上始终坚持的原则。颐年堂会议后,和平改革方针得到很好的贯彻,四川藏、彝地区的民主改革顺利完成。1959年西藏也进行了民主改革,农奴翻身获得解放。
今天,很多藏族老百姓的家里还挂着毛泽东的画像。在他们的心目中,毛泽东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而毛泽东当年并没有把自己和汉族看作是藏族的大救星,他主张平等对待少数民族。
建国初期,在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过程中,部分干部、群众表露出某些大汉族主义的倾向,一些地方出现汉族干部包办代替,不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和经济权益等现象。毛泽东对此采取了零容忍的态度,1952年,在中央转发甘肃定西地委关于执行民族政策的检查报告上批示:希望每个有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地区的县委及地委,于切实检查所属区乡的工作情况后向中央写一个报告。此后,全国各地开展了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大检查,主动查找不足,切实改进民族工作。
1955年3月9日,国务院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就在同一天,毛泽东亲自拜访来京的班禅时诚恳地说:“过去我同张经武、范明都谈过,要他们对我们的干部讲,我们进藏是诚心诚意帮助的,不是代替的,而且帮助还要帮助得好,不能让人家不舒服。同时我也对他们讲,要以这两条来考验我们的干部。虽然这样,但是你们也应该对他们进行帮助,随时提出意见,不对的要改正,如果不改正,你们可以提出意见,把他们调回来。”毛泽东的这番话令班禅十分意外,也十分感动。
在毛泽东的努力下,大汉族主义趋于消解,各民族之间联系密切了,情感沟通了,原来有积怨的多数取得和解,原来分割对立的逐渐走向团结合作,本来是团结的则更加亲密了。
新疆焉耆是一个回族聚居的地方,他们的祖先在150多年前从黄土高原西迁进入新疆,在这里扎下了根,繁衍生息。1954年3月15日,是焉耆回族难忘的一个日子。这一天县级自治区成立了,回族在焉耆当家作主了!
到1954年底,新疆先后成立了6个自治县,5个自治州。凡有聚居地、符合建立自治地方的民族都实行了区域自治,建立省级自治区的条件业已成熟。
然而,对于世居13个民族的新疆来说,确定自治区的名称是一个难题。1955年初,赛福鼎和包尔汉在北京开会,习仲勋约见他们,对他们说:“毛主席要我征求你们两位的意见,将来新疆叫新疆自治区如何?”赛福鼎对毛主席如此重视他们的意见非常高兴,于是开诚布公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自治不是给山川、河流的,而是给某个民族的。所以,它叫‘民族区域自治’,因此,‘新疆自治区’这个名称不太合适。”习仲勋当场表示说:“好,我向毛主席报告你的意见。”过了两天,习仲勋又约见赛福鼎和包尔汉,告诉他们说:“毛主席同意赛福鼎的意见,应该叫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毛泽东希望维吾尔族在新疆像汉族在全国帮助少数民族一样,照顾区域内的其他民族,通过自治区的建立,发展新疆各民族的团结合作。
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揭开了新疆历史新的一页。此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相继宣告成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自治区,成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改天换地、建设美好家园的全新起点。
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一直牵动着毛泽东的心。1952年,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说:“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后来又多次重申:“我们要诚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在和平解放前,西藏没有一条正规的公路。物资的运输非常困难。进藏之初,毛泽东就发出了“一面进军,一面建设”的号召,康藏、青藏公路由此开始投入建设。经过部队和筑路工人两年多的艰苦施工,1952年11月,将公路从西康的雅安修到了西藏的昌都。在举行通车典礼时,毛泽东亲笔为筑路人员题词:“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修路。”这极大地鼓舞了参加筑路的部队和工人。1953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康藏公路昌都至拉萨段的选线方案后,亲自批准采用南线方案,并要求1954年通车拉萨,可见毛泽东对西藏经济建设的高度关怀。
1954年12月25日,举世闻名的康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宣告结束。为了修筑这两条公路,11万军民付出了无比艰辛的劳动,3000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毛泽东的题词表明了筑路的意义所在:“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
两路通车后,各种生产、生活物资被源源不断地送到西藏,而西藏丰富的土产、特产和畜产品,也可以销往内地。50多年过去了,青藏铁路已经通车,但这两条公路仍然是西藏的运输大动脉。
在毛泽东的关怀下,中央政府对民族地区的建设给予了资金、技术、人力等方面的大力支援。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开始改变,逐步在缩小与先进地区的差距,走向共同繁荣。
今天,我国民族事业再次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各族同胞团结一心,掀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新高潮。民族地区的面貌也发生了可喜的巨大变化。实践充分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适合中国国情,得到各民族衷心拥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无比的优越性。
(压题照片:1959年10月12日,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参加国庆10周年典礼的各少数民族观礼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