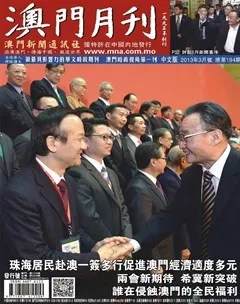無為而治與有為而治

在中國,自古以來在有關國家治理上,有兩種思路,一是無為而治,二是有為而治。撇開“有為”和“無為”二詞的褒貶涵義,我們大體上可以將建國後的前三十年看成是有為而治,而後三十年則是無為而治。兩種治理模式利弊如何,世人不難評判。
前三十年的“有為而治”表現為兩點:一是不斷折騰。一個又一個的運動,鎮反、土改、三反五反、工商業資本主義改造、大躍進、人民公社、反右、四清、文革,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二是包攬一切,指揮一切,以為全知全能,無所不能,樣樣要管。在社會經濟領域,政府之手無處不在,計劃經濟統治一切,經濟生產,物資分配,民眾生活,都被通管起來,連農民種什麼莊稼,何時播種,密植深耕與否,都是行政命令,不懂蠻幹,最後弄得國弊民窮,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
文革結束後,撥亂反正,與民休養生息,放寬搞活。從鄧小平的“不搞運動”、“不爭論”,到胡錦濤的“不折騰”,一系列的改革開放,實際上都體現了一種從國家無所不包、指揮一切的“有為而治”的體制,向逐漸減少國家對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干預,逐漸減少計劃經濟的比重,國退民進,放寬社會經濟自由,聽任市場經濟發展的“無為而治”的治國思路。經過三十年,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國力日益強盛。今日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全球經濟和國際事務中已經舉足輕重。
伴隨著經濟發展,近年來,貧富懸殊、貪污腐化、行賄受賄、群體性騷動、食品安全、勞工權益等問題愈演愈烈,維穩行動愈來愈頻繁,其代價也愈來愈高。社會矛盾有日積月累、日益加重之勢,既危及社會安定,亦危及中共自身的執政地位。
鑒於目前中國出現的問題,社會上出現一種懷舊思潮,即試圖重回過去的治國思路,以原有的舊式武器和旗幟,來解決今日中國的問題。
應當看到,中國經濟在三十年中的迅速增長,得益於國家在經濟領域的無為而治、放寬搞活、國退民進,當然中國今日社會矛盾的積累和社會亂象的出現也與公權力不作為或少作為有關。
所以問題並不在於政府是否應當有所為或有所不為,而在於應當正確界定政府作為和不作為的領域。社會的經濟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應當是市場的、私人的和競爭的領域,是國家無為而治的領域。至於國家有所作為的領域,只應當也必須是在政治法律上確保公正公平,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和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
顯然,那種認為因為“不折騰”、“不搞政治運動”,就應當除了被動維穩而一律放任不管的認識是有問題的,但是那種試圖重走國家干預一切老路的主張,卻並非是一種更好的選擇。
導致中國今日社會矛盾積累的深層原因,無疑有民主和法制建設滯後的因素。但是今日中國社會的許多社會亂象既沒有或較少出現在傳統的專制社會,也沒有或較少出現在西方民主國家中,這表明,政治體制改革固然可以減少或消除今日的許多社會弊端,但這並不意味著在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情況下,就不能有所作為。
對於暴力拆遷、農民工工資拖欠、勞工權益、食品安全等引發群體性騷動和群眾不滿的問題,為此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和強化執法,保護公民權益,保證食品安全,並不涉及根本的政治體制,完全可以也應當有所作為。
所以,我們在肯定三十多年來改革開放路線和在社會經濟生活領域放寬自由,減少干預的治理模式的同時,也應當看到迄今公權力在確保公正公平,保護公民權益和市場經濟秩序方面,還有很大的不足,還有很大的可以作為的空間。私權和公權應當有不同的領域。我們不能一看到現在存在的諸多問題,就簡單地認為無為而治是錯誤的,就盼望回到公權干預一切的舊模式。也不能因為放寬自由,搞活經濟,而放棄公權的應有職責,在該作為的領域無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