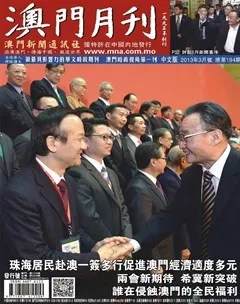让梦想飞翔




現代人生活忙碌,人們都被生活壓力追趕著步伐,每跨出一步都在喘息。澳門人面對經濟發展如巨浪般湧來的勢頭,從前純樸的生活文化都消失了嗎?近年來澳門“物慾”風行,尤其是年輕一代的追求,真的那麼一面倒嗎?
正當我對生活的意義感到迷惘的時候,我遇到了她,她帶我走進她的生活,感受都市人在璀璨繽紛的霓虹燈背後,還有一種柔和清新的恬靜。
她的名字叫佩兒,朋友逗趣地叫她“珍珠”。她個子嬌小玲瓏,披著一頭天然棕色的直髮,這是我對她最深刻的印象。看見我有點疑惑的眼神,她幽默地說:“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人。”
她散發出一種氣質,起源與她對我說起的童年。我知道這氣質來自於她從小對藝術的執著,對夢想的追求。
佩兒第一次對樂器感興趣,是在看了香港兒童節目《閃電傳真機》之後。節目中介紹了鮮為人知的樂器——非洲鼓,從此,玩非洲鼓便成了她的夢想。“非洲鼓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麼呢?”我問。她臉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答道:“讓人感到很自由自在,活蹦亂跳地拍打那個漂亮的鼓,邊打邊大叫大笑,像野人一樣快活,無拘無束。”聽了她的描述,我也很想立刻試玩非洲鼓,緩解這城市日積月累的悶氣。
佩兒與她喜愛的非洲鼓
在草根家庭長大的她,並不是像別家小孩那樣,三、四歲便有機會學習樂器。父母親都是工人,沒有培養兒女發展興趣的意識。佩兒從鋼琴開始接觸樂器,那時已在念高二。面對即將畢業和升大學的壓力,她絲毫不覺得抽空練琴是負擔,反而認為彈鋼琴是減輕學習壓力的好方法。音樂,對她來說是一種休息,讓她的頭腦更清晰。然而,在不懈的努力下,也會遇到瓶頸。嬌小玲瓏的她,擁有一雙小小的巧手,而正因為手指小巧,即使她使勁撐開拇指和小指,都不能彈奏音域較廣的曲子。對她來說,擋在前路的是無法改變的“身體不足”。她氣餒了,以為成為快樂來源的藝術生活將要破滅。
就在這時候,她遇到一位良師。她認為是僥倖,在我看來,更是她的信念抓住了希望。這位教會裡的良師知道她要放棄,由衷地告訴她:“如果你要放棄是因為這個理由,我會很心痛。”老師伸開手掌,貼在她的手掌上,她驚訝地發現,眼前這位她欣賞、敬重的老師,手指竟然和她一樣短。她深深地被打動,決定更用心、更勤奮地練琴。
一次偶然的機遇使佩兒參加了她人生第一次鋼琴比賽。靦腆、內向的她,以前從不敢在別人面前彈琴,這可是眾人炯炯目光下的鋼琴比賽。爲了克服自己的弱點,她竟然挑選了一首從來不敢彈的複雜曲子。佩兒事後回憶,這是一場關乎自己會否從此一蹶不振的比賽。“演奏過程是有遺憾的”,這遺憾使她離開賽場躲了起來不願面對觀眾。結果揭曉後,朋友們焦急地到處找她,因為,她獲得了第一屆亞洲鋼琴公開比賽兒童鋼琴曲集的冠軍。她喜極而泣。“遺憾”使她戰勝了弱點,而她,也戰勝了這個“遺憾”。
自鋼琴比賽之後,佩兒更瞭解自己的不足,她認為過去只是想把旋律演奏得盡善盡美,卻因為投入的感情薄弱,彈出的樂曲缺乏生命。在一出名為《一屋寶貝》的戲劇裡,她被故事和人物的情感所感動,亦從中得到啟發:希望從劇場裡調節感情的濃度,與音樂融合在一起。
她進入澳門演藝學院學習戲劇,原本有點缺乏自信的她,看見班內同學都有表演戲劇的經驗,更覺得尷尬不已。一年下來,她克服了很多心理障礙,在人前說話、表現,已沒有多大困難。但依然與其他人有一定的差距。校長也感到困惑,他對佩兒說:你的進步有目共睹,但你進步之後,才達到別人的起點。佩兒曾經感到很沮喪
學習戲劇的“一屋寶貝”
“這麼有挫敗感,為甚麼你還能堅持呢?"我追問。她毫不猶疑地說:“因為熱愛。平時上班的同事雖然時常見面,但各有各的生活追求而未必有共同目標。然而,在排戲的過程中,大家再辛苦,也會互相扶持,即使練習得手腳酸痛,也是快樂的磨練。我熱愛這種精神。”她還與我分享了自己的心得:劇場帶來的那份感動,要化為行動,得益才屬於自己的,繼而才能感染他人。
很多人在輝煌的成就下,並不懂得名利以外的真正快樂。佩兒卻不然,縱然她在劇場裡沒有顯赫的成就,但她已經完完全全融入演藝的快樂之中。而且值得快樂的並不止於此。當佩兒接觸了更多從事藝術的人士以後,得知澳門文化中心開辦“藝術‘身’體驗”工作坊,就毅然報名參加了非洲鼓課程。她從前沒有體驗過的夢想成真的時刻,終於來臨了。
她笑著告訴我,原來非洲鼓也有固定的節拍,不是小時候想像的那樣胡亂拍打就行了。初學時,她以為自己有樂理底子,可以學得比較好。她把所有節拍在腦中化成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的組合,怎料效果不盡人意,比起其他人來就更不理想。來自墨西哥的老師Raul Saldana告訴她,非洲鼓的節拍,只要“聽”,就能感受到。她恍然大悟,她當初喜歡非洲鼓,不就是因為它自由嗎?後來怎麼會被所謂的樂理知識束縛了自由的翅膀呢?有一次,老師知道她學過鋼琴,請她來試彈。可是她長期以來接受的教育和訓練,養成了一定要看著樂譜彈奏樂曲的習慣,離開了譜子,兒歌也彈不出來,竟然釀成了冷場。可老師一抬手隨便就能奏出輕快的小調。她深深地體會到,西方的教育從來沒有那種規範的框架,連彈琴也可以不看譜,把自己整個靈魂都融化在旋律中。由此她對東西方的方化差異有了更深的瞭解。原來,想把自己的文化生搬硬套到別人的文化裡,是不可行的。
透過非洲鼓作媒介,佩兒終於把豐富的感情釋放出來。老師在澳門居住了一段時間,察覺到中國的孩子會刻意收斂自己的情感,無法自然流露。他在學生面前演繹兩個不同的非洲鼓表演者,一個節拍十分規範,但沒有投放感情;另一個則開懷地唱歌跳舞,雖然節拍並不那麼緊湊。她回憶說:“效果顯然易見,後者讓你體驗整個表演過程,使人產生共鳴。”
除了傳授非洲鼓的技巧,老師還把很多人生閱歷教授給學生。她說: “其實中國的孩子,並不是一出生就遺傳保守的特質,孩童是很率直的。”曾經有個澳門孩子跟老師學唱歌,有一次試玩那讓人情緒奔放的非洲鼓,結果盡興之時難以控制自己,直想把頭往牆上撞。老師們立即上前阻止。孩子說他打鼓打得很亢奮,感到只有把頭撞在牆上才能讓自己冷靜下來。可見人的情感並不是天生收斂的。老師說,東方人應該懂得釋放自己的感情,展現自己的情緒;西方人則需要適度收起自己的情感,控制自己的行為。藝術是抒發感情的有效途徑,不僅彈琴如此,各項藝術活動都是如此。
佩兒回憶起最初學習鋼琴,以為學習是追求技巧,以為練好《蕭邦圓舞曲》就會快樂,現在發現,其實遠不如反樸歸真,彈一首民歌或流行曲那麼快樂。快樂就在於,不是為學而學,而是為喜愛而學。她的追求不會隨著非洲鼓課程的結束而結束,這個結束只是另一個起點。她的夢想飛得更遠:學習書法、國畫、小提琴、拉丁舞、街舞、形體、視唱……藝術領域不是一個一個孤立存在的,它們可以互相影響、互相包容、互相滲透以至相映成輝。即使不是在每個領域裡都很傑出,但她確實活在藝術夢想裡,活出了自己的光彩。
總有那麼一群人,在為追尋夢想而不懈努力。有時不被理解,人們認為他們在浪費時間,在做白日夢。但是有夢想的人,心思總是縝密的,他們從獨特的角度看到世界的美好,享受著生活裡獨特的快樂。佩兒告訴我:“我不介意在追夢的過程中,付出多少時間、多少金錢,多少精力,因為除了吃喝、穿衣、睡覺以外,我還有不一樣的生活。”為了進一步瞭解東方與西方文化藝術的不同風格,佩兒決定前往埃及體驗。她說,雖然是一時衝動,但藝術創作本來靠的就是衝動。
我們期待著她滿載而歸。
(作者是澳門城市大學文化產業管理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