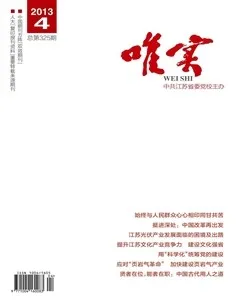挺进深处:中国改革再出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改革再次成为时代强音。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后即南巡深圳、珠海、顺德等中国改革前沿地区,并发表关于推动中国改革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启动新一轮改革的顶层意志;李克强总理在“两会”后的记者见面会上首次阐述关于改革红利的内涵,并表示虽然改革中要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改革必须推进,没有退路,显示了国家推动改革的高层决心;同样,在今年的“两会”上,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得到高票通过,凸显了新一轮改革政府带头的强烈信号。纵观上述重要讲话、重要判断或重要方案不难看出,从执政党到国家权力机关,从国家领导人到社会公众,对推动中国改革拥有了坚定的共识,对改革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挑战也做好了精神准备。毫无疑问,中国改革往前走的大环境已经形成,但同时也要看到,改革之路一定充满荆棘。挺进深处,知难而进!新一轮中国改革再出发,只有前路没有退路。
改革“窗口期”再难也要抓住
“改革必须抓住‘窗口’期,并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新一届党中央和中央政府高扬改革旗帜,近段时间以来,连续释放出深化改革的积极信号。舆论普遍认为,深化改革是当前和未来能否“全面把握机遇”,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关键。
过去10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奇迹”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但与此同时,一些矛盾和制约因素也日益凸显——我国的GDP考核让经济发展付出资源、环境代价,经济结构不合理矛盾凸显;收入分配不公,区域、城乡、行业间贫富差距过大,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官员腐败问题突出。面对现实困局,党的十八大报告给出了切实改革方向。“改革之箭”已在弦上,新一轮改革“时间窗口期”已全面打开。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就是与危机赛跑”,绝不可贻误时机。
面对执政风险,执政党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在深化改革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全党的理论创新与理论武装能力、文化创新与思想引领能力、利益整合与社会凝聚能力、党风廉政与自身净化能力、执掌政权与巩固国防能力、国际交往和世界影响能力、危机处理和稳定社会能力。
改革共识汇聚改革动力
笔者主持的一项涉及5万人的大型网络问卷调查显示,有37.50%的人认为“改革难了”,有30.74%的人认为“改革慢了”,有26.84%的人认为“改革少了”。很多人真切地盼望改革,认为改革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看到希望和有幸福感。
企业家群体也迫切期待深化改革的又一个春天。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知名民企董事长谈及改革紧迫感、述及经营企业时的苦水,几次唏嘘不已。“不改革不行了,民营企业5si2JC2rnfStBjWXyJjbMsJADrYxbC96SY5ztazWeYc=在资源配置、市场竞争、金融支持等方面长期不公,再不改,企业会继续出走国外、企业家会继续移民,因为有一种不安全感。”
基层改革者更是期待深化改革脚步不要停歇。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以政治文明为抓手,试点“还权于民”的改革。区委书记李南沉与笔者细谈“殷都试验”和为什么要改革,原定一小时的采访延续五个多小时,直到凌晨近两点,现场采访记录达六万多字。
河南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村是全国农村城镇化改革的“明星村”,63岁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是十八大代表,他虽患有严重哮喘病,但谈到农村改革问题时,忘记了自己是病人,来回踱步,高声大嗓地说:“有的地方城镇化其实就是土地城镇化,农民没有市民化,农民工就医看病、住房改善、子女上学等问题在城市里被边缘化。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城乡二元差距越来越大。我有生之年的理想是,把西辛庄建成中国第一个村级市,让农民在家城镇化。”
改革亟需冲破四大阻力
一些地方改革久议不决,一些部门改革决而难行,一些领域改革行而难破,新一轮改革阻力重重,集中表现出四大阻力:
“负思潮”阻力,即一些极端社会思潮在意识形态层面严重影响改革方向。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分析,许多国家的改革机遇都因被极端社会思潮左右而丢失,中国现在主要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四种社会思潮。“历史虚无主义否定我们党领导人民改革建设的历史;新自由主义要求对现有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狭隘民族主义以爱国的名义,煽动民族仇恨;民粹主义以代表底层民众自居,仇官仇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王德培说:“这些思潮都企图裹挟民意,影响决策。如不加以有效引导和应对,对改革大局非常不利。”
“伪改革”阻力,即一些政府部门借改革之名进行部门私利整合,或因消极执行改革政策导致一些领域的改革改而无效、改而效微。
“一些‘伪改革’表现在改革的不彻底性。”不少人士认为,大部门制改革到了地方政府这一层面,不少部门只是简单合并,领导职位不减反增,人员都没减少。一些“伪改革”以加强监管之名,审批不减反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说,一些部门在审查规模、价格等多个环节强化了审批权,中间多了不少“收钱”环节。“伪改革”还表现在政府减少审批,行业协会增加审批。某太阳能企业董事长举例说:“审批在工信部确实减少了,但在行业协会却增加了。例如,中国节能协会审批一个节能产品认证就要三四万元,而且每年都收,企业负担很重。”
“不改革”阻力,即与政府权力关系密切的既得利益群体,担心改革触动现有利益格局,不愿改革也不敢改革。
一些学者反映,既得利益群体不愿改革,因为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有自由进出的“旋转门”,有权力寻租的市场,有高收入的保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说,收入分配改革久久难以推进,主要是既得利益群体反对。
“怕改革”阻力,即一些领导干部担心改革风险大、难度大,因自身能力不足,怕失权、失稳,宁可消极观望,维持现状。
江苏省昆山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宣炳隆谈及改革创新体会时说,最怕的不是改革本身,而是怕领导不表态、不同意。四川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从2010年开始探索乡财改革,在网上公开包括每一笔接待费在内的乡级所有财务,网民热议为“中国第一个全裸乡政府”,认为是防止公款吃喝和基层腐败的有益探索。一年多来,因政务公开透明,这里的干群关系得到改善。然而,有的“怕改革”者却视其为另类,不予支持。
改革成败决定执政安危
一项大型网络问卷调查显示,高达89.02%的受访者认为,深化改革对于抓住战略机遇期“至关重要”和“比较重要”。显然,改革成败取决于执政党深化改革的步伐与方向,决定国家发展机遇的有与无。
坚持改革,事关发展机遇。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认为,抓改革也是抓机遇,未来10年能不能抓住战略机遇期,就看改革彻不彻底、坚不坚决。如果不能像小平同志当年那样有勇气,机遇期不仅没有,还有可能被逆转。
坚持改革,事关民心向背。一些干部说,深化改革就是执政党得民心的头等大事,执政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权力应该向人民感恩,人民分享到了改革成果,自然会向党和政府感恩,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坚持改革,事关执政安全。中国共产党肩负任务的艰巨性、繁重性、复杂性世所罕见。一些专家学者分析说,纵观世界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修修补补,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当前,面对“躲不开、绕不过”的体制机制障碍,如果消极应对,将问题击鼓传花,固然可能稳定一时,但“危机”就可能跑在“改革”前面,矛盾更多、危险更大,可能丧失发展机遇,甚至落入“转型期陷阱”,严重影响执政安全。
只有不断深化改革,执政党才能引领并攻克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难关,才能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有效化解执政风险。
抓住行政体制改革“牛鼻子”
今年“两会”上,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受到了各方高度关注,从国务院自身改起,这体现了新一届政府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的决心。显然,写入十八大报告的行政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文化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牵引和杠杆作用,是名副其实的“牛鼻子”。当前,社会对改革的观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领域改革的作为和成效。
“新时期新阶段,按照十八大精神要求,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对我国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深入推动科学发展、系统化解社会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一些专家学者、党政干部、企业界人士及群众代表认为,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行政体制改革就是政府在让自己的利、削自己的权。
“在未来3-5年内,要紧紧抓住这个‘牛鼻子’,简政放权,让利共治,在服务型、法治型、廉洁型政府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社会对政府改革成果充满期待。
校准政府三大角色定位
现在,社会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之一,就是政府边界不清而导致的乱作为,对政府自身改革呼声很高。
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等学者认为,未来3-5年,各级政府必须按照十八大报告中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具体要求,校准角色定位,在服务型、法治型、廉洁型政府建设上有新的突破,构建政府与市场、社会、企业之间的共治新型关系。“刚刚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朝着这个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服务型政府建设突出“公共”角色。服务型政府建设要紧扣“公共”本质,把为公共利益服务作为各级政府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资源配置和政府机构等方面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并且实施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公共服务体系,强化对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考核导向。
法治型政府建设彰显“护法”角色。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主抓行政体制改革的区委副书记刘光大说:“我理解法治政府建设要多依靠以下三种力量倒逼:一是行政问责硬起来,二是‘民告官’多起来,三是违法成本高起来。”现在全国各地“民告官”案件的数量与政府违法行为的现状严重不符。东南大学研究行政法学的副教授顾大松说:“这个局面要迅速扭转过来,创造条件让群众敢于状告政府违法行为。”
廉洁型政府建设塑造“清廉”角色。“一要求,二要吃,三要送。”一些企业家这样描述他们与一些政府部门打交道时的无奈。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说,政府部门寻租的确呈蔓延态势,这严重背离了廉洁政府建设方向,遏制这个势头,还政府以清廉面孔,“就是要尽快分权、制权、督权,建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监督机制,让寻租行为无所遁形”。
“厘清边界,才能有好定位、好角色。”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长陈家泽说,政府“天字第一号”的事情就是要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虽然很难划出具体红线,但守住两点就会心中有数:一是政府的行为到什么地方就能停止下来,这是一个简单的分水岭;二是凡是市场和社会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就不要去碰。
简政放权让利“剑指”寻租
自2001年以来,国务院已先后6批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9.3%;全国省级政府也取消和调整了3.7万余项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8.2%,简政放权取得一定成效。但大家普遍认为,如今审批领域的问题还是很突出,其异化和寻租程度依然严重。
一家国有大型投资集团的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感慨地说:“我们在香港上市了多家公司,我根本不知道是谁批的;而在国内上市了几家公司后,我连收件员、预审员是谁都知道,这就是繁琐审批产生的‘威力’。”某央企地方分公司负责人介绍说:“矿权的受理和资源开发就存在部门审批冲突,国土部门管矿权,发改委管项目,于是造成拿到矿权的拿不到项目许可,拿到项目许可的拿不到矿权,这种矛盾很常见。”显然,行政审批、监管方式已到了必须“彻底改、改彻底”的关口。
把大部门制改革与行政审批改革串联进行,不给职能交叉打架留空间。“审批制度改革要做到‘应减必减、应转必转、应放必放’,就必须从部门林立和程序繁琐上下功夫。”一些政府干部和专家学者建议,以大部门制改革和行政审批改革为核心的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必须遵行简政放权、让利共治原则,向深层次推进。
切断政府部门隐性审批利益链,纠正部分行业组织以“二政府”方式存在。某企业家说,现在一些部门名义上减少审批,但为了“创收”,却千方百计变相收费。“一套程序走下来,弄得企业身心疲惫,建议在下一步改革过程中,政府应该重点考虑怎么放权让利。”
还权于民、还事于社会,通过简政放权让利,实现政府与社会、市场协同共治。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奇说,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要有“社会”,政府事权该交由社会的交给社会,该交由市场的交给市场,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互相制衡、互相服务的新格局。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成立了囊括17个行业、群体的“殷都诚信联盟协会”,自我监督,市场环境立即有大的改观。
顶层推动方能攻坚克难
五年前,中央发布《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的纲领性文件,时至今日,相关改革卓有成效,但与社会期待仍存差距。部分改革试点地区由于是单兵突破,一些行政体制改革已经碰到了难题:
一是基层改得越快,越凸显上下不对接问题。某中部省份的一个市因为实施大部门制改革、整并机构,被上级部门认为是未设专门机构、对条线工作不重视,而被考核扣分;二是一些实施行政体制改革的部门或地方,“人往哪里去”成为一个突出难题,大大影响到了主要领导抓改革的信心和决心;三是有的改革仅停留在试点阶段,还有的试点要看“一把手”脸色。
行政体制改革现状折射了整个改革的现实,即:一方面,不少地方和部门都强调改革创新,各种各样的改革尝试似乎从未停止过;另一方面,人们似乎对改革还有诸多不满意,原因在于改革存在碎片化或变形的问题,损害了改革的权威。
汪玉凯、郭万达等人建议:“鉴于行政体制改革的复杂程度,遵循渐进的改革原则无疑是必要的,但要有宏观规划,给社会以明确的预期。在具体操作方案上要与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内的改革打通关节、合并事项、相互借力、整体推进。”“抓改革就是抓机遇。”迟福林、高尚全等相关人士认为,未来5-10年,我国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释放“改革红利”是关键。
十八大后,中央已经明确提出要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具体改革还要给出时间表和线路图。这些表述都直接回应了社会对改革的热切期待,无疑为中国改革再出发奏响突围号角,令人振奋。
(作者系新华社江苏分社常务副总编,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戴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