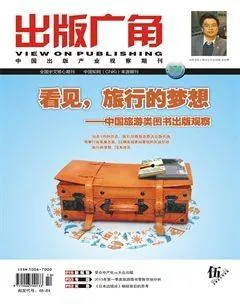民国“边缘报刊”的发掘、利用与研究
民国报刊是研究民国历史的珍贵资料库,离开这个巨大而又丰富的原始资料库,民国历史的研究不可想象。
民国报刊是研究民国历史的珍贵资料库,离开这个巨大而又丰富的原始资料库,民国历史的研究不可想象。研究民国时期的文学(1917—1949)同样如此。随着民国文学研究历史化、古典化成为研究者的一致诉求,如何更有效地利用民国报刊这个丰富的资料库、如何更进一步深入民国报刊内部去打捞史料,成为摆在每一个文学研究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刘涛的《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一书 (以下简称《考信录》),提出“边缘报刊”的概念,从对民国“边缘报刊”的发掘与整理入手,挖掘出民国时期为数不少的重要作家的大量佚文,有力推动了民国文学研究的进展。他的研究再次揭示了民国报刊对于研究民国历史包括民国文学的重要价值,值得引起相关研究者重视。
刘涛提出“边缘报刊”概念,对于民国报刊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边缘”,是相对于“中心”“主流”而言。所谓“边缘报刊”,概而言之,指的是民国时期那些影响不大或处于地域、政治边缘的“小”刊物或文化类综合性期刊、专刊、与文学无关的报纸副刊、出版时间不长影响不大的报纸文学副刊等等。“边缘报刊”虽在含义上指的是“大报大刊”之外不为人所关注的“小报小刊”,但仔细分析,可看出作者所谓的“边缘”还包含有其他更丰富的涵义。
首先,刘涛所谓的“边缘报刊”指的是文学报刊之外的非文学性的文化类、政治类、宗教类、音乐类报纸与期刊以及综合性的大型文化期刊。作者研究专业为民国文学,对于文学这个中心来说,非文学类报刊大多不在此类研究者的研究视野之内,属于“边缘”。例如,本书所关注的《河南中华圣公会会刊》就是一份“边缘报刊”。该刊由河南中华圣公会编辑发行,是基督教教会刊物。这样一份教会刊物,所刊文章内容多为宣扬基督教教义,与文学几无任何关联,因此,对于民国文学研究者而言,它当然是一份“边缘刊物”。本书所涉及的其他刊物,如《家庭研究》专门研讨家庭问题,《世界展望》专门研究二战时期国际政治问题,《春之歌选》与《每月新歌选》刊登的大部分是歌词,其内容皆与文学无涉,对于民国文学研究者而言,也属“边缘报刊”。但就是在这些边缘报刊上,作者却有不同程度的收获,如在《家庭研究》上发现成仿吾创作的话剧《离婚》,这是现在发现的成仿吾创作的唯一一部话剧,对于成仿吾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在《世界展望》上发现穆时英的系列作品,这些作品可证明穆时英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而非汉奸。这些佚文,对研究穆时英抗战时期的思想状况与政治倾向,对重新评价穆时英,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当然自不待言。
民国时期还出现不少各类学校所办的校级刊物即“校刊”和“学报”,这些校刊和学报由于其内容的综合性与学术性,与文学关系不太密切,因此,文学研究者对此类刊物也鲜有关注。对于这类边缘刊物,如《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校半月刊》《光华附中半月刊》《光华年刊》《厦门大学学报》等,《考信录》也多有涉及。作者在《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校半月刊》上发现郑振铎的一篇重要演讲《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光华附中半月刊》与《光华年刊》上发现穆时英大学时期创作的系列作品,在福建长汀《厦门大学学报》上发现林庚研究新诗形式的重要论文《新诗形式的研究》,这些佚文的发现,为研究上述作家提供了相当有价值的史料。
由“中心”进入“边缘”,由文学报刊进入非文学的宗教、政治、文化报刊,说明作者的研究视野已经由文学而延展至宗教、政治、文化,这是一种典型的跨界或越界行为。《考信录》对非文学类的边缘报刊的关注与考察,以及由此考察所带来的丰硕成果,带给报刊研究者的有益启示是:在专业的报刊研究中,要学会转换思路,扩大研究视野,尽量超越专业设置所带来的知识阈限,这样才能完成对自我的丰富与超越,带来意外的成长与收获。
其次,“边缘报刊”之“边缘”还体现在刊物的政治背景上。民国时期的一些综合性文化期刊或文学报刊,有一部分有着国民党或汪伪政权的官方背景,属国民党或汪伪政权的官办刊物,这类刊物,作者命之为“灰色报刊”。这类刊物,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政治原因,淡出研究者视野,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研究,也属“边缘报刊”。例如作者所关注的《东南半月刊》《建国青年》及《文化先锋》周刊、《中央周刊》等刊物,属国民党官办刊物或有着国民党的官方背景。《东南半月刊》由国民党中宣部东南区战地宣传办事处主编,发行人为冯有真,出版地在安徽。这是一个时事政治刊物,主要内容为宣传抗日建国的大政方针。《建国青年》创刊于1946年3月,1947年12月终刊,先在重庆出版,后移至南京。该刊提倡政治革新,所刊文章多为宣传中国国民党的政治主张和理论,有一些抨击中国共产党的言论。《文化先锋》由李辰冬编辑,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文化先锋社发行,出版地为重庆。该刊有国民党的官方背景,上面刊登有一些污蔑共产党的文章。南京《中央周刊》也属此类灰色刊物,该刊为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创刊于1938年7月,中央周刊社编辑并发行。刊物文章大都是宣扬国民党政治主张,以三民主义为中心。
作者关注的另一类“灰色报刊”则有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背景,如《中大周刊》《中央导报》《新流》等。《中大周刊》是伪中央大学的校刊,伪国立中央大学编纂课编辑周刊。伪中央大学是伪国民政府为粉饰太平于1940年7月宣布成立的,隶属汪伪政府。《中央导报》周刊,原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机关刊物,汪精卫集团叛国后于1940年在南京将其复刊,直属汪伪国民党宣传部,内容侧重于宣传汪伪政府的政策,社长林柏生,总编辑华汉光。《新流》是汪伪时期南京另一个重要汉奸刊物。以上有着汪伪国民政府背景或汪伪政权的官办刊物,与国民党的官办刊物或有国民党官方背景的刊物一样,由于政治原因,很长一段时间,被人为遮蔽,或得不到客观历史的研究,同样属于“边缘报刊”。
刘增杰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综合考察》一文中曾指出一些期刊研究,往往或隐或显地受到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潜在影响,大部分国民党方面的期刊作为“反动刊物” 被有意从报刊目录中剔除了。他认为应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只有多元融汇,才能激活研究主体的生命意识和文学意识,保证史料研究健康发展。用偏狭的视野根本无法认识现实斗争环境的复杂性所带来的期刊存在的特殊性,也无法还原意蕴繁复的历史形态。” 对于此类政治上的边缘刊物,刘涛在坚持价值评断的基础上,能打破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束缚,从客观的历史角度,对其加以观照和研究,从中发掘出大量珍贵的史料。《考信录》对于所谓政治上“灰色报刊”的关注与研究,启示民国报刊研究者应加大对国民党官办刊物、有国民党官方背景的刊物以及汪伪政权和其他沦陷区日伪报刊的研究力度,进一步增强民国报刊研究的丰富性与历史性。
第三,“边缘”还指涉办刊地点的边缘。作者不但关注办刊地处于北京、上海、南京等大的区域中心城市的报刊,而且还关注办刊地处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缘地带的报刊。这些地方报刊,由于僻处一隅,得不到足够重视和研究,在它们上面反而容易发现一些有价值的史料。《考信录》关注的开封《河南中华圣公会会刊》就是这样一个颇有价值的“边缘刊物”。民国时期开封虽是河南省省会,但与北京、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相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处于全国的“边缘”地带。这样一份地方性的基督教教会刊物,很少有人关注,即使研究基督教的专业学者也鲜有人提及。而作为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刘涛,却从中发现老舍的一篇重要演讲,为研究老舍的基督教信仰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史料。《考信录》所涉及的另一重要刊物《厦门大学学报》的办刊地为福建长汀。《厦门大学学报》作为厦门大学的学术刊物,其办刊地应为厦门,怎么到了福建的长汀呢?这与抗战有关。由于抗日战争,厦门大学曾一度搬迁至福建长汀,故《厦门大学学报》的办刊地点也转移到该地。
民国时期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皆存在区域发展的严重不均衡性,这直接导致了名刊大刊多聚集于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广州、香港等。但是,与此种现象同时出现的则是:在一些二三线城市也有为数不少的“小报小刊”。到抗战时期,随着中国政治文化中心依次向武汉、长沙、重庆迁移,大批文化人内迁,一度使这些地方及昆明、桂林等地,皆成为一个个分散的文化中心,上述一线城市的名刊大刊皆向上述城市迁移。此外,在内陆其他一些三线或更低一级的边远城镇,也出现了许多报刊。这些报刊由于地处偏远,得不到有效关注,许多已经流失和损毁。报刊研究者在研究民国报刊时,应加大对于这些边缘报刊的研究力度。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成绩,刘涛就是其中一位。
第四,同为文学报刊,也有“边缘”与“中心”之别。对于民国文学期刊和报纸的文学副刊,研究者多关注名刊大刊,如《新青年》《小说月报》《新月》《现代》《大公报》“文艺”副刊、《申报》“自由谈”副刊等,而对一些不知名的被遗忘、被遮蔽的“小”刊物,则关注不够,或根本忽略不计。这些处于历史“边缘”地带的文学报刊,如南京《中央日报·文学周刊》、北平《世界日报·明珠》、北平《北平晨报·风雨谈》等,同样也进入刘涛的研究视野。南京《中央日报·文学周刊》由储安平编辑,1934年5月创刊,1936年4月终刊。与《大公报》“文艺”副刊、《申报》“自由谈”等著名的报纸文学副刊相比,《中央日报·文学周刊》几乎没有什么名气,提及的人很少。但就是这样一份边缘性的报纸副刊,刘涛通过仔细考察,发现上面刊登过民国许多重要作家的作品,如老舍、李长之、陈梦家、方令孺、曹葆华、臧克家、林庚、孙毓棠、陈铨、陈瘦竹、张梦麟、田汉、洪深、宗白华、邵洵美、储安平等人。其中不少的作家作品,没有被作家收集,成为佚文,例如穆时英的文章《内容与形式》与《戴望舒简论》。北平《世界日报·明珠》、北平《北平晨报·风雨谈》与《中央日报·文学周刊》同为纯文学副刊,《明珠》在当时有一定影响,《风雨谈》则由于出版时间短,在当时的影响力就有限。时过境迁,《明珠》副刊还得到一些研究者的关注,而《风雨谈》则完全被人们遗忘。在这两个文学副刊上,刘涛同样发现了非常丰富的现代文学史料。由此可见,所谓的“小刊”不“小”,“边缘报刊”并非真的“边缘”。所谓“小”,所谓“边缘”,不过是文学史和报刊史的一种人为设定而已。后来的文学史研究者或报刊研究者,要以历史的态度,超越政治、意识形态所设定的差序格局,发掘和彰显被历史所遮蔽的文学报刊,这样才能逼近和还原文学史本来的无限丰富性与多元共生性。
刘涛抱着人弃我取的态度,舍中心而趋边缘,他对民国大量边缘报刊的精细考察,说明他的治史眼光很独到,值得报刊研究者借鉴。当然,由于刘涛并非纯粹的报刊研究者,他的专业是民国文学研究,因此,他对于民国报刊的研究,就不是仅仅关注于报刊本身,而是为文学研究服务。他从文学角度对于民国报刊的利用与发掘,同样也可给文学研究者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这些启示简要归纳起来有三点。首先,报刊是民国文学研究的源头活水,文学研究者只有进入到民国报刊这个虽杂乱无章但又丰富迷人的资料库中,才能使其研究保持历史的客观性与科学性,才能使自己的研究永葆青春活力。其次,《考信录》通过对作家佚文的考察,深入历史地理空间的深层,发现了被作家主体所故意遮蔽的隐秘事实,揭示了佚文生成与作家、时代、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作者发现,作家佚文的生成有两种成因,一种为时间久远所带来的无意疏漏,即作家佚文之“佚”不是出自作家故意,而是客观历史原因,如历史久远带来的遗忘、报刊之难以追寻或遗失损毁等。一种为作家出于政治考虑,对自己的主体与历史的刻意建构与遮蔽。如臧克家、冰心、曹禺等人的佚文,出现在国民党的官办刊物或有着国民党官方背景的刊物上,而这些文章本身,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与所谓的“政治正确”存有较大距离。因此,这些文章之“佚”,并非单纯的无意遗漏,而是出自作家的有意遮蔽。第三,《考信录》揭示出现代报刊对于历史人物所起的“起居注”功能,为研究民国报刊与历史之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认知角度。通过对北平《世界日报》的“教育界”专版的细读,刘涛发现“教育界”对于一些学界名流如胡适、周作人、冰心等人的报道,是跟踪式的连续报道,对于胡适的报道,甚至可看作是他的“起居注”。这说明民国报刊特别是报纸,在记录民国历史包括民国文学方面,承担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研究民国历史,除档案记录外,另一重要渠道就是民国报刊。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