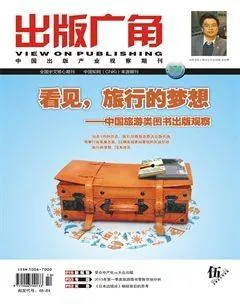一个大教授的小文章
有的人是为制造财富而活的,有的人是为了权力而活的,有的人是为了表现自己而活的。而我,活着就是为了写这些字,通过这些字来表达我的想法。
我写历史文化随笔,起于20世纪末。那时候刚落脚北京,一文不名,也百无聊赖。以前在黑龙江的时候,就喜欢《读书》杂志,于是就试着给它投稿,没想到居然被采用了。于是一发不可收拾,越写越多。渐渐地,别的杂志也来约稿,稿费也逐渐高了起来。反正平时没事总要看书,看到有意思的地方,喜欢把这段史料抄下来,再写上几句话。现在写随笔,无非是把过去的读书笔记扩展开来,弄规整一点。
后来,有人建议我把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归拢起来出书,还真有人要,于是出书。小时候读鲁迅全集,看到鲁迅一本本的集子,无非平时的报刊文章归堆,现在自己也可以这样,心里很得意。这时候,有书商对我说,你小子有可炒作的潜质,我们炒炒你吧,大家挣钱。我说算了,你们一炒,是福是祸我心里没底,反正书也能卖,就这样凑合着吧。但是,轮到这本《历史的坏脾气》了,正好那年香港中文大学聘我去教半年的书,人不在北京,出书的人自作主张,就炒了起来。其实,这本随笔集原来不叫这个名字,书名是书商的编辑起的,若干媒体一炒,就热了。热到一塌糊涂,我才知道,只好随他去了。
打那以后,七八年过去了,我写的东西越来越多,在许多地方开专栏,各大门户网站都有我的博客(多数是人家复制的),微博也开了,有点大事小事,就会有媒体来采访。原来立志做书斋学者的我,变成了一个非常热闹的人。我也才发现,原来我这么能写,写得这么快,有的时候,半个小时就可以出篇时评。
有的时候,也有点困惑,有点找不到北的感觉:我到底是干吗的呢?当然,更多的时候,我还是在看书。凡事想不通的时候,就不想了,这是我避世的法门。我没那么渊博,肚子里的货有限,不看书,就写不出来。这么多年写下来,不写已经没法过日子了,不仅手痒,而且心痒。小时候的志向,就是卖文为生,现在已经实现了。即使没有了学校教书的收入,我也能活。虽说现在的中国,知识产权大有问题,网络到处都是你的文字,收入却没有。印成铅字,刚卖出点名堂,盗版就上来了。而且国家对稿费征的税又高得吓人,稿费稍微高点,一刀砍下来,四分之一没了。但是,只要你产量足够高,换饭吃还是不成问题。
不过,这么些年写下来,你说要是纯粹为了稻粱谋,倒也未必。因为这期间,我也拒绝过一些报酬优厚的活儿。不想写的东西,给多少钱也不写。写出来,无非是想借此表达我读书过程中的一些想法。对与错,是与非,无从论计,但这些想法都是我自己的。有的人是为制造财富而活的,有的人是为了权力而活的,有的人是为了表现自己而活的。而我,活着就是为了写这些字,通过这些字来表达我的想法。这年头,字写多了肯定是会有名的,招人读,也招人骂。热闹到这个份儿上,硬说自己淡泊名利,骗人也不是这个骗法。我当然要名,但我在乎自己的名,名就是我的羽毛,多光鲜谈不上,但却不想让它们变得污浊。在网上,我有敢言之名,但有的事、有的时候,也不是什么话都敢说。但我不能说的时候就沉默,绝不说违心的话。做学问如此,写随笔如此,写时评或者将来写小说,都是如此。
我写我思,实实在在。一旦违心,写作也就没有了意义。写字可以卖钱,但不卖灵魂。陈寅恪先生说,人不能靠学问挣钱,要挣钱,可以做生意。我相信,如果老先生当年经商,也未必不能发财。但是,老先生一辈子养家糊口,还就是靠自己的学问。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命运,走到哪儿,人家都只认你的学问、你的文字。时运好的时候,你可以保持你的傲骨,同时也能拿到那份养家糊口的钱;时运不济,如果还要保持你的傲骨,可能命也没了。
我不知道是否有那么一天,时运不济,连今天这种艰难学文的机会也没了。到了那个时候,我还能不能坚守自己的信念?会不会因为一口饭而放下自己高傲的身段?但愿中国不会回到那个风雨如磐的过去,真要是退回去了,我想,我肯定不会苟活于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