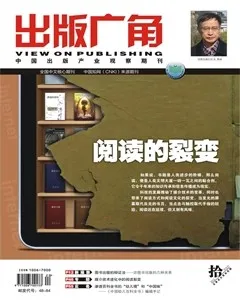谈中国文学对外传播过程中的主体性建构
李永东等认为,如果“走出去”被简单地认为是被西方世界认可,或纯粹为了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就不能不让人担心中国作家是否会因为迎合国际仲裁者的审美口味,逐渐放弃其主体性追求,从而使本国的文学渐渐失去宝贵的主体性。这种质疑对于中国文学的翻译也同样适用。
《狼图腾》引起的关注是空前的。国内学者对姜戎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论断进行了激烈争论,批评与反对的声音同样高亢。《狼图腾》通过英文翻译获得首届亚洲曼氏文学奖,其译者葛浩文及该书英文版成为翻译界研究的焦点。有的学者批评葛浩文的翻译不忠实原文,但更多研究则从目的论、翻译规范等角度分析葛浩文为何要对原文进行改动,以及译文如何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但是,对于何为主体性、译者的主体性是相对于什么而言的,则鲜有论述。本文拟借助福柯的话语概念,通过分析《狼图腾》,探索中国文学对外传播过程中,各方是如何构建自己的主体性的。
话语与主体
主体性这一概念使得个体同语言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关注的焦点从人的本性转向研究意识形态、话语或语言等因素如何塑成主体。笛卡儿提出“我思故我在”,充分强调主体的自主性,却忽略了社会关系及语言在形成主体过程中的作用。拉康把语言的作用引入主体形成的分析之中。他认为象征界对于主体的形成至关重要,象征界依靠语言与规则运作,语言赋予主体以社会身份,主体也通过语言学会了社会中种种规则与禁令。在象征界,主体发现权力的中心位于象征父权的“菲勒斯”,母亲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父亲,对母亲的欲望转化为阉割的焦虑。这种焦虑促使主体遵从象征界的秩序和规则。因此,主体缺乏能动性,其愿望、要求和行动都是为了获得他者肯定。 然而,主体是否只能被动地接受象征界的规则与禁令?这一问题在福柯的话语概念中有不同的解释。
福柯认为话语是所有言说的总和,主体进行言说的过程就是知识产生的过程,但并非任何主体的言说都会被看做是合法的知识,能够参与流通。主体就某一对象的言说,只有符合主流话语规范,才能得到各种权力机构的支持;反之,则会被排除在主流话语之外。福柯认为主体是在主流话语中产生并受其影响的,因此,他不懈地在著作中阐释话语如何产生权力,把囚犯、变态和疯子边缘化。在主流话语的影响之下,不但周围的人这样认定其身份,就连这些群体自己也是这样认定自己身份的。因此,福柯认为世界没有话语,就不存在。人们通过话语才得以理解自己、他们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他们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受各种话语影响、规范,甚至控制。从这个意义上看,主体体现出臣服主体性。但是,福柯也关注主体对主流话语反抗的可能性。
有些学者认为福柯否认了自主主体的存在。哈贝马斯指出,按照福柯的表述,个体不外乎是由话语机械地生产的标准产品。他之所以作这样的论断,是因为他认为在福柯的理论中,只存在一个话语,即主流话语,而没有看到福柯对反主流话语的强调。福柯认为权利是流动的,而非永远由某人或某个团体所掌握,他指出,“话语既是权利的工具,又是权利的结果,但也会成为一种阻碍力量,一块绊脚石或反抗策略的起点”。在《主体与权力》中,福柯指出人类历史上有三类反抗斗争:反统治、反剥削、反臣服依附。最后一类指反对臣服依附于他人或是依附于自身身份,失去能动性。我们不是要发现自己是谁,而是要探究我们可能会成为谁,换言之,我们要反对主流话语对于我们主体性的认定,发挥能动主体性。
译者的主体性
传统译论强调译文要忠实于原文,却忽略了一个事实:译文是在译入语文化中被接受的。译者是一个带有过滤网的容器,而这个过滤网便是译入语话语。为了使自己的翻译为译入语话语所接受,译者必须获得译入语权力机构的支持,这些权力机构包括出版社、图书馆、学术机构和政府机构。因此译者在选取翻译材料和翻译策略时要顺从译入语话语的规范。当前一些研究者提出应发挥译者的主体性,称道译者对原文大胆的反叛。然而,这种反叛背后的原因恐怕与译入语话语有很大的关系:译者对原作的反叛其实是对译入语社会文化规范的臣服。下面就以《狼图腾》为例,分析译者如何在译入语话语中构建自己的主体性。
葛浩文选择翻译《狼图腾》,一方面是出于本人对该作品的喜爱,但另一方面还是出于对美国主流文化的考虑,正如他本人所说:“一定要小心挑选能进入主流阅读的”。作为译者,他是这样来考量《狼图腾》在美国主流话语内的接受情况的:异国情调,成吉思汗之外的内蒙古,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都是能够引起美国读者兴趣的因素。因此,译入语主流话语对译者的影响,从文本选择之初便开始显现。
这种影响在翻译过程中仍然在继续,葛浩文翻译《狼图腾》时做了大量的改动。他一方面批评西方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学,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按照美国话语期待对译文进行调整。首先,他删除了每章前的按语。按语是姜戎从不同时代的史书、典籍中摘出来的,如《史记》《资治通鉴》《多桑蒙古史》《周书·突厥》等,还有波斯语的《史集》、法语的《草原帝国》和英语的《世界史纲》,这些按语构成了小说的另一条叙述线索,追溯了自古以来狼同蒙古族的密切渊源关系、蒙古族征服世界的辉煌以及游牧民族的强健精神,因此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葛浩文依照出版社的要求把这些按语都删除了,因为编辑认为读者所希望看到的是小说的内容,而非这类社科文献。
葛浩文的翻译行文流畅、用词准确,精妙的译文随处可见,体现了以英语为母语的译者优势,但是这种优势有时会凌驾于原作之上。他依照英语的行文习惯对原作进行调整、删减,有时把两段合并为一段,有时会把一段分译为两段或者三段。删减的部分也很多,原文中大量反思中国农耕文化、游牧文化以及中国国民性的议论性文字被删除了,还有一些细节性的描写也没有翻译。除此之外,葛浩文还删除了一些同中国政治、历史相关的部分,这种处理也是考虑到译入语话语的期待、接受能力。虽然总体上葛浩文能发现中国文学的魅力,并且不赞成西方对中国文学的俯就姿态,但从他对《狼图腾》的删减上可以发现,美国文学话语依然影响着他的翻译。如果说删除每章前的按语是出版社的授意,那么删除一些景物的描写则表明他认为那些描写是不必要的,这难道不是一种基于美国文学话语的判断吗?事实上,葛浩文认为“大多数的中国作家写的故事都不够完美, 因此译者必须承担起编辑的责任,把译文变得更加有可读性”。译者的选择体现了他对译入语文学话语规范的顺从,所以表现出来的是其臣服主体性。
中国文学对外传播
《狼图腾》外译被认为是中国文学海外图书市场开拓的样板。《狼图腾》在国内大卖后,其责任编辑便在英国《泰晤士报》、《意大利邮报》及法国的《快报》等外国媒体上展开宣传,美国的《时代周刊》还登了一则文化评述。长江出版集团的宣传策略也很值得思考,他们提炼出《狼图腾》的主题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隐去了小说民族、时代和地域特点,尽力彰显小说的普世价值。长江出版集团的主动出击迎来了英美出版公司的主动联系,最终创下了中国文学海外版权输出史无前例的纪录:已经输出海外版权30多个语种,销量也非常可观:截至2011年5月,英文版已经售出了几十万册,根据亚马逊英文网站统计,《狼图腾》的英、法、日、意文都创造了中国当代小说对外销售的最高纪录。
考察一下《狼图腾》走出国门的征程,可以发现尽管其版权输出国也包括蒙古、印度、越南等东方国家,但对外传播的主要目的地是西方。企鹅出版集团的系列推介活动也是在西方国家进行:英国举办的内蒙古草原风情展览、澳大利亚的游牧文化与现代文明研讨会、美国的读书和推广活动等。这种全球化的推介模式要求各方的全面参与,因此,连不喜欢媒体报道的姜戎也接受了几十家外国媒体的采访。《狼图腾》的推介模式被认为是成功的典范。有些研究者以此为例,总结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对策,包括培养优秀的翻译人才、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版权代理机构、建立国际版权交易平台等,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政策扶持。
政策扶持对中国文学传播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政策体现的是中国主流话语的需求。随着国际化的进一步深入,中国越来越需要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这种需求自然会获得中国译者的响应,因为他们也希望自己的言说(此处以译文的形式体现出来)能够获得权力机构的接纳,从而取得合法性,得以出版流通。纵观中国文学对外传播历程,显然政策扶持偏重于向西方国家译介。已经废止了的“熊猫丛书”主要用英、法两种语言向外译介中国经典著作、传说、史集,也出版了少量的德、日等文的译作;设立于2010年“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资助的目的语言暂定为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德文等5种;自2004年起实施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截至2012年9月,已经同57个国家签订了资助出版协议,但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依然是关注的重点。西方在全球时代的特殊地位造成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平衡,东方国家一味以西方文化为标准,竭力想获得西方的认可,而在与其他东方国家交流方面所做的努力则远远不够。以中国当代文学外译为例,在李朝全搜集的870多种翻译作品中,语种分布情况如下:“日文262种,法文244种,英文 166 种,德文56种,荷兰文30种,罗马尼亚文13种,瑞典文和意大利文各12种,西班牙文、丹麦文、韩文各11种,波兰文和匈牙利文各9种,葡萄牙文和捷克文各4种,俄文、挪威文和阿尔巴尼亚文各3种,克罗地亚文、斯拉夫文和马来文各2种,斯洛文尼亚文、土耳其文、乌克兰文和世界语各1种”。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除了日本外,中国当代文学主要输出地依然是西方国家。
中国这种文化心态体现了对西方主流话语的服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之间日益增强的交流意味着这种交流必须要依循一定的规则与秩fa63a6457e31cdc676a93cdddc776780序以保证其顺利进行,那么要遵循谁的规则?如果把各个国家作为不同的主体,那么,赋予这些主体的象征界是哪里?不可否认,西方仍然是菲勒斯中心,所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与竞争规则还是由西方制定的。东方国家的阉割焦虑体现为担心被排除在全球化的时代发展之外,这种焦虑外化为对西方规则的顺从,而且西方如同镜中之我,在东方国家的眼中是完美形象的代表,使后者产生迷恋认同。因此,作为镜中形象的西方,是东方国家尽力要模仿的对象;作为象征界的西方,是赋予东方国家主体性的大写他者。
如前所述,尽管姜戎不喜媒体宣传,但也接受了多家外媒的采访,然而这种努力依然不够完美:企鹅咨询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由于姜戎不会说英语,因此不能借助作家环游推广以直接面向媒体和读者进行宣传;而且,在英国诸如文学主题庆典这样有利于宣传作家、作品的场合,也是英语流利的作家更受欢迎,遗憾的是中国一流的作家几乎都不会英语,这同“已成功进入英美文学主流的印度作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能断言印度作家一定是遵从西方文化规则的典范,但至少,通过语言的臣服,他们获得了西方的青睐,曾经被殖民的痛苦,换来如今获得西方大写他者认可的门票,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很难说。
李永东等认为,如果“走出去”被简单地认为是被西方世界认可,或纯粹为了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就不能不让人担心中国作家是否会因为迎合国际仲裁者的审美口味,逐渐放弃其主体性追求,从而使本国的文学渐渐失去宝贵的主体性。这种质疑对于中国文学的翻译也同样适用。如果政策倾向于主要向西方国家译介我们的文学作品,译者努力在西方文学话语框架内对译文进行调整,那么各方体现出的都是臣服主体性。然而,正如福柯所指出的,主体能够进行自我反思、有可能抗拒主流话语。在中国文学对外传播过程中,我们要构建自己的能动主体性。可以尝试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东方国家,更多地向东方国家译介我们的文学作品,使其通过了解中国文学进而了解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通过中国文学的传播,与其他东方国家共同构筑东方文化的话语权,为东西方文化平等交流奠定基础。
因此,本文提出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要放在具体的话语中进行。译者在根据译入语话语对原文进行调整、增删时,表现出的其实是主体的两面性:相对原文而言,译者表现的是其能动主体性;但相对于译入语文化而言,译者表现出的则是臣服主体性。在这个彰显译者自由能力发挥的时代,指明译者对原文的反叛其实是对译入语话语的臣服,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但就中国文学外译而言,这会使我们在外译的过程中看明白原语和译语话语之间的权力关系,进而思考中国文学对外传播是要亦步亦趋跟随西方的步伐,还是应该把目光转向东方国家,努力构建自己的能动主体性。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
(本文为宁夏大学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项目号为sk20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