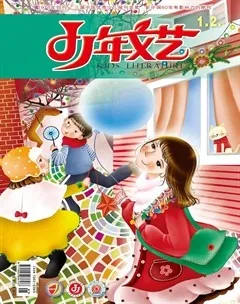炊烟袅袅的渔棚
我常常回溯到岁月的深处,总会想起爷爷奶奶的渔棚,以及渔棚边静静开放的栀子花和袅娜升腾的淡青色炊烟。
渔棚如一叶扁舟,泊靠在灵秀的卤汀河边。渔棚和小河、木桥、芦苇、菖蒲一起构成一幅静谧的油画,晾晒在古朴的岁月里。
黄昏时分,丝丝缕缕的炊烟从高高低低、黑黑黢黢的烟囱里冒出,如悄然绽放的睡莲,再现“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田园风光。
看到炊烟,我们心中便涌起一种温暖激动的情绪,燃烧麦秸穰草棉秆的焦苦味弥漫开来了,粳米萝卜饭青菜团子的香味飘出来了,大麦糁粥泡焦屑端上来了,清炒螺蛳和咸菜炖小鱼的味道令人心驰神往。
那时,队里的内港里养鱼,与卤汀河连通的村头最窄的河道口设有渔棚,用网挡住内河里的鱼。每到过年时,大队里拉鱼的场面十分壮观。家家都分到几斤鱼,人人喜笑颜开。爷爷早年是私塾先生,后来做了队里的会计。平时沉默寡言,忠厚老实,队里便把看守渔棚的营生交给爷爷。
爷爷奶奶的渔棚外观呈一个“介”字,灰色的调子,土坯垒墙,麦秸苫顶,如一条灰色的小船,负载着爷爷奶奶穿行于岁月的河流里,在如烟的往事中颠簸,历经沧桑岁月,恬淡平和,秋叶一样安详静美。
渔棚北边长着一棵粗大的榆树、一棵丰满的柿子树。渔棚的南墙边支着两个泥锅箱,是爷爷在月光下用穰草和着稀泥糊成的,最后在阳光下晒干成形。锅箱里面黑黢黢的,如焦墨。烧黄豆秸或枯芦竹时,噼噼啪啪作响,一股炊烟水袖一样拂过清清爽爽的天空。锅膛间的火光映红了奶奶的脸,也如吞噬柴禾一样吞噬着我们的童年岁月。冬天,我们会央求爷爷在锅膛里炕几个红薯,吃得脸像黑炭。
渔棚的土墙上钻了许多的蜜蜂洞,千疮百孔,光滑圆溜,有如怪诞的象形文字。洞口异常光洁,反射着金黄的阳光。我常常和菊香、英子、桂花、阿珍她们一起,拿着药瓶子,掏洞里的蜂蜜。用一根穰草小心翼翼地往洞里试探,嗡的一声,一只受惊的小蜜蜂扑闪着翅膀,从洞口飞出来。接着用穰草把里面的蜂蜜轻轻拨进瓶子里,用舌头一舔,哇,真甜!于是小嘴吃得金黄,小脸成了秋日的向日葵。
这时,奶奶总是捋捋额前的刘海,我们甜甜地笑,嘴角露出歪歪扭扭的虎牙。
渔棚斜卧在清亮亮的卤汀河边。渔棚边,爷爷用几根桑树桩和几根青竹子搭建了一个码头。小巧的竹桩码头给儿时的故乡带来浪漫的风情和古典的诗意。
凉爽的清晨或闷热的傍晚,总有村妇们蹲在码头上汰洗衣物。河面上水草多,得先用小桶拨开。她们低着头,一缕青丝瀑布般泻到水面,宽大的前襟露出洁白的脖颈,如宋代的瓷器。她们丰满壮硕的身段、凸显的娉婷曲线令人想起古希腊的雕像。性子急的棒槌举过头顶,啪啪声中,让人眼花缭乱。性子慢的,葱白纤巧的胳膊抡出优美的弧线,舒徐有致,如青衣花旦娴雅地甩着水袖。
远处有几只麻鸭和白鹅相互追逐嬉戏,常招来我们的一块碎瓦片,扑通一声,嘎嘎嘎地乱窜。正在洗衣的妈妈回过头嗔怪一声:去、去、去,别伤着奶奶养的生蛋鸭子。
竹桩码头上,只要有村妇淘米,就有很多小柳条鲹鱼争相抢食。这时,爷爷会在码头外围张下细眼丝网,等着鱼儿自投罗网。我们围在码头边,或爬到小木船上,兴奋地看爷爷张鱼。即使有人吆喝着去凿铜板,我们也不理会,双脚像生了根一样。
爷爷的渔网上,鲹鱼越来越多。我们欢呼着,蹦跳着,惊得河里的鱼儿纷纷跃出水面。晚上,凉月初上,一碗清香的炖小鱼,就能让爷爷喝下几盅老麦烧了。我们几个小馋猫总能饱饱口福,连奶奶养的那只小花猫也有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春风荡漾、槐花纷飞的季节,奶奶总会在渔棚的四周种上莴苣、扁豆、丝瓜、番茄、韭菜、青菜等。夏日,她种上芫荽、茨菰、芋头、马铃薯、黄芽菜、大蒜、菠菜、胡萝卜等。一年四季,我们总会吃上新鲜的蔬菜。爷爷奶奶和蔬菜们对望着,在地气氤氲的家园里含饴弄孙。我们这群小伢子也是爷爷奶奶种的蔬菜哩!
奶奶还在门前的泥地上栽着栀子花、鸡冠花、茑萝花、凤仙花、一串红、月季花、太阳花、川穹草什么的,一有空儿,就从河里舀几瓢水浇花。夏日里,花香浓郁,沁人心脾,让人不停地吸溜着鼻子。
奶奶总是不厌其烦地捡拾零落于地的花瓣,然后装在竹匾里晒干,说是用来填枕头,人睡着又香又舒坦。因此,我们常常枕着奶奶的花瓣枕头进入甜蜜的梦乡。
每当栀子花开的时节,奶奶便会把沾露的栀子花轻轻掐下,送给四邻亲友。连过路的素不相识的人,也时常得到奶奶温馨的慰藉。
奶奶喜欢在我们的辫梢上插一朵洁白的栀子花。那浓浓的芳香,一阵阵地沁人肺腑,醉得人忘了童年生活的艰难。我们欢乐的嬉闹声里,总夹杂着幽幽的栀子花香,在寂寥的乡村上空萦纡不散。
渔棚对面的小河边有棵驼背的桑葚树,桑葚紫中透红,蝴蝶般翩跹在绿意沸腾的桑叶间。我们总是最先尝到紫红的、酸甜的桑葚,吃得嘴角满是紫色,像涂了碘酒一般。夕阳如一颗红枣缀在河那边的乌桕林梢,我们的身上镶了一道金边儿,菊香的刘海儿在夕光中细长而柔和,如玉米缨儿。
夏日的水码头最具野性的风情。姑娘媳妇们在浣衣,嘤嘤嗡嗡的,声浪如旖旎的襟带,贴水皮迤逦而来,灵动了色泽丰盈的水乡黄昏。小伙子们一个猛子扎下去,会在招摇的水草间捉到一条鲫鱼或鳊鱼,岸上的人惊呼着,小伙子甩甩头上的水珠,斜睨着搓衣的阿珍她们,一脸的得意。
我们这些细伢子赤着膊,有时挺着小肚皮,有时抠一把烂泥扔上岸,有时潜进水里偷摸水边女孩子的腿,招来一阵脆骂。我们如小鲹鱼似的上下翻腾,一河的快乐在流淌。
待天黑定了,奶奶就点上我们用废药水瓶制作的那盏棕色的煤油灯,捻子扭得小小的,光线昏黄黯淡。我们坐在干净的渔棚前纳凉,月光像卤汀河水一样,皎洁而清凉。爷爷边编竹箩边给我们讲民间故事,不失时机地对我们进行仁义道德教育。奶奶坐在月光的毡子上纳鞋底、结渔网、织毛衣,月光给她的周身涂了光亮的银边,我们分明嗅到一股浓浓的栀子花香。
黄昏里,奶奶会搬出小凳子,坐在门前,结她永远也结不完的渔网。我们坐在她旁边,听她讲白蛇和许仙的故事,听她讲从前的趣事。晚风吹动她稀疏的头发,奶奶如同坐在一幅古老静谧的油画里。
逢到枝头喜鹊喳喳喳乱叫,奶奶总要放下手中的活计,倚门张望是否到亲了,末了,总轻叹一口气。是啊,喜鹊叫,亲来到。奶奶的几个闺女都嫁到几十里外的村里,难得回来一趟。奶奶常念叨她们哩。我们的疯闹在不经意间慰藉了她苦涩的内心。
中秋将至的日子里,奶奶不断念叨着柿子有没有黄熟。渔棚前的秋夜格外静美,月儿如碾如盘,莹莹汪汪,那密密的枝叶滤着月光映在地上,是一幅清简的素描。
奶奶摘下半熟的柿子捂得透熟后,就以一种秋天的姿态送给四邻亲友,余下的再让家人品尝。奶奶总是笑盈盈地看着那柿子树,如同抚摸着自己的儿孙,眼里放射出奇异的光彩。
放网和叉网是很辛苦的。每逢船儿撑近网口时,掌篙人高喊:“来船啦——放网哟——”爷爷应一声,嗤啦一下,网便下沉。渔棚里置一张木板拼成的床,支着打着补丁的纱布帐子。靠床头钉着两根木桩,上面搁着一根辘轳,网绳上系着滑轮,叉网时,扳着辘轳上十字交错的木棍,眼瞅着河网高出水面尺许,就将辘轳上的小木棍扣在木桩中间的绞丝绳上。渔棚里有一张爷爷用楝树根和桑木板钉成的小方桌,桌上少不了一瓶倒扣着酒杯的粮食酒。土墙上挂着粽箬、草帽、抹布、淘箩等物什,流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和乡土气息。
冬夜里,队里的老农摇棹或开挂桨船上街卖大蒜、大葱等,突突的挂桨声打破了冬夜的岑寂。有时渔网被挂桨叶打断,爷爷就撑着小船,拎着马灯,捏着网梭补网。我们躲在温暖的被窝里,感受不到爷爷奶奶经受的寒冷和辛劳。在贫穷而饥馑的年代,我们很容易满足。幸福和快乐简单而透明,像空气和月光一样,时时包裹着我们。
爷爷是在一个夏日的晌午突然中风而去的。那天夜里,渔棚后高大的梧桐树在夜里的雷雨中被拦腰劈断。村民们对此议论了好一阵子,说是雷公显灵呢,好人不长久啊。
那个冬天,奶奶终日抑郁,蜷缩在阴暗潮湿的渔棚里。偶有阳光斜射进来,给她带来些许暖意。惨白的阳光和阴暗组合的图案会使她产生一种快慰。我们默默地望着消瘦的奶奶,眼里的泪珠如栀子花瓣上惨白的露珠。
而现在,奶奶已经年过九旬,步履蹒跚,背驼耳聋,头发苍白,一派萧瑟。那盛满我们快乐和温馨的渔棚,依然静静地趴在村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渔棚斜卧清亮的卤汀河边,守望在风轻云淡的岁月里。如一片叶,静静地躺着,谛听土地的心跳;如一把锄头,犁在我们年少的心上。
每逢栀子花盛开的季节,我总要采摘几朵洁白的栀子花摆放在案头,时时吮吸着乡野深处的清香。村里的姑娘媳妇们辫梢上依然插着清香四溢的栀子花,如一只只小白鸽翩跹着,灵动了吉祥的村庄。
渔棚是故乡和村庄的缩影,盛满乡情和温暖、善良和体贴。渔棚的气质,就是爷爷奶奶的气质,透着宽厚与容忍、质朴与恬淡。在我心浮气躁时,我会踱到村头,凝望岁月深处的渔棚,我不禁想起阿波利奈尔·吉洛姆的诗句:时光流逝了,我们依然还在。是啊,慈祥的爷爷、朴素的渔棚、苍老的榆树、缤纷的童年都湮没在时间的长河里,留给我深深的眷恋和怀想。
发稿/沙群shaqun2009@yaho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