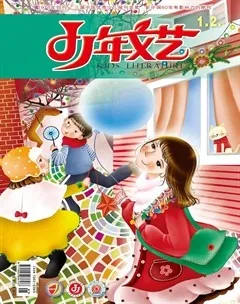一碗米粉解乡愁
乌鲁木齐的姑娘们没有不爱吃炒米粉的。大凡学校门口,必有两三家米粉店,一到中午便人声鼎沸,一座难求。而那些吆喝着“老板,多放些辣子”的剽悍食客,多半都是青春无敌的姑娘们。
新疆的米粉,不同于湖南米粉、桂林米粉、云南米线,它采用贵州出产的小指尖宽度的粗粉,改良新疆传统的炒面方法炒制。翠绿爽口的芹菜段,油亮入味的小白菜,薄软喷香的鸡肉片,还有一根根弹、韧、软的米粉,被一锅浓稠且红辣的汤汁所包裹,别提有多诱人了。姑娘们尽管被辣得涕泪横流,频频去取餐巾纸,但下回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进店抢座,对老板喊声:“小鸡炒,爆辣!”所谓“小鸡炒”,自然就是那经典口味——小份鸡肉炒米粉了。
我读初中时,学校门口有一家米粉店,尽管时时垂涎,却非周四中午不去。这倒不是说周四中午有什么特殊福利,而是因为若在平常日子里,莫说每个位置都已“名花有主”,就是老板炒制的速度也是远远跟不上食客点餐的速度,稍晚一步,便只有急得跳脚与干瞪眼的份了。而我们周四上午的最后一节是体育课,离下课还有几分钟,“念粉心切”的我们便可趁机开溜,冲进米粉店抢占先机。记得有一次,两拨女生甚至为了一个桌子的归属剑拔弩张,险些动起手来,米粉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老师也是爱吃炒米粉的,只是他们并不轻易屈尊下馆,而多是派我们代劳打包。
说说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两家米粉店吧。一家是七一酱园附近的啊臻米粉,它自制的辣酱风味独特,米粉以酱香著称。汤汁清洌浓郁,色泽红润,据说是用鸡肉、牛骨熬制的,且有一股中草药的味道。每食此家米粉,必要手持三件宝——馕、凉茶与餐巾纸。馕是一种烤制的圆形面饼,用馕蘸着汤汁吃,方不负这香汤美味。浸过汤后的馕酥软可口,就上米粉可谓绝赞。凉茶有泻火之效。若你能承受一般的辣味,不妨要微辣米粉;若你喜爱吃辣,便可要一般辣的米粉;至于那绝顶爆辣的级别,则非一般人的味蕾所能承受了。若不喝凉茶,仅品热茶,胃里难免如火焰山一般。通常下午有体育课时,中午我们便不轻易去吃米粉了。
南昌路上也有一家米粉店,是十年老店,非常大牌。它有诸多规定——周一不营业,每天的营业时间仅在下午1点到4点之间,两人在店内不得同吃一碗米粉。它的鸡肉米粉并不用惯常使用的鸡胸肉,而是带点碎骨的鸡肉,菜也不用芹菜,而是腌制的酸菜——倒也别有风味。
年纪稍长的人多不能忍受米粉之辣。有一回老爸老妈逛街,随便挑了一家米粉店解决午餐。结果望着一碗红彤彤的米粉,真是食之难咽,弃之可惜。
离开家乡后,我越发想念新疆的鸡肉炒米粉。可惜在异乡的新疆风味餐厅里,大多只有过油肉拌面、大盘鸡、炒面、烤肉、丸子汤、汤饭等等,虽然种类也很丰富,但其中罕见炒米粉的身影。我思米粉心切,偶尔只能点一碗桂林米粉,聊解乡愁,越发觉得口中寡淡。在河南洛阳旅行时,忽见美食街上有贵州米粉的招牌,欣而往之。店家端来鸡块米粉——没有我熟悉的炒米粉身影,只有一碗清汤,一卷寡粉,其上卧着几个鸡块,香菜少许,点缀其间。我失望极了,未及吃完便弃之而去。
另一次,我听说北京西单附近有一家新疆米粉店,老板是乌鲁木齐人,米粉味道正宗。尽管当时已经吃过饭,但我还是像刚出洞的老鼠嗅到奶酪一样,央求老乡带我前去。坐公交,倒地铁,七拐八拐找到时,却发现大门紧闭。一时间,我的期待土崩瓦解,只能咽咽口水了。
有一次在外吃饭,无意间听人说到人民大学附近有家“戈壁米粉”。一听这名字,我就敏锐地嗅到了家乡的味道。于是乎,手机地图,迅速定位。怀着激动的心情,又一次踏上了“寻找米粉”的征程。
多么熟悉的味道啊!米粉一端上来,我的舌头仿佛都不听使唤了,这味道熟悉得让我窒息。一样的鸡肉片,一样的芹菜,一样的辣椒,一样的米粉。这真是“独在异乡为异客,一闻米粉泪沾襟”了。
在这米粉之中,是我浓郁的乡愁。
发稿/庄眉舒 zmeishu@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