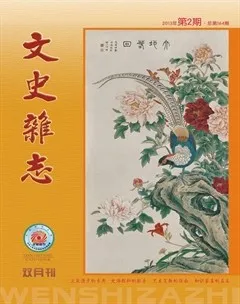孟子是怎样成为“亚圣”的?
有人认为,战国末年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已享有“亚圣”尊号。也有人说,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孟子戴上了“亚圣”桂冠,“孔孟之道”成为儒学亦即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代名词和同义语。其实,这都是想当然的说法,孟子真正成为“亚圣”是在明朝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此时,孟子去世已1800多年了。这就是说,实现从平民思想家到“亚圣”的角色转换,孟子花了1800多年。
孟子在世时,虽已是闻名四方的学者和桃李满园的名师,但因其政治主张过于迂阔,未为诸侯所采用,故社会地位不高。即使在儒学圈子内,因孔子死后,“儒分为八”(韩非子语),孟子学派仅是其中的一派而已,并未取得强势的权威地位。不仅如此,他的性善论、“法先王”等观点,还遭到同为儒学大师的荀子的严厉批驳。所以,正如周淑萍《两宋孟学研究》一书所说:“孟子其人其书其说,在其生前至秦末,除了本派的支持外,在外界可谓应者寥寥,无人喝彩,而受到的抨击和诘难反而相当猛烈。或许在当时许多人眼中,孟子不过是百家争鸣中一位言辞犀利、咄咄逼人、机敏果决、意气豪迈、好与人辩、敢为天下先的儒士,其学说也只是百家中的一家之言而已,没有值得推崇的特别之处。”[1]司马迁所撰《史记》流传开后,因其中有《孟子荀卿列传》一篇,于是人们便常将“孟荀”连称,有时也称“荀孟”。这说明,西汉中期及其以后很长时间,孟子和荀子的地位差不多,某些时候甚至比荀子地位还低一些。孟子地位的转折始于唐朝中期。当时,一些士人开始抬升孟子的地位,促使“孟子升格运动”兴起。
一、“孟子升格运动”的分期
首先使用“孟子升格运动”这一概念的是当代著名经学史研究专家周予同。一些学者也称这一运动为“贵孟”运动,或《孟子》升经运动。该运动的目标是要将孟子由平民学者升为圣人、将作为子书的《孟子》升为经书。整个运动历经数百年之久,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这里依据史料,并参考周淑萍《两宋孟学研究》、徐洪兴《中国学术思潮史·道学思潮卷》等书,将相关情况作一简介。
第一阶段:唐朝中后期——孟子升格运动的初兴期
唐朝宝应二年(公元763年),礼部侍郎杨绾上疏建议把《孟子》与《论语》《孝经》并为“兼经”,作为科举考试科目之一。其虽未得准允,却发出了将《孟子》由子书升为经书的先声。
唐朝著名文学家和思想家韩愈(768~824)在其影响深远的《原道》《送王秀才序》《读荀子》等文中,提出“道统论”,并开列了“道统”人物名单。他认定孟子是孔子真正的也是唯一的传人。此说奠定了孟子升格的理论基础,揭开了升格运动的序幕。
唐朝咸通四年(公元863年),晚唐著名文人皮日休又一次提出将《孟子》列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建议。这一建议虽仍未获准允,但如将其与杨绾、韩愈的言行联系起来,可以看出要求孟子升格已成为一种思潮,孟子升格运动已有一定声势。
第二阶段:两宋时期——孟子升格运动的全面推进期
孟子是战国时期鲁国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北宋景祐五年(公元1038年),孟子故乡兖州邹县建立了全国第一座孟庙。此庙由当时知兖州的孔子第三十五世孙孔道辅主持修建,后获朝廷认可。
北宋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孟子》一书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其官学地位确立。以后,该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要教材之一、科举应试者的必读之书。
北宋元丰六~七年(公元1083~1084年),孟子首次受封官爵。宋神宗诏封他为“邹国公”,从祀孔庙。孟子开始被神化。而荀子仅封为“兰陵伯”。这一巨大差别反映了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扬孟贬荀”倾向。
北宋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5年),《孟子》被刻石,成为经书,列入儒学《十三经》之中。
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大力推崇《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种儒学著述。南宋理学家朱熹将这四种著述结集在一起,并作了章句、注疏,合称《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成为后人学习的“范本和定本”[2]。南宋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宋理宗下诏表彰朱熹的注解是“发挥圣贤之蕴,羽翼斯文”;在与朱熹后人谈话时,还说他恨不与朱熹同时。理宗的这些话,既抬高了朱熹,也提升了《孟子》的地位。正因如此,这一时期陈振孙编撰的《直斋书录解题》把《孟子》列入经书类著作中。《孟子》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序》中写了如下一段话:“或问于程子曰:‘孟子还可谓圣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圣人,然学已到至处’。(愚按:‘至’字,恐当作‘圣’字。)……又曰:‘孟子有些英气。……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括号中的“愚”为朱熹自称。据此可知,在两宋理学家二程、朱熹心目中,孟子已是“亚圣”了。只不过这仍属民间意识,孟子要真正成为神化的“亚圣”,还差以皇帝为代表的朝廷认可这至关重要的一步。
第三阶段:元明时期——孟子升格运动的延续期
宋蒙对抗时期,理学和尊孟之风已传到北方。元朝建立后,孟子升格运动延续。
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元朝恢复科举考试,以《四书集注》为命题依据。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元文宗加封孟子“邹国亚圣公”。
明朝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明世宗更定孔子祀典,改孔子封号“大成至圣文宣王”为“至圣先师”,将塑像改为“木主”(木质牌位)。相应地,作为从祀者之一孟子的尊号也由“邹国亚圣公”改为“亚圣”。孟子走完从平民学者转变为“亚圣”的漫漫长路。但这里还需指出的是,“亚圣”之“亚”,与“冠亚”之“亚”,并非同义;其本意是相当于圣人、与圣人同一流。而且,明世宗改定祀典、变更尊号时,排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的还有“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三人。这就是说,在此时的儒家圣人序列中,孟子不过是“老五”。但北宋以来,“孔孟”连称已很普遍,“孔孟之道”已广为流行,《孟子》已成“经”,孟子的地位和影响已远超颜子、曾子和子思,所以,名义上排列第五的孟子,实际上已“稳居第二把交椅。”[3]
二、“孟子升格运动”的成因
正是孟子升格运动把平民学者孟子推上了“亚圣”的宝座,使他成为孔庙内“至圣先师”木主旁的又一尊神,且地位重要。那么,为什么是唐宋元明时期而不是别的什么时候发生孟子升格运动,为什么是孟子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最终成为“亚圣”呢?应该说这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首先,孟子有成为“亚圣”的本钱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学说的重要代表。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构建了以性善论为基础,“仁政”为核心,重视内心修养为特色的完整的学说,影响深广长久。《孟子》是儒学的重要经典,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语约意尽,文字精妙,历代注释不断,阅读者、引用者难以统计。这些都是孟子入圣的条件和资本。舍此,孟子升格运动不会发生,孟子成为“亚圣”则不可能。我们知道,孟子成为“亚圣”之前,颜回是“亚圣”。颜回是孔子的弟子,因安贫好学,为孔子一再表扬。唐朝时,玄宗加封他为“亚圣”。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按古代标准,颜回的个人品德可谓出众,但他一未创立自己的学说,二没著述留传后世,三未培养出多少弟子,作为“亚圣”,给人以徒有虚名之感。其“亚圣”尊号最终不保,势在必然。一般认为,孟子取代颜子为“亚圣”合情合理。
其次,儒学转型的需要
儒学史研究者一般认为,“内圣”与“外王”构成儒学的主题,孔子思想包括了这两个方面。作为儒家后学,孟子更多地关注和发挥了“内圣”这一侧面,荀子则更多地关注和阐释了“外王”这一侧面。孟子以不忍之心为仁政的出发点,荀子以礼为道之极。汉唐儒学重视礼制和教化,荀子思想色彩浓厚。但安史之乱以及其后的社会现实表明,这种儒学作用有限,既不能真正“教化”人,更不能使天下长治久安,还难以应对佛教与道教的挑战。儒学到了必须嬗变和转型的时候了。朝什么方向变和转?当时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从“外王之路”转向“内圣之境”。而上文已说过,重视“内圣”是孟子思想的重要特点。周淑萍在《两宋孟学研究》中指出,四心、四端、仁义礼智、性善、诚、良知良能、尽心、存心、善心、寡欲、知言、养气、义利、王道等是“孟子思想的基本命题”[4]。这就是说,孟子思想可为儒学的转型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冯友兰认为,如要在儒家典籍中寻求一种可以抵消佛教影响,回答当时人们感兴趣的问题的书,“《孟子》一书,实其选也”[5]。徐洪兴在《中国学术思潮史·道学思潮卷》中也说,心性论是孟子思想最精彩的部分之一,此可谓是孟子升格运动兴起的“关键之所在”[6]。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将孟子塑造成“亚圣”,将《孟子》提升为经书,是那个时代的需要。
再次,一代代“造神者”的不断努力
从中唐起,一批又一批士人参与孟子升格运动,为孟子登上“亚圣”之位立下汗马功劳。他们当中,不乏地位高影响大的知名之士,如韩愈、皮日休、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张载、王安石、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等。正是他们的尊奉、抬举和吹捧,才使孟子终成“亚圣”。
这里有一个现象很值得研究,那就是在“造神”过程中,一些“造神者”影响不断扩大,地位迅速上升,其结果是有的自己成为贤者、圣人、准神,乃至真神。如南宋理宗就下诏表彰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让其“列诸从祀”。这样一来,孔庙中又多了几块木主神牌。这一现象促使我们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某些著名造神者“造神”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最后,以皇帝为代表的最高统治者的认可和诏封
儒学圈内称孟子有“亚圣之才”或视其为“亚圣”,远早于明朝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但这属民间意识,仅仅靠此显然不足以使孟子成为“亚圣”。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是官方统治思想,要成为这种思想中地位仅次于“至圣”孔子的重要象征,则需统治者认可。这即是说,“亚圣”尊号必须由皇帝加封。北宋神宗封“邹国公”、元朝文宗封“邹国亚圣公”、明朝世宗更封“亚圣”,是孟子坐上儒家圣人序列的第二把交椅的“三级跳”——皇帝的认可至关重要。
世上本无神,神是人造出来的。孟子成为“亚圣”的过程是一个典型的“造神”过程。
研究这个过程,有助于我们揭露历史上各种“造神”运动的秘密。
注释:
[1][2][3][4]周淑萍:《两宋孟学研究》第20页,61页,导论,第1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冯友兰:《中国哲学小史》第5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徐洪兴:《中国学术思潮史·道学思潮卷》,第116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成都大学退休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