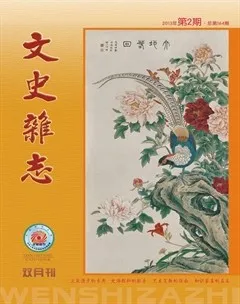“倒马桶”引出来的“龙门阵”
最近电视报道,从老式雕花马桶,到彩色的塑料痰盂,倒马桶这件日常琐事记载了上海小弄堂百年的变迁。从2006年开始,上海市政府利用专项资金免费为17个区县所有老式房子中没有卫生间的家庭安装抽水马桶,仅黄浦区这样的家庭就有近十万,从而结束多年来走路倒马桶的难题。这件事情使笔者想起上世纪60年代“四清”前夕在盐道街学校任教时,曾听从领导安排,以羸弱之躯参加过一次跟清洁工人“同劳动”的锻炼,改造“怕脏怕臭”思想;不仅当“掀桶皇帝”,推过满载粪水黄桶的大板车,而且挑过尿桶沿街高呼“倒桶子!”帮助老弱病残倒过马桶子、尿罐子。抚今追昔,笔者作为“老成都”还想为如今坐惯抽水马桶,进过星级洗手间,却不晓得老成都旧貌的青少年读者再摆点这方面的“龙门阵”。
上世纪50年代以前,俗谚有“东大街的茅房——难找”,说明那些大街上公共厕所不多。公馆大宅有私家茅厕(máo·si)自用,而绝大多数小户人家只好使用大小马桶子、夜壶、高痰盂,临时储盛大小便,早晚送往大茅厕倾倒;或者听到吆喝“倒桶子啊!”赶忙提起去倾销,接着就当街洗涮几遍,提回家去。涮的脏水自然倒向街边的阴沟,甚至阳沟,听其流淌,千回万转,最后归入府河和锦江,顺流消化。
城市大量的粪便基本上靠四乡的农民进城挑运。每天清早天麻麻亮,卖了菜的农民仍担起空尿桶进城,分赴各家各户舀茅厕的粪水(都已事先与主人家约定上门时间)。他们不但付出劳动,搞好清洁,每年还会给主人家送点豌豆、胡豆,表示谢意;主人家也回赠些点心或叶子烟。正所谓“人情美美”,“礼轻仁义重”。
为啥农民乐意进城挑粪水?因为粪水就是40年前中国农村种田栽菜唯一的肥源。“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所以农村人家除了自家把猪圈和茅坑修在一起储存人畜粪,还在路边搭茅草棚(不封顶)挖茅坑,既让路人方便解手,又可以攒积肥料。此外还要拗起狗屎鸢兜四下捡狗屎。俗谚云:“初五好日子,火烧门前纸。大人做生意,娃儿捡狗屎。”地种得多,肥源成问题,就得进城挑粪水,或者去粪塘子买粪水。直到上世纪60年代,城边羊皮坝路旁、皇城边街(白果林一带)还有菜农种植蔬菜,菜畦旁边都有储存粪便的大茅坑。上世纪60年代初,曾任毛主席秘书的田家英同志当年到新都县大丰区蹲点,就多次率领社员进城收粪水造肥。70年代,龙泉驿山泉大队还特派社员常往成都实验小学,利用校内几个厕所的粪水和筛选的渣土制造“颗粒肥”,运回果园和菜地施肥。何以为报?生产队也每年卖点桃子、苹果给学校,互相支援,体现美美人倩。
旧时通商大衢的大茅房人来得多,粪便存储量大,每天有雇用的农工清除运送,那是粪塘子老板包揽的大生意。粪塘子算得城市三百六十行中的特殊行业。《商务早报》载《四川旧闻:粪塘子春秋》说:旧日成都出东门大桥,椒子街、均隆河边街、望平后街、布坝子、天祥寺靠河边都是储存待运粪便的粪塘子(一丈多长,六七尺深的大坑)。上面由谷草搭棚遮雨,塘沿上铺以竹筏和木板。粪塘子老板雇的守粪人就在此居住,所谓:“穷椒子,臭椒子,出门就是粪塘子。粪塘子上草棚子,竹笆子上烂席子,上面住的干鸡子。苍蝇蚊子加耗子,臭虫虱子蛆儿子,生活不如叫花子”。其余拉粪、收粪人的工钱少得多,还要自寻落脚之地。每个月做不够“工口”(数量),要扣工钱。不论天晴下雨、酷暑严寒,必须早出晚归收运粪便。一旦出城晚了或在街头洒泼了粪水,会被警察惩罚担水洗街,“工口”做不够,饭都a97bfb563fdb1660961bbe6eddba4942没得吃。
粪塘子老板每天早晚坐茶馆与买主谈好生意,出货商自家去粪塘子,用木船赶水路运往华阳、仁寿、眉山等地。粪船上成都时也不放空,要运载柴捆子和其他货物来水津街卖。
据说东门的粪霸刘某,仗势欺人,雇人无偿清运东门一带机关、学校、工厂、商贸以及街面上公厕的粪便,欺行霸市。春秋两季农忙,急需肥料,他就抬高市价,趁火打劫。河边上几十家粪塘子谁敢不看刘某的价格卖粪,就会丢了赖以求生的粪塘子,整得倾cb37a154c68b6d7f9374834327957f1c家荡产,沦为收粪人。1951年初清匪反霸运动中,刘某被镇压“敲了沙罐”(枪毙)。
《成都日报》刊载《从伤心街到风水宝地》说:上世纪40年代,浆洗街上有近10家大粪经营专业户,主人雇工从城里清运粪便,储存在自家粪塘子,就地出售。近郊的农民一般进城卖了菜后,顺便买些用鸡公车运走。双流、新津的买主,一股用箩筐装着挑走。据说这样透气,大热天也不会翻泡。紧临浆洗街的桓侯巷一带,还有个狗粪市场,每逢赶场,便有人做狗屎的小买卖。北门头福街外有大粪塘,西门南巷子一带有大粪塘,较东门、南门的规模小些。按理分析,成都市四门都该有储存性质的“大粪塘子”,但笔者未曾调查了解全貌,无法详说,是为一憾。这四门设粪塘子,也便于农村的买主各自就近购买。
新中国成立后,成立清洁管理所,粪塘子逐步改造。1958年,大搞卫生运动,椒子街一带的贫民,苦战三天三夜,填平了全部粪塘子。当地街道办事处组织了6个生产组,安排了250多人参加工作。上世纪60年代初,浆洗街近10处粪塘子也先后绝迹了;洗面桥的粪塘子,因紧靠桂溪乡菜地,不碍市客观瞻,过了很久方才废除。改革开放前,成都普遍使用旱厕,虽有专人打扫,保持卫生,但仅靠大坑储粪,定期清除,仍难免臭气熏人,尿水遍地,常有人滑倒受伤,令人望而生畏。城管规定晚上清运粪便出城。每晚街灯未亮之前,万里桥南头和东门大桥东头,少则十余辆,多则数十辆安放着专运大粪的椭圆形黄木大桶的平板车排起长龙,等待进城。街灯一亮,一声放行,运粪车队立即启动,轰轰隆隆,浩浩荡荡,恍若坦克阵势匆匆忙忙冲过大桥进城,分奔大街小巷,堪称蓉城环保卫生一大“壮观”。
改革开放后,私厕、公厕的粪便经过稀释,由污水管输送出城;或由清管所的专用汽车抽运。若非偶有意外,大家都几乎看不到如何打开排污管,掏捞转送那些既脏且臭的人体排泄物。“倒桶子”、“尿水担子”、“粪塘子”、“坦克进城”……这一切虽说是青少年们闻所未闻的“西川夜谭”,却也成为老成都人茶余饭后偶尔提起的有趣记忆。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