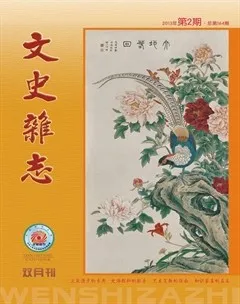鸟纹图像音乐意义考释
借用艺术图像研究古代艺术品,是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学等学科研究常常采用的方法。图像学的概念,在19世纪下半叶,由法国学者E·马莱最早提出,最初主要用于历史科学研究中对文献价值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以来,图像学成为西方艺术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一些西方艺术史研究者开始运用视觉艺术原理,从考察艺术图像题材入手,深入阐释在特定历史情景中艺术品的主题、内容及文化内涵。美国学者E·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视觉艺术的意义》[1]一书,对图像学的基本理论作了系统论述,创立了西方艺术史研究新的方法论。帕氏认为,可以分三个层次解释图像的意义:1. 解释图像的自然意义,即识别作品中作为人、动物和植物等自然物象的线条与色彩、形状与形态,把作品解释为有意味的特定的形式体系。2. 发现和解释艺术图像的传统意义,以及解释作品所表达的特定主题,也叫作图像志分析。3. 解释作品的内在意义或内容,这种更深一层的解释叫作图像学。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宗教、哲学,通过艺术家的手笔凝聚在艺术作品中,成为作品的本质意义和内容,即帕诺夫斯基所谓的象征意义。
《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精确地概括了图像研究的意义:“发现和解释艺术图像的象征意义,解释图像在各个文化体系和文明中的形成、变化及其所表现和暗示出来的思想观念。”[2]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大量出土各类艺术品,随着电子数码摄影技术的广泛使用,对艺术图像的制作越来越方便,对艺术品的研究也越来越依赖于对图像的解说和诠释。“图像学”成为许多学科新开设的一门课程。我们对汉代画像砖、石图像的研究,就属于“图像学”研究的范畴。在研究过程中,一方面我们运用图像学原理和方法,从图像所传递的信息中,客观地对图像本身的意义作出阐释;另一方面,采用历史学“双重证法”,以图像与文献记载互证的方法,对图像所表达的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含义作出分析和阐释。
《文史杂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用图像学和史学方法,简明分析古代艺术图像的园地。笔者多年来在此发表小文,受到读者欢迎,也增加了笔者撰文的兴趣。笔者在此,继续对前年发表的《汉砖上的“古乐”考二题》[3]中的“凤鸟悬璧”图像的音乐意义,作些考证;对鸟图形与音乐的关联意义,作些阐述,与读者共享,并望得到专家指导。
凤鸟与乐律。“凤鸟悬璧”(图一)是四川出土汉代画像砖图像中常见的一个题材。[4]“凤鸟悬璧”可表达的音乐意义我们已作过分析:l. 悬璧可敲击发出乐音传播。 2. 见于文献记载的最早的礼乐仪式名为“凤凰来仪”。3. “凤凰来仪”是古代祭祀乐舞的一种表演形态,由人化装成鸟兽的舞蹈形态。这种仪式性舞蹈,是祭祀仪式中的主要方式。4. 凤鸟与乐律。凤鸟与音乐的联系,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意义,即它蕴涵着我国关于十二律起源的传说。《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昔黄帝令伶伦作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黄帝又令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吕氏春秋》是我国先秦文献中可考写作年代的著作,成书于秦始皇即位之后5至8年,汉代已广为流行。其中对音乐起源、原始音乐的记载,代表了秦汉时期我国知识阶层对音乐的认知水平,也为后人研究史前音乐留下了珍贵资料。上述关于我国制定十二乐律的记载,以凤皇的鸣叫音为标准,凤为雄,成六阳律;皇为雌,成六阴律,反映了我国乐律体系的形成与早期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的特点;它还记载了我国乐律是以“黄钟宫”为本,上下生之,即用三分损益法制定十二律,这种律制在先秦时期已经成熟。
金沙出土两件璧形器物上的凤鸟图像,其中一件是青铜带柄璧(图二),璧的肉面上刻有3只凤鸟环璧孔飞翔。另一件神鸟绕日金箔璧形图像,璧的肉面上有4只凤鸟,中间太阳的芒纹恰好是12个。凤鸟与汉代画像砖上的凤凰图像极为相似。金沙出土两件璧形器上的音乐图像,反映出丰富的音乐内涵:首先,璧与凤鸟的联系,表明璧可敲击发出音高,而凤鸟的鸣声又可以确定不同音高。其次,我国早期关于音乐的起源和音律的认识,与天文和历法相关联,在文献中有大量记载。两件璧上的凤鸟一个为3只,另一个为4只,如果把中间的圆环作为太阳的象征,凤鸟围绕着太阳飞翔,旋转,与十二律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是吻合的。金箔上的凤鸟绕日图像上的太阳芒纹,恰好是12个,与12音律也是相等的。而3只凤鸟或是4只凤鸟的不同,可能与古代对历法的三季分与四季分有关联,也是需要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出土于山西曲沃县晋侯墓的“晋侯苏编钟”中,有12件编钟的正面右鼓部位,均铸有一只凤鸟图形,作为侧鼓音的敲击部位的标志。敲击凤鸟标志处,所清晰得到正鼓音上方的小三度音,音质纯正。[5]可见其调音已按乐律标准定音。鸟形标识既表示此为侧鼓音敲击部位,也含义此组编钟依据十二律调整音高,可旋宫转调。
达尔文音乐起源于鸟鸣之音的理论。鸟纹图像与音乐的关联,是我们在研究史前文化中应该特别注意的一个意义,也是我们在考察文物图像时应该考察和阐释的一个重要方面。如良渚文化玉器上的鸟纹图像和祭坛,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中的青铜树上的神鸟雕塑、鸟头柄形器等,其中的鸟儿,都被当作神鸟,表达了早期人类借助鸟儿的鸣唱和飞翔,与天地、自然沟通的愿望。鸟的图像,蕴涵着人类模仿鸟鸣之音,学会歌唱,学会语言的早期成长历程;蕴涵着人类早期认知行为的发展和成长;也蕴涵着人类早期精神需求和原始信仰的发生与发展。因此,鸟纹的图像成为史前考古学、文物学收集到的最多的形象之一,也成为图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种类。
关于人类音乐起源于模仿鸟鸣之音的理论,最为科学的考证和论述,是由19世纪末叶的英国科学家CH·达尔文提出并完成的。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指出:
1. 音乐起源的时代及物理特征。人的声音的进化,是由于发音器官构造的不同和发育能力不同促进的。人类音乐起源于非常古老的半动物祖先时期,由于择偶的需要,发出不同的音调,渐渐在重复的过程中,成为各个不同民族的“音乐语言”。虽然不同种族对音乐调子的感知和对音乐的运用不同,但是,音乐的能力起源于半动物祖先的时代。这个认识,乃是达尔文与同时代的科学家们以进化论原理为基点考察并得到验证的真理。人类对音乐舞蹈、装饰等早期艺术的认识,是在与大自然的接触中渐渐获得的。人类之所以能够从鸟禽和动物的叫声中获得音乐的感受,是由于人类天生具有的禀赋和人类器官构造使然,是不可抗拒的。
2. 鸟鸣之音的音乐特征。达尔文举出同时代学者研究不同鸟类鸟鸣之声不同的例证,精确地描述和讨论了鸟儿叫声具有音乐的特征。他认为“鸟类的鸣声是用于表达多种感情的,诸如痛苦、恐惧、愤怒、胜利或单纯的快乐”。比如母鸡下蛋时,频频地重复同一种叫声,以高于六度音程而截止,最后这声调持续较久,以此来表达下蛋的快乐。
达尔文认为,大多数鸟类主要是在繁殖季节才发出真正的鸣唱以及种种奇特的叫声,这是用于献媚异性,或仅仅是用于召唤异性的。当一些雄性鸟儿被长久地关在笼子里,或者当它们处于寡居的状态时,都会纵声唱出委婉的曲调。
达尔文认为:“鸣唱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艺术,而且通过实践会大大提高。”他举例同时代的詹纳·韦尔先生描述的一只鸟儿被教会鸣唱一支德国圆舞曲,它演奏得那么好,当这只鸟首次被放进一间养育其它鸟类的屋内并开始鸣唱时,所有其它鸟类,约有20只,都排列在各自鸟笼里最靠近它的一边,以最大的兴趣倾听这个新来客的演奏。
达尔文的研究证明了:鸟类之所以能够鸣唱,是由于它们具有构造复杂的发音器官,使它们能够发出各种声乐。
3. 鸟鸣之声也具有器乐特征。达尔文在研究中还发现,除了鸟儿从喉咙中发出的各种声乐外,不同的鸟类的雄者在其求偶期间所发出的鸣叫,都可称之为器乐。如雄的孔雀和凤鸟,即天堂鸟(bier of paradise),会振动羽毛,互相撞击,发出咯咯声;一种北美的松鸡,在求偶时会用它的双翼急击其背而发出鼓声。有人把它们比作远方的雷声,有些人则比作快速擂鼓之声。他还发现“鸟类的某些羽毛乃是为了发声的特殊目的而发生变异的”。比如有一种叫普通丘鹬(Scolopax gallinago)的鸟儿所发出的声音,令听者惊奇,因为它们其实包含了大自然的许多音响,如鼓声、羊叫声、马嘶声或者雷鸣声。科学家们还发现,这种鸟只有在交配季节飞到“也许高一千尺的天空”,然后以惊人的速度沿着一条曲线降落地面时,才能发出这些响声。这是由于它的尾部两边的外侧羽毛具有特殊构造。
达尔文最后在结论中总结到:许多鸟类的雄者在生殖季节里所发出的声乐和器乐声音的多样性,以及发出这些声音的方法的多样性,值得高度重视。不难想象鸟类的声调最初仅仅是作为一种召唤或用于某种其他目的,继而可能改进成为一种有旋律的歌唱……在达尔文看来,语言是人类获得的最晚的,也是最高的艺术;语言的形成是建立在人类对音乐的表达基础上的。[6]
达尔文以生动具体的实例和反复考察确认的结果,对音乐的起源作了令人信服的理论分析和最终结论,从而提出了关于人类音乐和器乐产生的进化理论。人类对音乐的感知和运用产生于如此久远的时代,人类最早的歌声早已消失,不可再得;但是当人类开始制造、用以发出模拟自然或者动物的发音器时,乐器产生了,那些材质坚固的乐器被遗存下来,为后人提供了可靠的考古资料。一些鸟儿的图像被雕刻成塑像,被描绘成图画,刻绘在器物上,也成为后人研究音乐的考古资料。历史文献中的大量记载,从神话学、历史学、传播学等多角度,为后人提供了文献参考资料。考察我国出土鸟形文物或图像,结合文字记载,我们可以得到的基本结论是:鸟儿图像总是与音乐联系在一起的;凤凰是皇家音乐的最高使者;凤凰的形象也是中国美德的象征。下面我们再分析两例著名的鸟纹图像加以证明。
良渚玉器上的鸟纹。朱乃诚先生在《良渚文化玉器刻符的若干问题》[7]一文中,对良渚刻符的分类、相对年代、刻纹的变化、刻符的含义作了比较全面整理和研究,其他学者也作过多方面研究,比较一致地辨析出,这些刻符中的最明显的标志是代表祭坛的“框形”和鸟纹。在朱氏引用的6幅鸟纹图像中,有4幅刻在玉璧的器面上,有2幅刻在玉琮的射部。鸟纹以写实手法绘制,生动逼真,与墓葬中随葬的鸟形塑像所用写实手法是相同的。由此反映出,良渚人在艺术思维和艺术技巧发展阶段上,还处于直观和写实手法阶段,因此刻符的意义,也就是直接服务于现实需要的仪式的再记录。良渚玉器上的主体图案是“祭坛与鸟”(题图)。祭坛用单线或双条线绘制,为三层梯台式长方形,最为突出的形象是祭坛最上层的鸟形。那么鸟形图像传达出怎样的意义呢?它们既可以是图腾崇拜动物,又可以作为祖先的化身。远古时期,人类把鸟儿作为沟通天地和神祖的使者,鸟儿通过美妙的歌声传递人类的愿望;人类可以模仿鸟鸣,巫师能够听懂鸟语,还能够用人类自己制造发出乐音的玉器,与鸟和自然对话。在祖先崇拜时期,人类相信鸟儿也是祖先的化身,人类同样可以通过模仿鸟的歌唱、舞蹈,甚至化装和飞跃等行为,向神祇传达人类的愿望和信息。西方的万物有灵论、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巫术论,同样适用于解释我国原始时期人类的精神信仰。在玉器上精心雕琢刻符的主题,揭示的正是一次次举办的巫术仪式。
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青铜树上的神鸟。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2件大型青铜树都有鸟形雕塑。Ⅰ号大型神树(k2②:94)通高396厘米,树干残高239厘米。主要特征:圆座,拱形三足连接树干,顶端残缺,发掘者估计树尖上也应立有一只鸟。三层树枝,各分三个弯曲垂柳形树叉,共九枝;树枝上有九个花朵,花朵上各立一只鸟,鸟均为鹰嘴状钩喙,嘴尖有一穿孔,尾上翘,镂空,翅膀上刻羽纹;树底干一侧有一只攀龙。(图三)Ⅱ号青铜树(k2②:194)通高193.6厘米,树干残高142厘米,残损严重。残留的树枝端开有一花朵,花瓣上有一只鸟,鸟头顶中空,作鹰嘴状钩喙。鸟的造型与设置的位置都与Ⅰ号神树大体相同,如果复原,也应当是对称花朵上站立着鸟。另有二号坑出土的小型神树(k2:③272),从下树干分成三枝,树尖的果实上站立一人面鸟。[8]有学者考证,这只人面鸟可能就是文献记载的传说中的司木之神“句芒”的图像。
《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东方句芒,鸟面人身,乘两龙。”《吕氏春秋·孟春》篇记载:“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数八,……祭先脾。”依古代五行说,春季属木,孟春指春季开始的这个月,主宰之天帝是太皞,也即传说中的伏羲氏,以木德称王天下,被尊为东方之帝。辅佐木德之帝的人,叫句芒,是太皞之子,被尊称为木德之神。按照木德规定的规则,如“其音角,律中太蔟”,是指这个月的音,要用五音即宫商角徵羽中的角音,音律是十二律中的太蔟律。再比如:“是月也,命乐正入学舞。”是指这个月,帝令主管音乐的乐官进入太学教国子练习乐舞。神树作为祭祖礼仪中沟通天地上下的梯道,可示为祭祀木德之帝,上有鸟形为辅佐天帝的木神,应与管理音乐事宜有关联。恰如文中所记,这个月是乐官教授国子们练习乐舞的开始。我们曾提出,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不少文物,当是祭祀礼仪乐舞的用器。鸟形与音乐的关联意义是一个有趣的论题。如果从图腾说考证,东方人的原始信仰以鸟为标志,那么图腾的意义,也应当与人类从鸟的鸣叫获得最初的乐感,以及促进器官的发育有联系,而不仅仅是作为食物的崇拜和信仰。
由上述两例艺术考古中鸟的图像分析,可以看出,鸟儿与音乐的联系,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具有多方面的深刻文化内涵。
凤凰形象的象征意义。作为产生音乐、乐律的凤凰形象,春秋战国以后,它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如“五象”之说。《韩诗外传》卷八记载了一则故事,说黄帝即位,因没见过凤鸟的形象,乃召天老问:“凤象何如?”天老对曰:“夫凤象,鸿前鳞后,蛇颈而鱼尾,龙文而龟身,燕额而鸡喙,戴德负仁,抱忠扶义”。天老描绘了凤鸟的外貌象征德仁。接着又描绘了凤鸟的声音舞动象征时序,曰:“小音金,大音鼓,延颈奋翼,五彩奋明,举动八风,气应时雨”。天老再言凤的举止行为象征礼仪:“食有质,饮有仪;往即文治,来则嘉成。”最后归纳出凤的品格和能力:“惟凤为能通天祉,应地灵,律五音,宽九德。”由此天老又告诉黄帝,只要得到凤凰五象,就能够得到皇天降祉,永远留住凤凰了,曰:“天下有道,得凤象之一,则凤过之;得凤象之二,则凤翔之;得凤象之三,则凤集之;得凤象之四,则凤春秋下之;得凤象之五,则凤没身居之。”于是黄帝乃服黄衣,戴黄冕,致斋于宫,招来凤鸟。
《山海经》中也有多处记载,将凤凰与歌、舞,礼、乐,仁、义、德、信等联系在一起,反映了我国先秦时期实行礼乐文明制度以及哲学和道德观念,并以凤鸟的出现,象征天下祥和,太平安宁。凤凰作为吉祥物,至今依然以典雅、华贵的美感,得到人民的喜爱。
注释:
[1][美]:E·帕诺夫斯基:《视觉艺术的含义》,傅志强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823页。
[3]幸晓峰、沈博:《汉砖上的“古乐”考二题》,《文史杂志》2011年第4期第30~33页。
[4]参见幸晓峰:《汉代石刻艺术“悬璧图”》,《文史杂志》2008年第5期。
[5]参见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6]参见[英]CH·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叶笃生、杨习之译,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83~692页,第447~489页。
[7]朱乃诚:《良渚文化玉器刻符的若干问题》,《华夏考古》1997年第3期。
[8]参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227页,445页。
作者单位 幸晓峰、沈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成都)
吴 萌:成都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