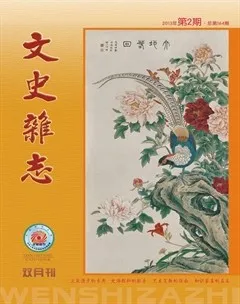傩母·地母·人母
研究中国民间神灵信仰,女娲尤其是不可忽视的极重要对象之一。下面,根据笔者对女娲神话传说以及相关民俗的理解,提供研读札记若干,以供大家参考。
一
着眼主流戏剧,可以说以女娲神话直接入戏的剧目在历史上不多,大概这跟中国神话过早步入历史化轨道以及远古女性神话被后世男性中心社会“删节”得七零八落有关。据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明清传奇有《女娲氏》“演炼石补天事”,又有明末《二十四孝》演女娲炼石补天,摄古今著名孝子二十四人之魄现身敷演。二戏作者不详,剧本今亦不存。不过,转换角度看华夏民间小戏,古老的女娲信仰还是在其躯体上烙下了不可谓不深的印迹,这尤其体现在女娲与傩母的关系上。
“以歌舞演故事”的中华戏曲,从发生学层面跟原始宗教仪式不无瓜葛。前人所谓“八蜡,三代之戏礼也”(《东坡志林》),正向我们道及此。巫傩文化在中国由来甚古。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论述“上古至五代之戏剧”时,就从古代巫觋文化角度追溯戏曲的发生,提出“后世之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并且说“巫以乐神,优以乐人;巫以歌舞为主,优以调谑为主;巫以女为之,而优以男为之”。巫是沟通神、人的中介,当其进入迷狂状态而以神之代言者的形象出现时,当其以象征性的歌舞形式作仪式化巫术表演时,庶几从中可观后世演艺中角色装扮的表演情形。《说文》以舞释巫,不无道理。傩或傩祭、傩仪是指巫师为驱鬼敬神、逐疫去邪、消灾纳吉所进行的宗教祭祀活动,其中唱的歌和跳的舞称为傩歌、傩舞,而傩戏便是在傩歌、傩舞的基础上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对于“活化石”般存在于民间的仪式戏剧如傩戏、目连戏等的研究热潮在海内外兴起,为今人重新审视中华戏曲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念,从中发掘出的诸多宝贵的民俗资料也受到学界重视。
考察民间傩戏可知,女娲正是备受崇拜的神灵之一。巴蜀傩戏中的师道戏,有泸州龙门派道坛和梁平正一派虚皇坛,后者奉太虚玉皇和三宝天尊。从其坛场布置的神图上我们看到,位于“三清”左右的神灵是伏羲、女娲。[1]在湘、黔、滇、川等地民间,演唱傩戏时供奉戏神“傩公”、“傩母”,其为伏羲和女娲。有研究者指出,“湖南自古巫风繁盛。长期以来被视为上古神话的一场古巫之战(‘炎黄大战’),导致中原九黎部落在其首领尤被杀后南逃洞庭,与以女娲为人祖的土著组成‘九黎——三苗集团’,以尤头为图腾,史称‘三苗国’。”而在湖南民间,“沅陵傩坛属‘娘娘教’流派,即以南方人祖女娲为傩神。巫师行法时多‘礼请’并赞美女巫或女神。女巫师在《和神做追究》傩坛法事中必须搬请‘东山圣公、南山圣妹、潮水洞大娘二娘三娘、五天五岳皇后夫人……’除了东山圣公(伏羲)外,其余几乎全是女巫和女神,其中南山圣妹即女娲。”[2]以“圣妹”称女娲,盖在民间有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的传说。又据高伦《贵州傩戏》介绍,不但被尊为“人皇”的“‘傩公’是传说中的伏羲,‘傩婆’是传说中的女娲”,而且傩堂法事巫书中也有二人“对天一拜成婚配”的叙事。
女娲是怎样进入傩神行列的,详情无从而知,但其作为“生”的象征具有压邪祛祟的功能,这是不言而喻的。诚然,伏羲、女娲以兄妹婚配而繁衍人类的故事流行于史,但这种神话叙事其实出现较迟。伏羲、女娲之名在先秦典籍中已提及,可是,相互间并没什么瓜葛。岁月推移,及至汉代他俩才被绘入帛画中或刻在砖石上,成为互有关联的人首蛇身的神话造型,如四川合江出土的汉代石棺上该类形象常见。这时,其关系或是兄妹(如《路史·后纪二》注引《风俗通》:“女娲,伏羲之妹。”),或是君臣(如《淮南子·览冥》高诱注:“女娲,阴帝,佐宓戏(伏羲)治者也。”),并未婚配。到了唐代,二位方才摇身一变成夫妻(如卢仝《与马异结交》诗“女娲本是伏羲妇”,即是其反映),并且形成了唐末李冗《独异志》中记载的“昔宇宙初开之时”、“天下未有人民”而女娲、伏羲兄妹“议以为夫妻”的故事。对此演变史,今天研究民间以伏羲、女娲为“傩公”、“傩母”的习俗时,是应有知晓的。
二
作为太古神话中名声赫赫的大神,女娲做了两桩惊天动地的大事:补天和造人。当年,鲁迅撷取古史创作小说《补天》,就热情地歌颂了这位炼石补天再造乾坤的大女神。结合古籍记载和民间传说来看,远古时期曾发生一场世界性大灾难。在那天塌地裂、洪水泛滥、猛兽横行、生民遭难之时,是大神女娲挺身而出,“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浮水”,由此“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淮南子·览冥》),从此天下太平。而据《列子·汤问》,女娲之所以补天乃是因为大地原本有缺陷,其曰:“然则天地亦物也。天地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缺”。此外,洪水神话是一个世界性母题,也在中国各民族口头文学中有丰富多彩的折射。透过神话看真相,“积芦灰以止淫水”的女娲其实是比鲧、禹要早得多的治水英雄,故受到万世崇敬。
女娲补天,使用的材料是土、石、芦灰,皆跟大地有密切关联。女娲造人神话见《风俗通义》等书:“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在此神话中,女娲造人凭借的仅仅是黄土,而土所表征的也就是大地。大地生长出植物,人类社会中母亲生养子女现象正与之相似。由于“类比”这神话思维的基本逻辑使然,“以地为阴性名词,图像作女人身”[3]并由此产生地母崇拜是世界性现象。民俗事实表明,女娲在国人观念中正是“地母”(Earth Mother)偶像的原型。《论衡·顺鼓》记载汉代风俗:“久雨不霁,则攻社,祭女娲。”按“社”即桑社,是古人祈生殖、祭地母的标志。《礼记·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阴气也。”《淮南子·说山》高诱注:“江淮谓母为社。”《抱朴子·释滞》则一语道断:“女娲地出。”今之学者亦肯定,“女娲既是地出,就带着庄稼神兼土地神、泥土神的性质。”[4]既然如此,古老的“女娲抟土造人”神话的实质无非是说:女娲作为人类的大祖母,她仅仅依靠自身便生养出了人类。至于《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载女娲之肠化生十神,又是一证。这里,既无作为对偶的伏羲,也无作为群偶的诸神,难怪《说文解字》释“娲”这“古之神圣女”时也肯定其是“化生万物者”。
古有“三易”之说,根据《周礼》介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三者从时代上乃分属夏、商、周。关于商易《归藏》,前人所谓“坤以藏之”(《周易·说卦》)、“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孔颖达《周易正义·序》引郑玄对《归藏》名义的解释),凡此种种,无非是在说“万物归藏于母”,强调天地万物皆由神圣的母性所生所养。区别于《周易》,更古老的《归藏》以“坤”而非“乾”开篇,自有其跟人类息息相关的发生学根基。[5]《说文》称“坤,地也”,地字“从土,也声”,而“也”乃女阴之象形,因而段注释“地”云:“坤道成女,玄牝之门,为天地根,故地字从也。”坤为土为大地,象征着母性,即所谓“地为母”(《后汉书·隗嚣列传》),“地者,元气所生,万物之祖也”,“其卦曰坤,其德曰母”(《初学记》卷五引《白虎通》《物理论》)。《路史·黄帝纪》:“黄帝有熊氏,河龙图发,洛龟书成。于是正‘乾’、‘坤’,分‘离’、‘坎’,依象衍数以成一代之宜。谓土为祥,乃重‘坤’,以为首,所谓《归藏易》也……”正因为“土,地之吐生万物者也”(《说文》)、“土者,万物之所资生,是为人用”(《尚书大传》),土地是养育万物之母,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和生产资料都来自大地,所以“谓土为祥”。
“以土为祥”,这是古代农业崇拜的体现。而在母系居主的远古时期,由于生殖崇拜和农业崇拜在初民原始思维中的重合,土地和母亲在神情意象上往往神秘互渗。“地母”崇拜成为跨民族、跨地域的多见现象,其深层缘由盖在于此。
三
神话是先民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的产物。人类起源的发生学探讨,把我们的目光引向远古“大母神” (the Great Mother)崇拜。《苗族古歌·枫木歌》有道:“假如是现在,爹妈生你我,生下就生下,有啥值得说?回头看当初,枫树生榜留,有了老妈妈,才有你和我。”这位先于人世间具体“爹妈”(两性结合)的“老妈妈”,实为人类起源传说中独自生养人类的“大祖母”或“大母神”。从中国多民族文化角度审视,女娲神话在汉族之外的许多民族中都有传播和影响。苗族生殖信仰里就有崇拜“圣母”女娲之风俗,如前人记载:“妇有子,始告知聘夫,延巫师,结花楼,祀圣母。圣母者,女娲也。”(贝青乔:《苗俗记》)
常言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古代中国以血缘宗法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中,“无子”是国人大忌。为求子嗣,为了传宗接代,民间有拜送子娘娘的风俗。这送子娘娘的主要原型,首推华夏神话史上的女娲。河北涉县中皇山有娲皇宫,民间俗称“奶奶庙”,传说此处就是“人祖奶奶”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地方。庙里有广生宫,宫里有子孙殿。庙中,神像前会摆着各种泥土或其它材料做的娃娃(人偶),专供前来烧香求子的信众们“拴”走带回家去。农历三月十八相传是女娲生日。每逢此日,方圆几百里的人们都要来赶庙会,其中求子妇女居多。求子的妇女,或向送子娘娘磕头烧香许愿,取“神药”(香灰)回家用水服下;或以红头绳在送子娘娘像前拴一人偶娃娃揣在怀里,不回头走到家里。日后若是生了孩子,便来庙里还愿,除了烧香磕头还要送三个布缝或泥土做的娃娃。每逢庙会,人山人海,香火旺盛,还有戏班艺人演唱《刘二姐拴娃娃》等节目,唱的是刘二姐因不生育而遭受婆婆白眼和丈夫虐待;求子心切的她和小姑子去赶庙会,向送子娘娘烧香磕头许愿拴娃娃的整个求子过程。由此有人物有情节的演唱不难看出,女娲信仰深深地扎根人心,老百姓对女娲在现实中的功用如送子、治病赐福、保佑发财等耳熟能详,对该女神也顶礼膜拜至极。中皇山原名女娲山。女娲在天、人、地“三皇”中位居“人皇”,因此娲皇宫所在山名“中皇”。如今,当地还办起了娲皇宫文化节,“古代的习俗,也借庙会在长期流传着”[6]。
跟许多地方称女娲为“人祖奶奶”不同,河南省西华县思都岗女娲城庙会称女娲为“人祖姑娘”。其实二者在生殖崇拜底蕴上并不矛盾,后者折射出更古老原始的“贞法受孕”或“处女生殖”母题。思都岗女娲城庙会远近闻名,“庙会上有传统祭祀歌舞,有传统服饰、步法、禁忌,称‘担经挑’,也禁忌男性参与,唱经歌《龙花经》,乃长篇祭歌。其中有一首唱及女娲庙会起源的歌,表明‘龙花会’所祭祀的主神是人首蛇身的女娲,只唱‘祭女娲,朝祖宗’而未提伏羲。庙会上,老百姓大都能讲出女娲创世治世的系列神话;部分‘宣传功’的妇女能唱出女娲治水、居住、采集、斗兽、补天等英雄神迹。‘对功’为庙会传统祭祀歌舞之一,又叫‘盘功’,庙会上相识或不相识者,以对唱方式结识并切磋功力,即兴演唱,较量女娲所赐道行及各方面的知识。‘渡船’也是庙会传统祭祀歌舞之一,内容与‘对功’相似,唱两岸风物,形式借助地方戏曲声腔、道白,双方扮作村姑和船家,以能否让人上船渡到对岸去见女娲老娘而展开对答。”这种祭祖娱神的“担经挑”(又称“担经跳”、“担花篮”)表演,在河南淮阳人祖庙(太昊陵)的庙会上亦见。淮阳人祖庙的主神是伏羲,但其主要习俗表现出强烈的女性崇拜意向,因此有学者推测,“也许此处崇拜的大神最初本是女性神女娲,后来才慢慢变成伏羲的”,“是后来男性中心社会意识渗入的结果”[7]。也就是说,对大母神女娲的信仰和崇拜,有更古老的文化根基。
以上“人祖”信仰习俗,跟古籍记载的女娲独自“抟土造人”神话相呼应,表明着女娲作为生养人类的伟大祖母的至上地位,她理当是华夏神灵殿堂中先于诸神又高于诸神的始祖神。
注释:
[1]参见于一:《巴蜀傩戏》第43页,大众文艺出版社,1996年。
[2]胡健国 :《长无绝兮终古:论〈楚辞〉与沅湘巫傩文化》,载《艺海》1998年第3期。
[3]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第56页,中华书局,1979年。
[4]萧兵:《楚辞与神话》第36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
[5]参见李祥林:《〈归藏〉及其性别文化解读》,载《民族艺术》2007年第2期。
[6]欧大年、范丽珠主编《邯郸地区民俗辑录》第190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
[7]杨利慧:《女娲溯源:女娲信仰起源地的再推测》第144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民间神灵信仰研究(一)”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四川大学教授,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
研究所(成都)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