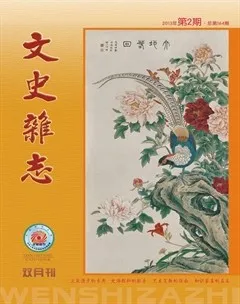延安整风运动中王实味冤案始末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反对党八股》两次演讲中,强调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要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1]毛泽东同志这一重要论断,对整风运动的方针、目的、任务和方法,作出了明确深刻阐释。为使整风运动顺利开展,中央倡导发扬民主,让群众“大鸣大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党内干部中存在的党风问题提出意见和批评。1942年3月5日,中央主管整风运动常务工作的康生在延安大礼堂召开干部大会,对整风运动作了动员报告,强调“要发扬民主,让群众大胆讲话,提倡出墙报,批评领导,对错误观点不要立刻反驳,也不要加以压制。”[2]党的号召很快得到党内外干部群众响应,尤其是知识分子和新党员反响更大,一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由此展开。
延安知识界、文艺界积极贯彻中央整风指示精神,走在整风学习前列。他们在各种学习会上提出批评和意见,不少人还通过墙报、小字报、漫画、打油诗,或在报刊发表文章,提出各种批评意见。1942年3月,《解放日报》文艺副利上接连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等杂文,反映对当时延安生活中存在的某些问题的不满和意见,对一些老干部弃旧娶新,官僚化作风以及生活待遇等级制,包括衣分“三色”(高级干部深蓝色斜纹布、中级干部灰青色平布、基层干部黑色土布)、“食分五等”(小灶、中灶、大灶等),进行了尖锐批评,立刻在延安政治生活中激起强烈反应。“王实味是这当中的突出代表人物,他写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刊3月15日《谷雨》刊物),又连续在研究院办的《矢与的》壁报上写出《我对罗迈同志(李维汉,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坐镇主持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在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灵感两则》,攻击李维汉等同志,言词尖锐,冷嘲热讽,而且有片面性,把抗日民主根据地描绘成‘肮脏和黑暗’的封建专制社会,主张文艺家‘首先针对自己和我们营垒进行工作。’一时间把延安都轰动了。”[3]
文艺家们的这些批评,在延安一些领导人中引起很大反感,有人很快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批评;还有在内部简报、墙报上予以责难。“有的领导同志从前方回来发了脾气,说我们在前方打仗流血,王实味这样的人却在后方这样讽刺挖苦我们的领导干部,攻击我们的党。”[4]对此,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他在夜间提着马灯去看了王实味等人在墙报上的批评文章,但并未表态。当时他并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也没有把王实味看做是敌人。他只是让秘书胡乔木找王实味谈过两次话,给后者写过两次信。信中有如下一段话:“《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意见,再次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立场。”[5]这说明毛泽东同志对王实味等人是看重的,所以要其注意提意见的立场和方法,不要走偏方向,颇有爱护之意。4月初,毛泽东同志在所主持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上,谈到整风中文艺界一些人提出的批评意见时说:“他们的批评意见确实此较过分一些,个别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较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6]但仍称王实味为同志,并提醒政治局同仁,不要轻易对过分批评者上纲上线,强调思想“落后分子”不都是反革命,提出要“争取落后分子”。这再次说明当时王实味的问题,仍属于思想问题。
从4月初至5月底,王实味所在单位中共中央研究院,对王实味展开批评,开大小会70余次,且问题不断升级。“开始还是作为思想问题来批评。批评会议持续到5月下旬时,有人揭发王实味曾同‘托派分子’有过联系,在上海时帮助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传》中的两章。(1929年,王实味在上海从事翻译工作期间,同托派分子王凡西有过接触,帮助他们翻译过《托传》中的两章,没参加‘托派’组织。1940年他在延安已向党组织作过交代。)这时,康生插手了,他决定彻底追查王实味与‘托匪’的关系,使问题成为敌我矛盾;并把同王实味接近的四位同志,也一起定为‘五人反党集团’。”[7]6月11日,丁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文章,称“王实味有‘托派’思想”。6月15日至18日,延安文艺界举行座谈会,批判王实味,并一致形成决议,认定王实味在政治上是敌人。
此时,毛泽东同志开始改变对王实味的看法。在6月19日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赞同文艺界座谈会决议的意见,指出:“现在看来,王实味的有系统不是偶然的。这个人多半是有组织的进行托派活动,抓住时机,利用矛盾,进行托派活动,向党进攻。”[8]10月23日,中共中央研究院党委作出决定:开除王实味党籍,认定王实味从1929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有停止过“托派”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托派”分子。1943年4月,康生下令正式将王实味逮捕入狱。
1945年,党对在“整风运动”中错定为政治问题的大多数同志做了改正,但王实味仍戴着“反革命‘托派’分子”帽子,继续关押在监。1946年2月,康生等人再次作出“王实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1947年6月,关押王实味的山西兴县监狱被国民党飞机炸毁。晋绥公安总局请示中央社会部,对王实味如何处置。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作出批示:将王实味秘密处死。1947年7月1日夜,王实味被秘密杀害,置于一口枯井中掩埋。据杨尚昆回忆,“处死王实味,事前毛主席不知情。他知道后,拍着桌子向林伯渠同志要人(按:林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9]
王实味属于受五四民主和科学思想影响,满怀乌托邦社会改造梦想,从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一代左翼知识分子。1926年,他时年20岁时就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离开北京到上海,依靠译著获取稿酬维持生计;期间,同原北京大学党支部里的刘莹结婚,先后育有两女(但长女夭折)。1937年10月,王实味安排妻、女返回刘莹老家长沙后,只身抵达革命圣地延安,开初在“鲁艺”学习,继被分配到陕北公学任第七队队长,几个月后调出版局,从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翻译。1938年5月,他被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洛甫(张闻天)指名调马列学院编译室工作,同年12月调中央研究院文学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享受中灶伙食,月津贴四元五角,着中级干部服待遇)。王实味个性傲诞,颇具书生气,看不惯学院某些领导的官僚作风,尤其对陈伯达等谀上压下种种表现不满,与之关系不和。但他对张闻天、王学文、范文澜等领导却十分尊重。1938~1942年,王实味译出《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雇佣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及《列宁全集》18卷中的两集等马列主义理论书稿达200万字。“文革”后,王实味妻女积极为其冤屈申诉;曾在延安工作知情的同志亦通过不同形式、途径为王实味案的平反积极奔走。直到1992年,王实味在蒙冤50年后,才终于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平反昭雪。
注释:
[1]《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人民出版社版,第814页、829页。
[2]转见《新华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3][4]见《党的文献》,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5]转见《百年潮》2002年第12期。
[6]转见《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中华文艺出版社版。
[7][9]见《杨尚昆忆延安整风》,香港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
[8]转见《中共党史研究》,华夏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作者:四川省作协(成都)会员、四川公安文协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