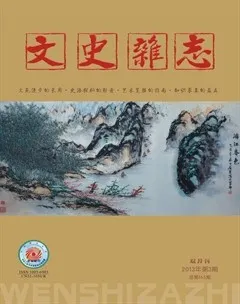成都新出石犀略考
“神兽”在天府广场出土
上世纪的1969年,成都城市建设的步伐开始加快,一阵风似地拆除了“皇城坝”上许多前代建筑,开辟道路,修建大楼。这个皇城坝上,原有五代蜀宫和明代蜀王府的旧址,清代就地改建成贡院,作为“为国求贤”的地方。在贡院范围内,照例有一座中心建筑物“明远楼”,高出大小考棚之上,起着号令和监视整个考场的作用。此时明远楼也被推倒,1973年在其东面开始修建电信大楼。就像前清各地贡院都要修建明远楼一样,全国许多城市的电信大楼顶部,都要修建“钟楼”供老百姓瞻仰,以便知道时间;因此1978年电信部门这一工程建成后,一座钟楼就稳坐在电信大楼的顶上。那大钟是上海钟表厂生产的,平均误差一天只有30秒,民间报时的精度完全合格了。此后一二十年间,每天沉浑的钟声传入寻常百姓家,提醒城内居民什么时候该起床,什么时候该煮饭,成为老成都人的美好记忆。
老成都人还记得另外一桩事,1973年11月修建电信大楼的长话机房,在开挖地基时,曾经发现地基深处埋着一个巨大的石兽。1987年出版的《成都城坊古迹考》记有此事,指出那里原是前蜀宣华苑的瑞兽门所在:“解放后修建电讯大楼时,掘得一石狮,则苑之瑞兽门当在斯。因石兽甚重,未能移出,而施工又甚迫促,乃留于原处,其上即为大楼基脚。”此书2006年再版修订时,这段文字载于《杂考篇》第二章“秦汉以后史迹”第七节“摩诃池与宣华苑”中。当时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的老先生们推测,此兽既然在蜀宫宫门附近,就应该是个石狮了。
按照近年成都市城市改造规划,决定将坐落在天府广场东北角的电信大楼拆除,修建“天府大剧院”。运行了32年的钟楼大钟,先是老化不响,后是走走停停,而且民众也并不需要瞻仰它来获得时间信息,实该下课了。于是在2010年10月,将包括钟楼的电信大楼一拆了之。不过,当10月下旬地基开挖到4米多深处时,37年前曾经现身的石兽露出了冰山一角,彼时限于条件不能挖掘,此时却有了现代化的先进手段,完全可以获知庐山真面目了,从而引起众多媒体的关注,争先恐后深挖新闻材料。经过一番打听,媒体很快找到了当初负责修建电信大楼的四川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施工股技术员车凡英。这位先生对当年地基打桩时的情景记忆犹新。他记得那时有一根建筑桩打到石兽的肚子上,遇到很大阻力,挖开一看,原来是一块特别巨大的石头。后来挖开直径2米的大坑,只见四脚朝天的石兽体量较重,却也无可奈何。当时许多人都认为那是一头石象,因为只有象才那么大。原工艺设计负责人林昌海也回忆起当时情景:由于成都的地层比较松软,高楼的地基桩一般要打七八米深,但打到石兽处,只打了4米左右,再也打不进去了。他看见那石兽“鼻子很长”,估计和真象差不多大。施工方赶紧请来文物管理处的专家现场勘查,因为石兽躺在深深的坑底,难以详细观察,又限于70年代的技术条件,觉得此物重量太大,挖掘和起吊运送都很困难,只能依照《文物保护法》就地回埋。当时的直观判断,那并不是石狮,而是一头石象。
可是,依照当年施工队原助理工程师王顺清的回忆,1971年修建电信大地下室时,发现的应该是一匹两米多高的石马。马头朝南,马尾朝北,身长两米多。所以除了石象以外,还有一种石马的说法。当年应邀到工地勘察的成都市文物管理处苟治平说,1973年他前往施工现场,确实看到基坑里挖出了巨大石兽,但侧身卧地,右边半截仍在沙土里,只见左边足部和腹部,没有条件看清头部,具体是狮是象还是马,“没法准确判断”。
媒体记者推想,由于《成都城坊古迹考》记载过石兽的事,可能编书者还掌握着更加详细的信息,可是原先编书的老先生至今皆已作古,而笔者曾经参与过此书的再版修订,因此2010年底成都电视台就对笔者进行了采访。我的推测是用于镇水的石犀,民间俗称石牛,因为古蜀有这种治水民俗,千百年遗风未息。明末清初张献忠“入川屠蜀”,皇城坝的前代宫廷破坏得十分彻底,钟楼地下的石犀,很可能在那时被埋于地下。笔者的这一判断,居然就言中了。
2012年12月25日,经过考古勘察程序,“天府大剧院工程”正式开工建设,急须将基坑中的石兽吊装出土,以便施工。到了2013年1月9日,深居地下数百年的石兽,在一台起重机的操作下,终于吊上地面,翻了个身。经过清理得知,石兽为整块红砂岩雕刻而成,身长3.3米,宽1.2米,高1.7米;重约8.5吨;马嘴象耳,腰背有沟,臀部浑圆,四肢粗壮,右侧身上刻有卷云纹和其他印迹,左侧有一些新近凿痕,显示出犀牛的形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毅鉴定为“石犀”,认为这件大型圆雕保存得相当完整,“是填补中国雕塑艺术史的重大考古发现”;前来考察的文物专家皆认同此说,并认为石犀是秦汉或更早的文物;92岁的苟治平更是兴奋不已。
新闻媒体不失时机地进行了大量报道,形容出土的石犀是一种“神兽”,与金沙“太阳神鸟”等量齐观。有关方面把石犀搬运到金沙博物馆公开展览,以满足成都市民的好奇心,同时吸引来许多外地来客。
出土石犀的来龙去脉
2013年1月石犀出土时,考古人士进行了一系列挖掘清理工作。在5个探方的揭露下,明确了天府广场地层,从近代直至战国时期较为完整,有灰坑、灰沟、城墙、角楼、排水沟、房屋、水井、建筑台基等遗迹,各个时期都有出土器物显示出较为系统的连续性,包括瓦当、地砖等建筑材料;碗、盆、盏、灯台、釜、罐、碟、纺轮等生活用品;还有个别佛像残片。早期有高约30厘米的战国陶罐,小口大腹。石犀处于第七层的灰坑中,根据此层出土大量蜀汉时期精美瓦当和铺地砖可知, 时代约为蜀汉末期至西晋。那时石犀所处的地方有着规模巨大的建筑物,或为蜀汉宫廷之一,但这些建筑在西晋时期即被彻底毁掉。根据地层学判断,石犀建立年代应在西晋以前;而从其造型古朴,刻纹粗犷简练,不像东汉以后那样精致,故其实际制作年代应早于东汉,推测制作年代上限可到秦汉时期。晋代以后,这一石犀沦为路边的闲置物,在它身上还发现了磨刀的痕迹。
由于刚出土的石犀身上存在多种病害:一是多处缺损;二是右侧前后腿有不同程度的表层空鼓;三是两侧都有片状剥落;四是表面风化;五是土锈结壳;六是粘有混凝土;七是表面泛盐;故在初次论证会上,专家们研究了一些保护和利用的方案。首先对石犀进行预包装,进行临时处理,再安置底座,最后整体装箱进行搬运。
关于蜀地推崇石犀的来历,最早可以追溯到创建都江堰的李冰。《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十引西汉扬雄《蜀王本纪》提及,成都“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枚在水中,以厌水精,因曰石犀里也。”表明两千多年前蜀守李冰曾制作了5个石犀,两个在成都府中,一个在市桥下面,两个在渊水里。由于《蜀王本纪》已佚,这里摘抄的文字是否可靠,存在疑问。现存的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记李冰“外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溪于江南,命曰犀牛里。后转置犀牛二头:一在府市市桥门,今所谓石牛门是也;一在渊中。”表明李冰制作的石犀确是5头,由于李冰在成都城区开了一条石犀溪,所以有了“石犀里”或“犀牛里”的地名,在水里的石犀只有一头,并非两个;但市桥门那一个确实存在。据这些早期记载,李冰在修建了都江堰干渠以后,就沿河安置了一些镇水石犀,其中放在成都城南的至少有两个,一个在渊水中,一个在市桥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抄录上述两种材料,记成都“西南石牛门曰市桥,吴汉入蜀,自广都令轻骑先往焚之。桥下谓之石犀渊,李冰昔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渠于南江,命之曰犀牛里,后转犀牛二头在府中,一头在市桥,一头沉之于渊也。”他的意思是成都府有两个石犀,就是渊水和市桥这两个。
后来在石犀所在地出现了“犀浦”的地名,意为沉犀之浦。《旧唐书·地理志》说:武后垂拱二年,分成都县置犀浦县。唐代《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一载:“犀浦县,本成都县之界,垂拱二年分置犀浦县。昔蜀守李冰造五石犀,沉之于水以压怪,因取其事为名。”宋代《太平寰宇记》记犀浦县亦云:“周垂拱二年,割成都之西鄙置,盖因李冰所造石犀以名。” 此县共辖20乡,县境东到今成都杜甫草堂和百花潭一带。书中记华阳县:“杜甫宅在西郊外,地属犀浦县。接浣花溪,地名百花溪。”杜甫《梅雨》诗亦有“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即咏当地之景。宋欧阳忞《舆地广记》认为:“犀浦县属益州。秦时李冰作石犀以压水精,穿石犀渠于江南,命之曰犀牛里。县取此为名耳,不在其地也。”说明犀浦县城那里并没有李冰的石犀,不过渊水倒是存在,因此就叫“犀浦”,其地应接近百花潭,似即所谓“渊水”。犀浦县治今为郫县犀浦镇,旧《郫县志》言 “县治仪门下穿洞,直通犀浦,极深,敞高可十尺许。每夜月中天,洞中曙光如昼,古谓之明月洞。”说明李冰石犀在唐宋时仍有遗迹。
关于李冰所建市桥的地理位置,《华阳国志》谓:“直西门郫江中冲治桥;西南石牛门曰市桥,下石犀所潜渊中也;城南曰江桥;南渡流曰万里桥;西上曰夷里桥,上(亦)曰笮桥;桥从冲治桥西出,折曰长升桥;郫江上西有永平桥。”可见市桥与渊水两地比较接近。《太平寰宇记》云“市桥在州西四里。”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成都七桥考》说:“秦少城正南为石牛门。门外跨郫江有桥,为市桥,为当时各族人民市易处。汉建益州,称为州市,谓一州最大市也。《寰宇记》卷七十二云:‘市桥,在州西四里。’又引李膺《益州记》云:‘汉旧州市在桥南’。《华阳国志》云后汉大司马吴汉征公孙述,述妹婿延岑伪遣鼓角,麾帜渡市桥挑战,汉兵争观,延岑纵兵出汉军后袭击,大破之,即此桥也,七星桥之五。郑樵《通志》谓古市桥‘今曰金花桥’。考石犀渊当即今之王家塘;石牛门当在今宁夏街东武担山与文殊院之间,去金花街、五福桥不远。宋代犹能知其处,今难确定何点矣。”明代天启《成都府志》亦云“市桥,即今金花桥也。”《成都城坊古迹考》说:“1984年修西干道时,在同仁路南口东侧地下3至5米,发现粗大木桩,排列如梅花桩形(南北向),又在金河街发现汉唐遗物及系船桩,可证明市桥遗址在此。”表明李冰石犀,本立在今同仁路南段。
唐宋记述中也有李冰石犀踪迹。杜甫大概见过,故有《石犀》诗:“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滥不近张仪楼。”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说,他曾看见石犀庙里的一个实物:“石犀,在李太守庙之东阶下,亦粗似一犀。”但因年代久远,断了一只脚。“一足不备,以他石续之,气象甚古。”他的《杂咏》诗云:“石犀庙壖江已回,陵谷一变吁可哀。即今禾黍连云处,当日帆樯隐映来。”可见此庙本来距江水不远,但南宋时河道已经变成耕地了。此庙又称石犀寺、石牛寺、龙渊寺,汉魏之际江边曾出土石犀,蜀人因此立庙,祭祀李冰。唐代改名空慧寺、圣寿寺。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王士性《入蜀记》也说在寺里见到了实物:“一石立殿左,牛形,又似未琢成者。或云李冰所作。”《全蜀总志》言“李冰五石犀,在成都府城南三十五里。今一在府治西南圣寿寺佛殿前,寺有龙渊,以此镇之。一在府城中卫金花桥,即古市桥也。”曹学佺《蜀中广记》说:“今寺殿阶左有石蹲处,状若犀然。”这一风化了的李冰石犀,民国初年轮廓犹存,身高七八尺,大于常牛,其首向西;那时四川省立第一中学在此成立,还一度考虑名为“石犀中学”。后来抗战时期学校驻军,官兵们还利用这一风化了的大石,堆土修建旗台,每天升旗。到了1952年,石犀已剥落得不再成形。后来初八中(今28中)修建教室时,石匠们便将它劈为石条,砌筑阶沿。于是成都唯一的李冰遗物,就此消失!
《成都城坊古迹考》说,今西胜街原前清右司衙门那里,民国2年(1913年)改成第二小学堂,在平操场时在土里又挖出另一个石犀,身上刻有几十个字,文史馆馆员饶伯康曾将拓片给刘师培看过,认为是镇水之物。据当时考证,这两处石犀的连线,应为李冰所开郫江故道所经。不过,这一石犀应该是汉代人的仿制,可惜文字拓片连同馆员笔记,“文革”后文史馆里已经找不到踪迹,无从查考。由此得知,汉代已有仿制石犀的习俗存在。天府广场出土的石犀,也许就是那时的制品之一。
石犀应是滨江而立
现今天府广场出土的石犀,气象仍然相当古朴,有些专家疑为秦汉时代的仿制品,是个正确的意见。既然如此,石犀就该站立在江边,为什么现身于离开锦江较远的天府广场?这一点,需要用“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沧桑变化来解释。成都地区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地面坡度为千分之四,夏秋暴雨集中向东南流,因此需要垂直于地势走向、横向开渠排洪;故自古城南一带就有许多河道存在,直至20世纪前叶,皇城坝那里还有围绕“皇城”的御河和另一条金水河,只是在70年代“备战”的口号下,被填平改造为人防工事而已。
在唐宋记载中,除了李冰修建的“成都二江”,还有流过唐代大慈寺南面的解玉溪,以及宋代城区的四大沟脉。明代《蜀中广记》引《通志》云:“解玉溪在华阳大慈寺南,韦南康所凿也。溪中细沙,可以解玉。”流沙河有篇回忆文章说:“现在站在布后街西端,左拐是梓潼桥正街。千年前的唐代,此街是一条河。河床出产优质金刚沙,可以解剖玉,故名解玉溪。河水是从千年前当时的西北城角水洞子入城的,流经青龙街、西玉龙街、玉带桥街、玉沙街、东玉龙街、桂王桥街,蜿蜒流到此地,仍向东南流去。又经东锦江街,流过当时大慈寺南门前,经磨房街入内江故道去。”1996年台湾邱永汉集团准备在大科甲巷开发百货业超市,即今伊藤洋华堂所在地,在开挖地基时发现了晚唐至宋代的下水道,其规模不小,全是用秦砖汉瓦修建起来的拱券式涵道,高宽都在一米以上,笔者曾前往参观,在其中可以直立行走。据考古人士清理研究,认为下水道是利用淤废的解玉溪河道而建。后来在北新街挖地基时,又发现了同一下水道的另一段。将这两处连成一条线,可以恢复解玉溪水道的原址,距离今天天府广场并不远。唐宋时期的地方官,对于城区水道的管理颇为尽力,宋代席益《淘渠记》言:“白敏中尹成都,始疏环街大渠,其小者各随径术,枝分根连,同赴大渠,以流其恶。”白敏中曾经新开大渠,就是后来的金水河,离开天府广场更近。如果将时间倒退到李冰时代,当时新开的石犀溪,很可能就在今天的天府广场附近。所以现在的广场,古代说不定横着一条大河,出土的石犀,那时正在河边守望。不知何年何月,一场特大洪水冲塌了河岸,石犀就侧身滚进河底,深埋至今。
李冰留下的石犀镇水习俗,后世一直继续着。有些人工渠道沿线,往往有类似的石雕存在,王士性《入蜀记》云:“成都故多水,是处以石犀镇之。城东有石犀九枚,立于江边,可按。”明正德《四川志》记有:万年堤“三百余丈,置石人、石牛各九,以镇水恶。”不过后世的石雕已不是犀牛状,而是水牛形了。清嘉庆《华阳县志·金石》称:“今惟余石牛一头,余无存。”现在望江楼对岸有一条石牛堰,得名就因抗战期间在九眼桥一带挖防空洞时,曾经挖出石牛。至今望江公园河滩上还陈列着两条石牛,均为附近出土。
关于犀牛灵异的传说
旧时民俗中石犀镇水的来由,基于古人的特殊信仰,觉得犀牛有一种分水能力,故号灵犀。因为犀牛的主角长在鼻子上,下水游泳时,如果速度够快,水波会向两边明显分开,好像它主动地劈波分浪一样。《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十录《南越志》说:“巨海有大犀,其出入有光,水为之开。”又录晋代刘欣期《交州记》:“有犀角通天,向水辄开。”所谓“通天犀角”十分神圣,葛洪《抱朴子·登涉》甚至说:“得真通天犀角三寸以上,刻以为鱼,而衔之以入水,水常为人开。方三尺,可得气,息水中。” 三国时吴国万震《南州异物志》说得更玄:“犀有特神者,角有光耀,白日视之如角,夜暗掷地皆灿然,光由中出,望如火炬。欲知此角神异,置之草野,飞鸟走兽过皆惊。”《太平御览》又录《晋书》:“温峤还武昌,至牛渚矶。云其水多怪物,遂燬犀角而照之,见奇形异状,或朱衣,乘车马。峤梦人曰:‘与君幽明道别,何苦相照?’”把犀牛角点燃,居然可以照见水中的牛鬼蛇神。按这样说,如果让犀牛站在岸边,任何水精当然就不敢兴妖作怪了。因此,石犀立在河边镇水,就是非常自然的事。
传说中的犀牛不但能够分水,而且还能分树。《太平御览》所录《林邑经记》说越南有这种犀牛:“犀行过丛林,不通,便开口露齿,前向直指,棘林自开。”还有一种使鸡害怕的犀角,名为“骇鸡犀。”《战国策》云:“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说楚王。楚遣车百乘,献骇鸡之犀、夜光之璧于秦王。”这种犀角就是通天犀角,《抱朴子》说:“通天犀角有白理如綖者,以盛米置群鸡中,欲啄米,至则惊却,故南人名为‘骇鸡’也。”这种通天犀角还有解毒作用。
实际上,犀角确是一种名贵中药,价格不菲。传为春秋时陶朱公《范子计然》说过:“犀角出南郡。上价八千,中三千,下一千”;无论使用何种货币单位,见到这种天价也会大吃一惊。北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十七引日华子之说:“犀角,味甘、辛。治心烦,止惊,安五脏,补虚劳,退热,消痰,解山瘴溪毒,镇肝明目,治中风失音,热毒风,时气发狂。”书中又指出,犀“有鼻角、顶角,鼻角为上。大寒,无毒。主风毒攻心,热闷,痈毒赤痢,小儿肤痘,风热惊痫,并宜用之。”书中还举出犀角能够避尘的实例:“石驸马保吉知陈州,其州廨一皆新之。每毁旧屋,则坐于下风,尘自分去。人皆惊怪之,盖其所服,带辟尘犀也。”犀牛角居然还有净化空气污染的功效。
由于通天犀角剖开后,可以看到里面有一条白线似的纹理,贯通角的首尾,被古人看作为灵异之物,便用“灵犀”一词来赞美它。唐李商隐《无题》诗“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名句,就采用了这个典故。可惜天府广场千年石犀的角已经不复存在,未免有些令人遗憾了。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