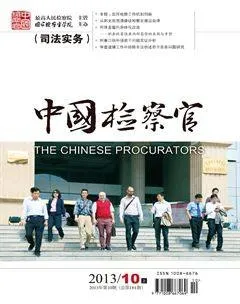正义该怎样实现
周克华案件的情节像落入俗套的警匪片的现实版。黑老大恶贯满盈却手段狡猾,屡屡侥幸逃脱让警方束手无策,编导们往往以警察掏枪射出正义的子弹结束罪恶的生命作为故事的结局。这是一种较具有感染力的艺术处理手法,既简单直接又酣畅淋漓,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对正义的期待。反正歹徒是该死的,手刃也好,审判也罢,不让他活着是最基本的正义,正如《让子弹飞》中姜文只是给“黄四郎”在九种死法中选择了最能让观众击节叫好的一种。艺术塑造往往是非黑即白,非好即坏,英雄百分之百是英雄,狗熊百分之百是狗熊,但是当今微博时代是怀疑的时代,公众的思考要复杂得多,譬如公众一直质疑倒下的是不是周克华本人,人们甚至可以质疑这个“周克华”是否具有从轻情节,这个正义的警察是否有公报私仇之嫌,你是否剥夺了人家的辩护权,对他开枪是否有必要等等。要说服大家,那好,公布真相来,正义要“看得见”。这里面不光有个“该不该死”的问题,还有个“该怎么死”的问题。前者是个实体问题,后者则是个程序问题。
英美人有一句众所周知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这句话上半句指的是实体公正,意思是案件不仅要处理得正确、公正,并完全符合实体法规定和精神,下半句指的是程序公正,意思是案件还应当使人感到审理过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这里面存在一个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平衡的问题。正义是我们每个QiayaEG6S/0P+1rEzPCpdZsrNxKTpkNvH6WJ+GyRT+s=法律人的追求,而达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平衡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很高的境界。有时候,我们可能担忧过于苛刻的程序设置和操作,会使实体正义得不到伸张。但是,对于一个长期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群体来讲,对于一种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没有杜绝的办案方式来讲,无论怎样强调程序的独立价值都不算过分。事实上,在程序正义得到尊重和人权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实体正义都会实现得更好,从这个意义上讲,程序正义就是实体正义。作家萧乾在《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一书中讲到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就是很好的例证。“那帮罪行累累、十恶不赦的纳粹头目就是把他们碎尸万段,也不为过。然而纽伦堡战犯审判的主持者好象在表演耐性,一点也不急于为那些恶魔定罪,把他们送上绞刑架。听说纳粹德国投降时,除了已自我消灭的希魔,共抓了二十万名大小头目。花了足足半年时间经过初审,逐步缩小惩办范围,所以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才开始正式开庭审判,次年八月才结束,九月三十日及十月一日两天,分两批宣判并执行。统共竟花了二百一十八天!我当时所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法庭不但准许犯人作充分的自我辩解,并且还为他们每人各聘有律师出庭辩护。据我所知,凡在纽伦堡被判刑的,至今没有一个需要改正或平反的,也没有听说过关于当时量刑不当的烦言。”现在的网络时代,还是有人喜欢以狂欢的方式把一个人送进监狱,还是有人热衷以运动的方式打黑或是反腐。
事实上,在纷繁芜杂的生活中,作为实体正义未必能够确保实现,那句英美人法律格言的上半句“正义应当实现”也是一种理想化的说法。相反,过分强调实体正义的实现未必是理性的,正如“命案必破”可能会导致刑讯逼供的滋生,以至于出现冤假错案。关于这句法律格言的另一种说法是:“正义可能没被实现,但是必须看起来已经实现了。”这种说法似乎不好理解,但更有法律理性。它的意思是实体正义我们没法保证,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在我们在程序正义上做到了最大的努力;反过来,只要是我们尽职尽责地处理案件,做到程序公正,其结果就应该被认为是正义的。就像医生对死者尽到一切可能去救治但没能挽回他的生命,要让他的亲人明白:“我们尽力了。”尽管这样于事无补,但是亲人心理上会得到一定的慰籍。这或许在司法实践中给我们一定的启示,很多案件我们是无法找到真相的,或者说找到真相却不能用证据固定下来,或者是受伤害的人永远得不到补偿,或者争讼的双方都认为实体上得不到满足,那么我们需要用程序的公正来宽慰受伤的灵魂,至少让他感觉到司法是公正的。尤其是在处理陈年积案或是信访案件时,在我们离开上帝的帮助没有能力也没有可能还原历史、纠错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把我们实现正义的方式让人看得见,也让人明白:我们尽力了。
很久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实体和程序是皮和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之焉附”,从而忽略了程序的独立价值。这次刑诉法的修订,是我国30余年法治进程的一部分,尤其在保障人权和确立程序的独立价值上有很大进步,我们期待它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尽管我们还会有很多无奈,例如会有媒体改变司法、信访支配司法的情况,使得“实现正义的方式”多少显得有些尴尬,但毕竟我们又往前走了一步,检察官们定会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