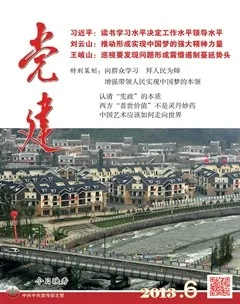醉在红楼
五月槐花香。一树树立在夏日里,绰约,繁盛。
睹花思人。一年前,这世上爱花的周汝昌老人离开我们远去了。
一年间,他的遗著《红楼新境》、《寿芹心稿》得千万读者用心品赏,其里程碑式的代表作《红楼梦新证》增订纪念版也如约问世。
心血凝就的一字一句,告慰着老人“为芹辛苦见平生”的执著,也延续着老人永不凋零的学术生命。
“醉红”晚境:
“九五光阴九五春,荣光焕彩玉灵魂”
得识周汝昌,是在其生命的最后两年。
2011年年初,笔者致电周宅,向素未谋面的周老约稿。仅两天后,其女伦玲便发来了老人口述、她记录整理的文稿。近两千字,娓娓讲述大观园联句内蕴,字字珠玉,句句鲜活,几无可删改之处。
于是,便有了后来数次登门拜访。
自1989年始,周汝昌便居于京城红庙一套三居室。这里的简朴,引发过很多来访者的感喟。破旧、寒酸,既无丰富的藏书,更无奢华的摆设。但和老人交谈片刻,便有气象万千、陋室生辉之感。那是久经岁月淘洗之后沉淀的智慧与性情,是病弱之躯关不住的活力与灵动。
谈研红新得,忆人生浮沉,析红学现状,时年九十有四的老人和笔者一聊便是两个多小时,兴奋处眉飞色舞,激愤时言语铿锵,对所喜所憎丝毫不加掩饰。
就在那次交谈中,老人兴致盎然地提到了正在写作的新书。
这该是怎样艰难的“写作”——1975年,周汝昌因用眼过度左眼失明,右眼则需靠两个高倍放大镜重叠在一起方能看书写字,写出的字大如核桃,经常串行。近几年来,右眼也近失明,只能依靠口述成书。
不能亲自查阅资料,无法随时增删修改,对老人的学养和脑力堪称极大考验。然而,他从2000年至今仍出版新书十余部,且不断有文章面世。
“很难想象父亲脑中装了多少东西。精神好的时候,他能六七本书同时进行,讲一本讲烦了,就叫停,马上讲另一本。”伦玲大姐告诉笔者,周老的三女二子皆是其助手,每人手里都有两三本书在整理。
即便如此,老人仍深感遗憾。“我目未全盲时,写作《红楼艺术》一书,从出版社拍板到交稿,只有一个半月。那种工作效率,恐怕今天人们听来都不肯信。”
2012年4月,老人赶写完《寿芹心稿》,身体明显更不如前。儿女“强迫”他卧床休息,他无奈,便把新出版的《红楼新境》放在枕边,不时拿起摩挲,默默无语。精神稍好,他便要求子女念新书给他听,还口述了一本刚构思好的新书大纲要求子女记下,书名暂定《梦悟红楼》。
5月300f7cHjB0xheQaElwvOxiuo4r6MzpBSb1llUZIl2tVQc=日,神色安详的老人叫来儿子周建临,“心痛中赋诗”一首:九五光阴九五春,荣光焕彩玉灵魂。寻真考证红楼梦,只为中华一雪芹。
谁能料到,这竟是老人最后的遗言。转天,老人便撒手人寰。
他燃生命为烛,祭奠雪芹;而今,烛泪尽,情未了,人已去,空留一段“高山流水”之余韵,隔时空深情唱和!
曲折平生:
“悬真斥伪破盲聋,探佚专门学立宗”
上世纪20年代,天津咸水沽镇一户普通人家。一位早慧孩童好奇地翻开了母亲时常捧读的一本古书《石头记》。难解的书名和篇首大段“作者自云”,令他草草扫过几眼便丢下,未曾挂心。
这便是周汝昌。那时的他怎么也想不到,此书竟会冥冥中与他重逢,并左右他跌宕浮沉的整个人生。
1947年,就读于燕京大学西语系的周汝昌收到四哥祜昌寄自家乡的信函,托其查证一篇关于曹雪芹的文章。四哥研究《红楼梦》多年,为助其一臂之力,周汝昌遍查燕京大学图书馆,果有新发现。勤学善思的他不愿埋没新知,便撰文《曹雪芹卒年之新推定》,发表在天津《民国日报》副刊。
不久,一封信函飞至周汝昌手中,署名赫然为“胡适”。原来,胡适在友人推荐下通读此文,颇为赞赏,当即来信。周汝昌自是兴奋。他仔细研读《红楼梦》,很快不能自已,“发现了一片大天地”。
伴随着和胡适的书信往复、探讨切磋,1953年,煌煌40万言的《红楼梦新证》出版。此书不但发掘考证了海量史料,并且把对作者身世的研究与文本本身相结合,开创了不同于“新索引派”的研究理路。在今人眼中,它仍是“红学研究中绕不开的经典之作”。
短短一年间,此书3次再版,甚至被毛泽东圈阅品赏。但一场借红学而起的政治纷争正暗流涌动,周汝昌自然被卷入其中。受冷眼、被批判,下放“五七”干校……之后十余年光阴就此蹉跎,一直到1970年,方在周总理关怀下调回北京。
安顿后第一大事,便是修订《红楼梦新证》——厄境中他从未停止思考,太多心得急于表达。
青灯黄卷,昼夜奋笔,修订版《红楼梦新证》竟由初版时的40万字增至80万字。然而,书未出版,他竟累至双眼视网膜脱落,经手术治疗,右眼视力仅存0.01,左眼失明。
二十余岁起便因病逐渐失聪,现又几乎目不能视,对一个爱书人而言,这该是怎样的苦不堪言?在无声且黑暗的世界中,周汝昌反倒心无旁骛,相继出版了《献芹集》、《石头记鉴真》、《红楼夺目红》等数十本著作,并屡发新论,将红学构建为曹学、版本学、脂学和探佚学四大范畴。2004年,他倾注多年心血的《石头记会真》出版,被认为是其红学研究的又一高峰;同年9月,精校本《红楼梦》(《八十回石头记》)问世,被评价为“第一个最接近曹雪芹原书原貌的真本善本”,再次震动红学界。
痴真品性:
“万口齐嘲玉,千秋一悼红”
精研一生,周汝昌并不认为自己已读懂了《红楼梦》。
在他看来,《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更是“中华文化之学”,包含总结了我们民族的文史哲和真善美。
字字句句,见得一介书生的“痴”“真”二气。
“他可以忘记自己的生日,却年年给曹雪芹过生日。”伦玲大姐说。
“周先生年轻时在我校执教,有天出门,见一小饭馆名曰‘潇湘馆’,便含怒质问店主:怎可亵渎林妹妹之雅舍?店主不理。岂知周先生回校召集学生于店前抗议,店主只好改挂店招。”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放回忆。
而文化学者张颐武则感觉:“周先生似乎是他的《红楼梦》中的人,他其实更愿意在那个世界里做逍遥游。”
然而,痴者往往是执拗的,直来直往,不迎合于人,对不足之事多有批评。因此,周汝昌早早地陷入了学术论争之中。所幸的是,一入“红楼世界”,他便找到了自己的“大自在”、“大欢喜”。正如后人评价——曹雪芹痴,用10年写《红楼梦》;周汝昌更痴,用60年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痴人之间性情相通,周汝昌确是曹雪芹的旷世知音。
为悼念雪芹,老人写下“万口齐嘲玉,千秋一悼红”的诗句,并直言此生“无悔,不悔,难悔,也拒悔”。
周老虽去,却留铮铮风骨烛照人间。缅怀之余,或许该有一问:何时能多一些以学术为生命的真学者,为千古文脉的传续而痴而狂?
(责任编辑:王锦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