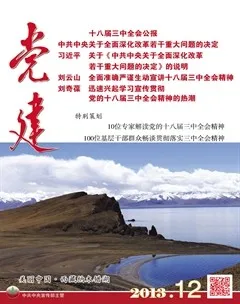我以颤抖的双手抚摩那三十万亡灵的冤魂

又到了12月13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日
我以无以言状的悲怆追忆那
血腥的风雨,
我以颤抖的双手抚摩那
三十万亡灵的冤魂,
我以赤子之心刻下这苦难民族的伤痛,
我祈求,
我期盼,
古老民族的觉醒!
精神的崛起!
时光仿佛倒流到1937年那血雨腥风的岁月。我恍惚走向南京城西江东门,这里是当年屠杀现场之一。那逃难的、被杀的、呼号的……那屠刀上流淌的鲜血正滴入日本军靴中,白骨层层铁证男女老少平民死于日军的残暴里。
极目西望长江滔滔,平静中有巨大的潜流,俨然30万亡灵冤魂的哀号!
1
叫人不能容忍的是,尽管当年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皆以确凿无疑的犯罪事实为依据,对日本战争罪犯作了正义的判决。可是战后70多年来,日本政府在对待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上,基本上采取暧昧或含糊其辞或躲躲闪闪的态度。
其极右势力更是否定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每年的8月15日都有许多官员包括内阁大臣等去靖国神社参拜。1996年8月,日本公开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实际上是对侵华战争包括南京大屠杀全面的翻案。
一个公然敢于推翻铁的史实的国家及其右翼人群,是未来和平危机的隐患!
世界近代史上的三大惨案——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法西斯大屠杀、广岛原子弹爆炸、南京大屠杀,在未来人类会重演乎?在当今和平环境中提出这个问题似乎耸人听闻,但细想则是令人忧心忡忡。
因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程的扩建是历史的需要,是人类的灵魂工程。作为凝固历史,铸造国魂的雕塑则是直接进入人心灵的。它为人们对客观史实的认识提供价值判断之参照。
2
2005年12月15日,我有幸成为纪念馆扩建工程大型群雕的创作者。在不平静的创作过程中,有无数彻夜难眠的夜,至今仍历历在目。
如此重大的题材,如此重要的地点,如此壮观的场馆,雕何?塑何?雕塑者何为?
首先是立意,立意的基础是立场。是站在南京看待这座城市的血泪,同情当年市民的苦难遭遇?或是站在国家民族的方位,看待吾土吾民所蒙受的劫难?我认为,只有立足于人类、历史的高度来正视、反思这段日本军国主义反人类的兽行,才能升华作品的境界,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纪念、仇恨。
回顾一下我国自上个世纪至今所有表现抗战题材的作品,几乎是再现场面。那种国仇家恨溢于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这是时代的必然。但今天的中国日益强大,今天的世界日趋文明,中国有自信来倾诉历史的灾难与蒙受的污辱。作为受辱者,中国有责任控诉战争,有责任告诉世界: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一个遍体鳞伤的弱国是没有能力祈求和平的!因此凝固平民悲怆形象,表现祖国母亲蒙难,呼唤民族精神崛起,祈望世界和平,应当是整个作品的表现核心。
立意明确后,要解决的是作品的取材与形式。有许多建议几乎是一致的意见:入馆处表现屠杀的惨烈,尸骨成堆,尸横遍野。主建筑下面血染成河。我则认为,纪念馆处于街区,在喧闹的现代商业、人居环境中,世俗生活情感与惨痛历史悲剧之间需要过渡。雕塑应当一目了然而又层层引人进入,悲情意识由内而生发。因此,叙事性、史诗般群雕组合可产生这样的感情交响,波澜跌宕,起伏壮阔。它超越一般意义上灾难的描述,痛苦的诉说,在这史诗中所生发的美,足以鞭挞丑恶、罪恶,足以从灵魂深处渗入,而荡涤人类的污浊。它有别于单一化、极端化、政治脸谱化的捏造,而是以普遍人性为切入点来深刻表现。
在这恢宏的精神意象辐射下,一个强有力的旋律在我内心油然而生:
高起——低落——流线蜿蜒——上升——升腾!
它对应着:体量、形态、张力产生的悲怆主题《家破人亡》(11米高);继而是各具神态、体态、动态的《逃难》群雕(10组人物);再继而是由大地发出的吼声,颤抖之手直指苍天的《冤魂呐喊》(12米高抽象造型)。
群雕以三角形体面的主体建筑为背景,组成激越而深沉,悲惨而激愤的乐章。就空间而言,它所形成的气场,使观众统摄于悲天悯人的氛围中。
3
优秀的创作设计方案是思想的体现,只有成为公共艺术,走向空间落实为物化后的精神载体,才能称为作品。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其核心是“遇难、纪念”。矗立在新馆始点的《家破人亡》,以11米的高度,表现被凌辱的母亲悲痛之极,无力地手托着蒙难的儿子麻木地向着苍天呼号。屈辱而不屈。她是千千万万受难家庭的代表,是蒙难祖国母亲的象征。造型似大写的“人”,嶙峋而沧桑的身躯在视觉上给观众以震撼。
这尊标志性雕塑的创作手法采用“大写意”,让母体成为山河、成为巨石。且配以诗文:
被杀害的儿子永不再生
被活埋的丈夫永不再生
悲苦留给了被恶魔强暴了的妻
苍天啊……
我常常在思索,如真的存在灵魂,那当年的受难者会是怎样地告诉今天的人们,他们身心的创伤?
我曾访问过幸存者常志强。说起亲眼看着自己母亲被日本人刺死,弟弟的泪水、鼻涕与母亲的血水、奶水冻凝一起的情景,老人仍声泪俱下,噩梦未醒。我有一个强烈的欲望,要复活那些受屈的亡灵。纪念馆内那些头盖骨上的刀痕,那被砍断的颈骨,那儿童骨头上的枪眼……那在光天化日下被剥光衣服的妇女的哀哭,身上还投射着日本军帽的影子;那被反绑着双手、跪着,刹那间,身首已分的俘虏;那被集体活埋的妇女、青年,昂首不屈的男子……我甚至走在南京旧城区,也不自觉听到轰鸣与哀鸣!
试想,纪念馆的大门就是被攻陷的中华门,如果每个进入馆内的观众,相遇了这批由城内而逃出的亡灵,这当是历史与现实,幻觉与真实,灾难与幸福,战争与和平的相遇。我将这10组21个人物置于水中,与行人及建筑若即若离,营造时空的对语。尺度近乎真人,从感觉世界里与观众互为参与。
他们中有:妇女、儿童、老人,有知识分子、普通市民、僧人等。最为让人悲悯的是常志强的母亲将最后一滴奶喂给婴儿;最为勾起回忆的是以儿子搀扶80岁母亲逃难的历史照片为原型的创作;最为令人惊恐的是那被日军强奸的少女为一洗清白而投井自尽;最为引人沉思的是僧人为死者抹下含冤的双目……这21个人物,虚实错落形成悲烈的曲线。雕像为银灰的色质,迥然于见惯了的青铜、古铜色,它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时空冤魂,是弥天恐怖中逃出的难者。
这组雕塑我做得极为淋漓酣畅,它可以凭借体态、动态的极端夸张而达到极强的表现意念,可以将老人那颤抖的筋脉刻画得入微而生动;也可以从他们凸起的双眼揭示那惊恐与愤怒!在这里,精妙的写实和概括的写意,准确的塑造和变形的夸张,结构和比例的所有标准只服从于“表现”!这种表现是源自魂的底层又深入到骨子里的大表现!由此,我真正体会到结构与灵魂的对应;表现与精神的对应;夸张与情绪的对应。
建筑师为纪念馆设计的主建筑由东至西,最高处18米,最低处西端为正负零。我设计的《冤魂呐喊》在西端,从构思上步入情绪高潮,从整体视觉形式上呼应了建筑,也为建筑的西端增加了应有的平衡。它以劈开的山形寓意破碎的祖国河山,其豁口便自然成了纪念馆的门道。它虚拟城门,是逃难之门,是死亡之门。左侧三角形直指苍穹,塑造了一呐喊的冤魂。右侧表现的是平民生灵被屠戮的场面。它拔地而起,斜插云霄;是冤屈的吼声,是正义的呼号。以三角形的视觉冲击紧连大地,撼人魂魄。
在《冤魂呐喊》这组雕塑中,几何体的运用是我无意间在视觉幻念中形成的。它是从大地深处突兀而出的!我冥冥感到在那样的空间,在《家破人亡》、《逃难》后需要这样一个“大抽象”符号的感情特征而彰显,以昭观众。
《冤魂呐喊》,将人间的苦难诉诸上苍,分别为12米、7米的两个三角形体块将观众陷于其间,压抑狭窄的“逃难之门”为观众与“逃难者”塑造了同一个情感通道。
4
走出纪念馆,是和平公园。
但见绿洲一片,在出口处是长140米,高8米以“胜利”为主题的浮雕墙。以“V”型为基本构成,分别以“黄河咆哮——冒着敌人炮火前进”和“长江滔滔——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作浮雕。在“V”型的结点处塑造了一位吹响胜利军号的中国军人,脚踏侵略者的钢盔和折断的指挥刀。采用中国古代雕塑象征主义手法表现了人民的胜利、正义的胜利,也象征着让战争远离人间。
该雕塑采用现代设计的构成手法,借助三角形“V”字的大小对比透视,形成气势宏宽的大场面。胜利的主题与《和平》公园主题相辅相成。放射状的浮雕有力地表现了胜利的精神状态,它仿佛拥抱和平的双翼。为一部悲烈、沉郁的史诗结尾处,找到了舒展而光明的警句。
塑造手法中刀砍、棒击、棍敲与手塑相并用,其雕痕已显心灵伤痕,是民族苦难记忆,是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罪证记录!
塑造的悲与愤产生速度与力量。我在《辛德勒名单》主题音乐的回响中完成每一个形象。为此,我写道:
我以无以言状的悲怆追忆那血腥的风雨,
我以颤抖的双手抚摩那三十万亡灵的冤魂,
我以赤子之心刻下这苦难民族的伤痛,
我祈求,
我期盼,
古老民族的觉醒!
精神的崛起!
(责任编辑:王锦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