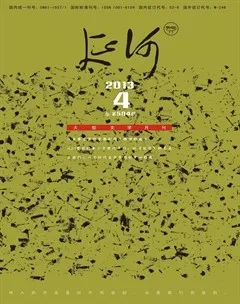触摸陕南的血脉与风骨
1、勾描陕南
大自然的伟力造就了秦岭。从四亿多年前的陆地抬升到一亿多年前的印支运动,在漫长的地球地理变迁中,秦岭逐渐脱离大海,度过漫长的成长期,形成了横亘在大地上一道脊梁,铸就了它雄伟的身姿。在最近的一亿年中,大地上的这道隆起,被剥蚀、被拉动,青藏高原东部的这片山地处在运动之中,在它的北部,地壳被侵蚀、剥离、下陷,形成了广阔的平原。在它的南部,大地分裂,在秦岭巴山之间,形成了缓缓跌落的坡地。
秦岭南坡舒缓下垂,长达一百多公里,直达汉水河谷地带。发源于南坡的众多河流,清澈流淌,汇入汉水。沿着汉水是一连串的花朵似的冲积盆地,这些宽窄不一的河谷盆地,被这条大河连缀起来,宛如一道绿色走廊。这里生长着蔬菜、粮食和水果。人家临水而居,构成了村庄与城镇。汉水之南,群山莽莽苍苍,这是绵延的大巴山区。两列大山拱卫,一道河川蜿蜒,整个陕南地区,看起来就像是一条由山川构成的宽阔散漫的大峡谷。
2007年10月,一条跨越秦岭的高速公路建成开通,这条从北京至昆明、将西安和成都勾连起来的国道大动脉,把秦岭北部的关中平原与南部的汉水河谷地带的空间距离缩小到几个小时的车程。公路建成开通之日,来自大都市西安的旅游车辆立刻将这条高速公路拥塞成一条传送带,车辆奔流不息,游客来往不休。也许这片山地的平静早已被打破,但是这条沟通了西南地区与北方地区的国道大动脉,划开了山地的帷幕,露出了它平静而神秘的面容。多少年来,秦岭地区被视为地球上最具有生物多样性的区域,汉水流域清澈的水源为长江输血,也为整个南水北调工程贡献清洁的水资源。这片山地由此而吸引了各种各样的目光,令人不禁想要去触摸它的风骨与血脉。
陕西由截然不同的三部分构成:莽莽苍苍的陕北黄土高原,八百里宽阔延展的关中渭河平原,一唱三叹的陕南秦巴山地。秦岭是中国地理和气候的南北分界线,地处秦岭南坡和巴山地区的陕南山地,相对于个性凸显的陕北和关中,陕南刚好就居于地理和气候上的南北过渡区域,风俗人文意义上的特点不显,个性标识的丧失,往往令人惶惑。
让陕南的人文历史专家感到惶惑的是,他们很难找到用来指代陕南的人文标志。走进陕北,苍茫的黄土高原天生与它悠扬婉转的陕北民歌相互应和;在关中,高亢激越的秦腔,飘扬在村镇上空;相比之下,陕南是缺少这方面的个性指代的。人文史学专家们发现,在这片山地上,风俗民情是如此的五方杂陈,方言乡音如此的南腔北调,生活习惯也是如此混然杂糅。没有一个人文标志可以让人油然而想起陕南,也没有一个地域标志可以让人深刻地记住陕南。多少年来,地方的人文历史专家想要摆脱这种尴尬,触摸到陕南的血脉与风骨,他们最终将发现,这种无个性,恰好也许就是它的个性,这种特点的杂陈,也许恰恰就是它内在的风骨。
对于生活在这片山地上的居民来说,找到自己的集体标志似乎并不重要。他们祖辈传承,生活显得平静而封闭。山区与平川,村落和城镇,或缘山而建,或临水而居。相对与飞速发展的外部世界来说,这片山地显得封闭而滞后,它有一些迟钝、一点平和、几分散淡。
2、老家何处
作家余秋雨的一次汉中之行,一席关于汉中的话,成为汉中人引以为豪的事,汉中人把余秋雨的几句演讲辞镌刻在汉江河堤的汉白玉镶板上,希望引起每一个观者的联想:
“我讲汉语,我写汉字,这是因为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王朝——汉朝。而汉朝一个非常重要的重镇,那就是汉中!汉中这样的地方不来,那就非常遗憾了!因此,我有一个建议,让全体中国人把汉中当做自己的老家,每次来汉中当做回一次老家。”
“老家”,是令每一个中国人心动的词汇。对于中国人来说,老家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词汇,而是一个文学化诗意化了的形象,忘记老家意味着对祖先的不敬,记起老家意味着我们家族的源头。老家是故乡,老家是血脉之源。
一个“汉”字引起了一番诗意的张望和联想。这个“汉”字,正是一条大江的名称,自古以来人们把“江河淮汉”并称,汉水作为长江的最大支流,也是滋润着陕南山地的水脉。山脉构架、河流滋润的这片山地,理所当然因为这个“汉”字而受到瞩目。
但是对于这片山地上的居民来说,老家何处,却是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我想起了20年前的一次问答。
3、家族史与集体记忆
我问我的父亲:我们老家是在哪里?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都需要填写无数的档案,中学老师对于“籍贯”的解释是“老家”——所以当时我想起问父亲这个问题。
对于一辈子居住在陕南大巴山区的父亲来说,这个问题显得有些麻烦。他是个农民,虽然也读了些书,但是一辈子在瘦弱的山坡上劳作,大山对于他的人生来说就是重重障碍,阻挡了他张望远方的目光。他坐在山里人家的火塘边,跟我讲述我家族的传说。山里煤油灯的光亮昏暗得近乎于无,倒是他的旱烟锅里的火星一闪一闪,把我带到了遥远的年代。
这是陕南山区居民多少年来的常见的生活场景,大山封闭,坡岭无声,山区人家的火塘里燃烧的木头冒着烟、火塘上悬挂着铁铸鼎罐,罐子里也许烧着水,也许炖着腊肉。山区居民往往围着火塘,对着火光吸着旱烟、讲述着他们祖辈相传的往事。
父亲告诉我,我们的老祖宗是两百多年以前的兄弟俩,这两兄弟来自于湖南湘潭,他们怎么来到这里,我父亲无法讲清楚。他们在这山里面刀耕火种,繁衍生息,后来创出了一份家业,成为本地的大户。我们家族的最后一个地主的结局有些悲壮,他当然是两兄弟中某个兄弟的后代,到了上个世纪的民国时期,这个富裕的地主,拥有宅院、长工、家仆,但是他得了一种怪病,背上长了大疮,有一天他背上的毒疮疼痛难忍,刚好屋外大树上的一只白乌鸦啼叫不休,于是他暴怒之中操起火枪去打那只可恶的乌鸦,枪响之际,乌鸦落地,他背上的脓疮也崩裂,于是他在血流和剧痛之中死去了。这个家族繁衍几百年,范围覆盖了周围的几个乡镇,不到二百年之后,我们这个姓氏在周边乡镇成为人口众多的家族,其中有一个村的大部分村民都姓这同一个姓氏。
这是我父亲的讲述。从父亲的讲述中,我知道了两个信息:第一个,我们的老家是湖南湘潭;第二个,我们的祖宗是用近乎流浪的方式来到这片山地的。
陕南民俗学家陈良学在他的专著《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中讲述一个家族的来源,陕南汉阴县“黄”姓家族的繁衍发展历史:兴宁黄氏是福建客家人,是战国时楚国贵族春申君黄歇的后裔,发源郡望为湖北武昌江夏县,故号“江夏堂”。在悠悠历史岁月中,黄氏后裔渐次移居福建、江西、广东等地。其中一支先后从梅州——龙川——揭阳石坑——迁移至长乐长沙坪,又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正月初八起身,迁移到四川省宁远府西昌县黄莲坡(今黄联乡)大中坝立业。另一支的黄国煌夫妇二人则是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陕南汉阴县凤凰山以南的凤江乡堰河村定居下来。艰难的垦荒生涯给黄氏的生活和繁衍带来极大的困难,黄国煌夫妇在此生下三子:除黄大昌存活外,其余二子均殁于早夭。至黄大昌成人,定居生活已有了较大改善。迁往陕南的黄氏家族逐渐进入人口繁衍的鼎盛之期,到第五代已经繁衍为37支,到第六代、第七代,其人口繁衍成几何倍数增长,后裔众多不可胜数。
在陕南地区,这样的家族故事数不胜数。这样的故事贯穿在古老的传说中,构成了陕南人的集体记忆。这种类似于美国西部垦荒传奇式的故事,让我们感觉到这片山地的血脉流转。事实上,远至唐代的安史之乱,宋代的南北对垒,到明清以后的太平天国运动、白莲教起义、捻军起义……屡次的战乱与兵祸,使得无数的外来人口进入这片封闭的山地,繁衍成为本土的居民。
在陕南大巴山区的镇巴县的深山老林中,曾经生活着一支苗民,很多地方史志专家试图考察他们的来历,但是由于时间久远,生活的封闭,他们的家族史同样只能流传于口头。镇巴县政府在清水乡的河谷平缓地带为这些苗民修建了移民新村,从大山林中迁居出来的苗族后裔,围着篝火跳舞、在夜色中唱起古老的山歌,我们能从这舞姿和歌声中隐约感受到来自遥远贵州高原上的一丝苗族风情。
陕西略阳县地处秦岭西缘,在这里,发源于秦岭的西汉水曾经是汉水的源头,由于地质变化,它被袭夺成为上游嘉陵江的主要支流。嘉陵江上游峡谷幽深,两岸山区的居民保持了独特的民俗风情。山区民居檐头雕花、门墙高峻,白线钩边,是典型的羌族风格的建筑。略阳人有着陕南独一无二的地方小吃,名叫“罐罐茶”。一个深秋的早晨,我的略阳朋友周吉灵带我们去乡下品尝这种地方小吃。乡村的火塘边熬着茶水,茶中加入了藿香之类的草药和香料,用这种茶水煮出了加入油料的炒米、炒面、腊肉、花生……入口生香、令人神清气爽。这是嘉陵江上游山区居民的主打早餐,当地人认为这吃法是古老的羌人发明。我的这位当地朋友曾经考察自己的家族来源,最终寻找到甘肃陇东南地区,这一地区曾经是羌族的聚居地,三国时代诸葛亮六出岐山,羌族土著曾经是最得力的友军。我这位朋友指着自己直挺的鼻梁对我说:他的祖先也许就是羌族的后裔——羌族人高鼻深目、身材高挑、面容俊秀,是民俗学家公认的俊男靓女。地处汉水源头的宁强县,原名就叫“宁羌”,地名中隐含了本土的血脉流承。在陕南汉水上游和嘉陵江上游地区,羌人融入本土,历经演变,成为本土居民,他们的老家已无迹可寻,陕南,已然成为他们的老家。
4、峡谷里的村庄
汉水上游地区的最大支流褒河发源于秦岭南坡。西河则是褒河上游的一条支流。西河沿岸的山向着天空升起,河谷地带缓慢变幻,形成了一个个小块儿的河谷平地,山势有时挤压河流,形成狭窄的峡谷,有时让河流肆意铺展,绕一道大湾,铺展处就形成一些小小的半岛。在这些平缓的地方,往往都居住着几户农家,形成小小的村落,他们的房屋从树林和玉米地中间露出来。
道路顺着峡谷河流修建,两边都是高大苍翠的山。山都是从谷底陡然升高,山上露出一段段的绝壁,像是青翠的山林中的一些大块儿的色斑。有的山形如刀,斜插入谷底,有的浑圆,呈流线型落入河边。河流湍急,往往缓慢铺展,在平缓处和石头冲激,形成细碎的浪花;有时在山底形成水谭,显得幽深平静。
时而可见钢索吊桥悬挂在河上,吊桥一端是公路,一端是小小的村落。收获了的玉米杆密密站立在土地上,像是深秋的树林,与高处的山林形成了颜色的对照。看上去,秋天是从河谷开始的,逐渐上升。这里的河水冰冷,已是秋水;河边的缓坡上玉米干枯,黄绿夹杂,呈现初秋季节的色彩;而在更高的山上,林木苍翠,依然还保留着夏天的景致。农家的门头悬挂着一串串的玉米棒子,远远地耀眼发亮。路边多树,坡地上的核桃树,房前屋后的苹果树、枣树、柿子树。苹果开始变红,但还没至鲜艳;柿子由青转黄,成熟的已显示出金黄,发出饱满鲜润的光泽;枣树的叶子中间,果实青白,有的成熟至红褐色。
陕南山地的高处山岭和低地河谷,被季节描绘出丰富的色彩。河谷地带生长着蔬菜和稻米,山岭坡地往往多长水果,水果也是南北品种兼有,北方的苹果酥梨,南方的甘蔗甜橘;河谷和山岭之间的浅山丘陵上,遍布着茶园,陕南被称为中国茶叶最北生长线,人们饮茶成为习惯,茶叶在汉水沿岸的商埠码头曾经是重要的贸易品种。
居住在宛如隔世仙境的山地,陕南留坝县的狮子坝村的村民包胜武同样无法说清自己家族的来历,他是一个不到四十岁的农家汉子,身材敦厚,面孔黝黑,在社火戏中,他常常扮演的角色是关公。狮子坝的地社火被留坝县申报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包胜武告诉我,这里的地社火已经传承了三四代人,至少有一百多年历史了。
地处秦岭腹地的狮子坝山多林密、地广人稀,他们逢年过节自娱自乐,敲锣打鼓演出地社火,为的是给寂静的山林增加一点声响。社火起源于古老的祭祀,在陕西各地均有流变,但是都是以脸谱、造型、表演为主要特点。每逢春节这样的传统节日,人们穿上戏装,画上脸谱,或高抬游行、或就地表演、或高跷行走,使古老的祭祀仪式变成了地道的民间娱乐。狮子坝的社火戏属于社火的一种——地社火。地社火不拘场地,可以在宽大的场院上演出,也可以在农家的厅堂里开场。演员一般不超过三五人,每个剧目的时间少则五六分钟,长也不超过二十分钟。使用的乐器很简单,无非锣鼓弦子,服装类似于大戏的服装,道具如关公的大刀、神将的鞭、哪吒的乾坤圈,都是最简陋的,有的是临时制作的,面具上画脸谱,也并不复杂。相比于舞台大戏,这只是小打小闹,但是在褒河上游,这样的苍茫山林中,农民们无缘一睹大戏的风采,所以他们创造了属于本土的社火戏。将舞台大戏零碎化了、大众化了、民间化了,这就是一种百姓的创造。
留坝文化馆的音乐干部苏茂华多年来搜集研究留坝山区民歌,对民间音乐深有研究,亲耳聆听83岁的老人包光盛唱起狮子坝地社火的唱段,他判断说,狮子坝的社火戏的唱词有秦腔眉户剧的风格。也不难听出,社火戏中的道白,依然保留了关中话的音调。但是,同样也可以发现,在这些唱腔中,吸收了更多的大巴山区民歌的风格。狮子坝地社火就这样,兼容并包,多方吸取,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百多年的山居生活中,它成为本地居民的重要娱乐方式。在锣鼓声中,包胜武和他的乡亲演起了《三请诸葛》、《哪吒闹海》等剧目,简单的唱腔令人想起朴素的山歌;粗朴的动作,写意着古老的艺术。
翻过秦岭到达关中,秦腔高亢张扬,八百里秦川,无论老幼妇孺,皆能吼几句秦腔。这种生活习性,渗透延续到秦岭南坡,演变成了地道的陕南民间艺术。你可以把这看作陕南血脉中的杂糅流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陕南个性中的兼容并包。
5、隐秘的庇护之地
从关中南来,进入秦岭以北的各个峪口,往往见山壁陡立,高与天齐,道路在陡峭的崖壁上或者昏暗的山峡中穿行。这鸟飞难过的危险之旅,却是自古以来由北方进入西南地区的必经之路。秦岭北陡南缓,缓缓下落的秦岭南坡,为南来的暖湿气流留下了足够的爬升之旅,这股从大陆南部海洋长途跋涉而来的暖湿气流朝云暮雨,滋润了山地,培养了葱绿的植被。两千多年前,在秦岭巴山地区,高山上有乔木,悬崖上有奇花,河谷两岸,生长着茂密的植被。宋代的大文人文同曾经隐居在汉水沿岸的洋县境内,他是一位著名的画家,传说文同画竹,“胸有成竹”,这是因为他朝夕与竹相处,耳濡目染,了然于心,令人怀想当时这片绿地上,竹木茂盛、生机盎然的景观。
葱绿而隐秘的山地,为这里的生物提供了庇护。在远古的幽谷中,可以想象生活着各种飞禽走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著名的熊猫专家潘文石教授曾经长达十年考察研究秦岭大熊猫,在秦岭南坡的华阳山区,他和助手常年跟随大熊猫的踪迹,把这片山地称为“大熊猫的最后避难所”。
与大熊猫一样受到高大逶迤的秦岭巴山庇护,秦岭南坡和汉水河谷地带生存着朱鹮、金丝猴、大鲵等种类众多的珍稀生物品种,这些避世的生物仿佛一个象征,令人想起了居住在此地的陕南人。
历史上屡次战祸纷争之中,由于这里是抵达巴蜀的重要通道和给养渠道,两汉三国,刘邦在汉中称王拜将,上演楚汉争锋;诸葛亮在定军山用兵鏖战,建立鼎立局面。宋代陕南成为南宋与金国对垒的前沿阵地,在陕西略阳县的嘉陵江畔,至今还可以找到当年边境战争的遗址。此后自元明清三代,屡次的饥民暴动,农民战争,在中华大地上演,却最终使一部分人长途奔波,逃避到小小的陕南山地,繁衍生息,变成了此地的居民。陕南是如此特别,因为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它实在只是一块小小的版土;但是它又如此令人难以忽略。因为在青藏高原以东,秦岭是最高大的山脉;自长江上溯,汉水是最重要的支流。高山大河,构筑了一片独特的山地。这片幽深僻远的山地,成为北方与大西南沟通的障碍,也成为流民最便捷的庇护之所。
历史上的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为此地带来了来自两湖两广地区的流民;西南与中原的对垒征战,导致羌汉交融,川贵地区的移民来到陕南,同时南下的中原移民也定居此地。陕西及西北地区的回民之乱,使得陕南成为回民的重要聚居地,陕南地区的安康市和汉中市,都有回民居住街区,西乡县的鹿林寺是西北地区重要的清真寺之一。由于陕南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移民的重点。
移民开垦,居住繁衍,构成了一个人文标志模糊暧昧的陕南。陕南地区的方言体系令人迷惑,东部的商洛人,乡音近于关中;中部的安康人,口音颇似湖北;西部的汉中人,则操着川腔。
由于这种避世迁移的原因,陕南人生活得近乎封闭,生活安宁恬淡。在陕南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当数汉代的张良和商山四皓,前者功成身退,隐居在秦岭西段紫柏山下,辟谷修炼,伴着青山老去,陕西留坝县紫柏山下的张良庙是陕南地区的名胜古迹,历朝历代受到高规格的保护,至今仍是殿阁巍巍、树木环拱。商山四皓则隐居商洛山中,食野草为生,与走兽为伴,显示的是一种与世无争的性情。道教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宗教之一,道家所体现出来的生活观念和人生智慧,是至今为人所探讨的,它也影响着陕南人的性情。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封闭落后的陕南让人感到惊讶,无论是自然环境的影响还是人文民情的熏染,都与这片山地的独特性情有关。
6、山地的忧思
秦岭南坡的华阳镇曾经繁华一时。秦岭长青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地带在秦岭中段山岭活人坪梁以南。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里是著名的森林采伐基地。这座小镇上有完整的长街,狭窄的古朴街道,木质的铺板门面,这里曾经布满供销社、茶铺、小吃店、杂货店,三五成群的林业工人在这里打发他们的休闲时光。镇头有一座保存完好的古戏楼。这里与关中太白县相连,由此步行翻越秦岭,可以在一天之内直达关中平原。唐代的著名古道“傥骆古道”就从这里经过。
在陕南汉中区域的方言中,洋县的方言最为独特,人们的方音接近关中口音,是地道的“秦腔”。地方文史专家们普遍认为这可能与那条唐代的著名古道有关。在华阳的古戏楼上,开演的就是高亢激越的“秦腔”,唱念道白,人们耳熟能详,百听不厌。华阳镇曾经的繁华,仿佛这座古戏楼,演示着不同时代的繁华与苍凉。
发源于秦岭的酉水河在华阳镇外流淌,得益于这条河流,在秦岭山地上形成了一片山地坝子。平展的高山坝子,散落着村庄,华阳镇座落在坝子的边缘。站在小镇的街头,可以看到山岭在不远处绵延。向北的山岭高大逶迤,流线型的山脊划过天边。向着那些山岭出发,很快就可以进入幽深的峡谷,当年采伐森林开凿的林区公路穿过峡谷,沿着山岭盘旋而上,直达山岭最高处。不到20年,森林遭到大规模砍伐,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林业采伐的终结时代,这些高大的山岭上已经没有大树可以采伐了。实际上,如今进入华阳林区,已经看不到大树了,望出去除了新生的次生林,就是细小的乔木、低矮的灌木,林间肃然,除了小鸟的飞动声,也很难见到野生动物的身影。要知道,当年就是在这里,中国熊猫之父潘文石教授曾经长达十年,率领着助手和学生,观察跟踪大熊猫,成为传奇佳话。
如今的华阳镇已变得苍凉冷清,行走在古镇上,可以见到大多数铺板门面是关闭的。古戏楼上的大幕已收起,锣鼓声已没有了余音。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森林禁伐政策的推行,华阳林区的森林采伐告停,实际上也无木可伐了。森林采伐时代的最后岁月,工人们得长途攀爬到险峻的高山顶上,寻找一两株幸存的大树。随着这些古老大树的轰然倒地,森林在痛苦的呻吟中变成了废墟,如今深入长青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地带,登上海拔2500米以上的高山,也只能见到被地衣和青苔覆盖的树桩,仿佛惨烈的伤口,向人们诉说曾经的痛楚。上世纪80年代中期,长江中上游实施水保天保工程,森林禁伐,森工企业关闭,长青林业局大量森林工人被遣散,华阳镇的繁华结束了。2006年秋天,当我来到华阳小镇,看到华阳长青保护站的工作人员正在招待所门口晒着温暖的阳光、喝茶打牌。这座小镇宛如世外桃源。站在镇外酉水河的的铁索吊桥上,远远望去,四面都是一列列的大山,那些圆润的山脊构成了视野中优美的线条,大山青苍,村落布局在高山平坝上,一派安宁与闲适。
傍晚时刻,夜幕从山岭上垂落下来,一轮清丽的月亮浮现在天空,四周安宁,夜晚肃穆。站在铁索吊桥上,可以听到河中的水哗哗流淌的声音,宛如动听的音乐。
小镇上的灯光亮起,像是闪烁的星星。我们走进一家餐馆吃饭,服务员拿来菜谱,让我们感到惊讶,菜谱上有猪獾、有野鸡,有麂子、有野猪,熊肉是被口头告知的——要知道,这些都是国家明令保护的野生动物。面对这场野生动物的盛宴,我们感到震惊。不敢点菜,即便点了可能也无法下箸。
这是经济大潮中的普通一幕。
华阳镇外,又一条翻越秦岭的公路正在修建,设计中的这条公路将沿着古道,以最便捷的线路翻越秦岭,把更多的外来旅游者带入秦岭腹地——这里生活着国宝大熊猫、金丝猴、羚牛等多种珍稀生物。在过去的岁月里,穿行在这些幽僻的山岭中的外来人,多是国际组织的专家和中省单位的官员、媒体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普通旅游者将由此进入秦岭南坡的保护区,他们带来的不单单是来自外边世界的惊奇目光,还有着对陕南平静封闭生活的好奇打量……
陕南现实所怀有的焦虑感来自外来的冲击。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在急切而冲动地制定施政方针。他们不约而同把目光盯向旅游业。2006年五一黄金周,陕南柞水县的溶洞前,拥塞着来自西安的游客,这些来自大都市的游客,把旅游花销带给陕南的同时,也把垃圾、废弃物留在了这片清洁的山地上。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陕南人变得躁动而惶惑,那自古传承的血脉与风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他们再一次触摸打量自己的生活,也让旁观者为之满怀忧思。
栏目责编:阎 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