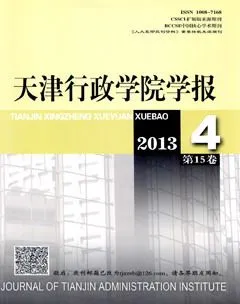大国国际形象与气候政治参与:一项研究议程

摘 要:国际形象对于国际政治中的大国而言是一个不容忽视却又难以界定的重要因素,它包含了一定时期内为他者所认知的国际相对地位、身份、威望、声誉、荣誉等。在国际关系理论史上,对国际形象的界定较为模糊,甚至一度曲解,国际形象的建构其实是一个渐进和复杂的过程。大国参与气候政治的行为与其国际形象存在相关关系,正向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政治进程,可能使大国的国际形象得以重塑,对于新兴大国而言,亦有助于为崛起而进一步创造软条件。
关键词:形象;国际形象;大国;气候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4-0050-08
一、问题的提出
在国际关系中,由于国际行为体的实力增长,尤其是伴随着国家的崛起进程,基于战略考量和现实政治的需要,国际形象之于国家间互动及国家崛起本身的意义逐渐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然而,国际形象同时又是一个既容易被联想到又往往难以名状的因素,给国际形象下一个定义,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少分歧与争议。
从“形象”这一词源考察入手,可以泛指“形状相貌”[1](p.2003)。按照《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版)的解释,形象也可以定义为“引起人的思想和感情活动的具体形状或姿态”。在英文中,与“形象”相对应的词有“Image”、“Identity”、“Reputation”、“Prestige”、“Figure”、“Form”等多个(从我们要讨论的国际形象来看,“Identity”、“Reputation”和“Prestige”较为对应,下文将论及)。西方学者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认为“形象”是人们关于某一对象的信念、观念与印象[2](p.607)。
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主要分析单位以及国际体系内的主要行为体,其国际形象理应得到较多的讨论。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尤其和平崛起路径与和平发展道路受到广泛关注之后,国内学界逐渐意识到了国际形象的重要学理意义,并开始尝试性地对国际形象进行界定:其一,认为国家的国际形象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与自然要素的综合认知与评价,其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外交形象、在国际公众中的形象和国际媒体上的形象[3]。其二,认为国际形象是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基本精神面貌与政治声誉。其中,大国的国际形象是现代国际社会中作为大国应具有的良好精神面貌与政治声誉,是国际社会从时代精神角度赋予的责任和义务。当代良好的大国形象,至少包含五个方面因素,即现代身份、世界贡献、战略意志、特殊责任、有效治理[4]。其三,认为国际形象即一国在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诸方面相互交往过程中给其他国家及其公众留下的综合印象[5]。其四,认为国际形象是在国际社会的相互交往中,国家自身及其他行为体对一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民族、政府行为和发展模式等相关构成性或表现性要素的相对稳定的认识和评价。它是主客体作用的统一体[6]。
同时,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反观国外学界,真正为国际形象给出明确定义的尚不多见,而往往由国家的“声誉”(Reputation)、“荣誉”(Honor)、“威望”(Prestige)等来指代。比如国际威望(International Prestige),又可以称为“国际声望/名望”或者说“国家声誉/名誉”,它指的是一国通过将国内道德、知识、科学、艺术、经济或军事等投向(Project)他国从而获得某种理想的对外形象(Foreign Image)[7](p.41)。也有将之定义为一国对自己的认知与国际体系内其他行为体对该国认知的综合,此形象是一系列信息输入和输出产生的结果,是在结构上“十分明确的信息资本”[8]。再如声誉、荣誉这些词,在国际政治的历史与现实研究中也总是在交替而频繁地使用着——从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追求安全、荣誉与利益”、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声誉值得国家为之而战”、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的“声誉促进国际合作”、查尔斯·凯格利(Charles Kegley)的“维护国家声誉以向盟国展示自身的承诺可信度”,到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的“一国的声誉即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该国的持久特征或特性的一种信念与判断”等①。可见,对于声誉/威望的研究众说纷纭,相关的界定也较为随意或缺乏明确性。
为分析与叙述的需要,本文将国际形象定义为:行为体(主要指独立政治单位,如主权民族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为其他行为体所观察和所评判的国际相对地位(Standing)、国际威望(Prestige)、国际声誉(Reputation)、国际荣誉(Honor)等。评判的重点在于多数他者对该国国家身份/特性(Identity)的认知。比如,我们不仅仅关注美国到底是不是比苏联拥有更多更先进的高新技术,而且还在乎印度等其他国家是否认同这种技术成果[9]。如此一来,国际行为体的国际形象至少需要两个(及以上)其他行为体(尤其是体系内有影响力的大国)的评判,从而在范围上保证形象认知是“国际的”,在程度上是较具有观察性的,至少从源于他者评价的量变积累上而言理应如此。
既然国际形象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历史和现实的)为他国所认知的威望、声誉、国际身份、地位等意识上的存在,那么它具有一定的可塑性,也可以塑造他国的期望,因而一定程度上也应当是一种软权力。同时,由于全球化导致全球问题的大量涌现,作为体系内的大国参与全球问题的治理,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往往可以引起他国的关注或全球回应,从而产生一定的国际影响。如此一来,参与全球气候政治对于崛起中的大国而言,无疑具有较重大的现实意义。然而,参与(正向参与或负向参与)全球气候变化的政治,多大程度上可以契合于中国的和平崛起模式,做出积极的国际承诺(正向积极参与气候政治)是否与中国国际形象的上升呈正相关?国际形象的维系与上升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其与国家软实力密切相关,形成与发展机制较为复杂。目前我们对于国际形象的考察,往往近乎于给定其“无所不在”的先验性,换句话说,即存在把“国际形象”口号化、标签化的倾向,这样一来,我们对于一国的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理解,或对崛起大国参与全球事务的解读,很可能流于泛泛。因此,本文的基本目的可以说是“于无疑处设疑”,对看似“简单明了”的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考究,在全球气候政治的视野下,考察气候政治参与中的大国国际形象问题。
二、理论解读与基本观点
从认知心理学上讲,形象建构有赖于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间的精神/情绪(Spirit)。二战后,理论家们几乎将精神/情绪从政治词典里排除出去。他们呼唤权力与物质利益,以此来解释原用于扩大荣誉、威望,或提升地位(Standing)的那些外交政策。早期的学者其实颇具匠心于融合精神/情绪,尤其在马克斯·韦伯那里,将荣誉与利益区别开来并认为领导者对前者更为敏感。他坚持认为,“一个国家可以原谅对其利益的损害,但不能容忍对其尊严的挑衅,尤其当它自视甚高时,其尊严不容挑战”[10](p.356)。国际政治对韦伯而言,是由那些国家为追逐所谓优越性之欲望(Desire)而推动的。国家获取超越他国的权力是为了获得权力威望(Power-prestige),即“超越其他共同体权力的荣耀”。国家间的地位竞争,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竞争,给国际关系带来了非理性元素,使国际形势恶化、军备竞赛与冲突加剧。韦伯为此还将法德关系作为例证[11](p.911)。即使在高度发达的文化关系中,政治家将冲突诠释为保持物质利益的权力问题,一般而言,这种冲突观还是要从属于自尊(Pride)、荣耀(Glory)、优越性或霸权的出现。荣耀(Glory)大致上给从古至今的战争提供了一个比任何基于经济驱动与政治算计的理论更为现实主义的解释[12](p.20)。
一旦我们超越韦伯,20世纪国际关系理论则将荣誉和地位降格为独立的动机。战后杰出的理论家要么忽略精神/情绪,要么将之视作显示和最大化权力的工具。汉斯·摩根索是一个典型,在他看来,国家总是追求增加、保持或显示他们的权力。国家旨在获得更多的权力,奉行“帝国主义”的政策。国家的外交政策旨在保持权力则奉行“现状政策”。国家想要显示权力则奉行“威望政策”。它试图“通过自己实际拥有的权力或自己认为拥有的权力、或希望他国相信自己所拥有的权力,来影响他国”[13](pp.70-83)。威望政策并非国家政策的终点,而是为维持或挑战现状。它能基于实际的权力或阻吓。摩根索承认通常很难彻底了解威望政策的潜在目的。更耐人寻味的是,摩根索对威望追求进行从结果到手段的贬抑,竟源于亚里士多德,认为追求认同是人的基本动力[14](pp.18-20)。对于权力的渴望,“一旦个人的生存得到了保护,他担忧的不再是生存,而是其相对于他者的地位如何”[15](p.165)。为了建构勉强说得过去的(Parsimonious)理论,摩根索颠倒了权力与威望的关系,他将前者从属于后者,推论权力是如何获取和保持的。他忽视了韦伯的箴言:权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任何政治理论须建立在对那些目的理解的基础上[12](p.22)。
在摩根索之后,罗伯特·吉尔平将威望从权力中区分开来,并首次赋予其在国际关系中的突出地位。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他将威望描述为国际体系中仅次于权力的最重要因素,以及“国际关系的晴雨表”。对于吉尔平来说,威望有着道德上的和功能上的基础。前者源于领导者国家提供公共物品,以及增进或保护公共意识形态的、宗教的或其他价值的能力。弱国追随强大的领导者,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接受现存秩序的合法性。每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相应地推崇一种意识形态以使得他对其他国家的支配合法化。在吉尔平看来,威望与冲突是紧密相连的。威望等级毫无争议且难以挑战时,和平才成为可能。这种等级制的削弱或动摇,一般先于冲突和战争时代。威望有别于权力,是因为权力认知会落后于国家的实际能力。体系中的权力认知与权力分配的非对称性越强,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大,尤其崛起大国权力被低估时更是如此。“体系中的崛起大国日益要求改变现状以反映他们新增长的实力及未满足的利益。”体系的管理失效,直到“认知与权力现实相符”,这常常需要战争,大国间战争的主要功能在于重建威望等级[16](pp.34-35)。
英国学派的主要学者对荣誉与威望不以为然。他们是所在方向的现代主义者,关注法律和实践意义上的国际社会显现(如布尔在《无政府社会》中所强调的那样,主要行为体即大国自身成了相对地位排序的评判者,依据相对权力的原则,则这种排序方能在“欧洲协调”中正式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权力政治说异曲同工)[12](p.23)。
因此,从理论上看,我们所定义和分析的国际形象,其中包含的相对地位认知、威望、声誉、荣誉这些重要构成性因素,如今看来它们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似乎“不证自明”(Self-evident),得以频繁出现在国际政治的理论与历史论述中,然而回顾经典和进行一些理论史研读后我们似乎不难发现,受制于主体间认知差异,“国际形象”或被漠视、或被权力政治观绑架、或被工具化解读,因而在其界定与分析中往往存在相当的模糊性和随意性。
在国际政治中,过于关注形象(威望/身份)上的相对地位(Relative Standings)/相对收益(Relative Gains)而发生的危险是可以想见的,如军备竞赛、安全两难、囚徒困境、政治市场失灵等。历史上的雅典和斯巴达、一战前的两大军事集团、二十年危机时期(1919~1939)的现状国和德日意挑战者、二战后的美苏(古巴导弹危机和苏美争霸)皆为我们容易联想到的例证,当然其实还有中国古代史中的群雄逐鹿诸侯混战时期(春秋战国、三国、魏晋南北朝)和所谓中原王朝和边陲游牧民族的对峙(秦、汉、唐、两宋、明朝)等都是经典的案例。实际上,在国际形象建构中的投入,一些行动的有限性往往不那么明显,或者换句话说,一国国际形象上的净收益有夸大的可能。比如二战前的英法等国,与其说是沾沾自喜于其绥靖政策“效果”,不如换个角度看是作为现状者的老牌帝国对自身大国威望的过度自信;中国封建时代统治者所建立的朝贡关系,希望因此可以为其统治带来威望,而往往只不过是一种华夏中心主义的迷思[17]。
然而,个人的、社会群体的,或国家的威望/形象,是如下因素考虑之产物:a)基本特征;b)对威望/形象给予认同的他者之价值;c)部分基于威望/形象考虑的短期行为;d)主要基于威望/形象考虑的行为。仅后两者易于操作[9]。从社会心理学上看,文化催生的形象/身份具有双重意义,它强调一些动机(Motives)的同时还贬损其他动机,并形塑行为体的发展和表达方式。从国家的精神层面来说,为获取尊重而行动,以及与此相关的路线与机制安排,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说,动机是构成形象/身份的重要因素,因为动机决定了我们的利益关切,而利益关切又促成了我们的行为(参见图1)。
如此一来,形象/身份、利益、行为,这些似乎都是社会决定的。然而,行为体并非社会化的囚徒[12](p.563)。反馈存在于这个“形象/身份→利益→行为”关系链的各个环节。行为体的行为具有重塑利益的潜能,而利益的重塑又影响到行为体的形象(如图1曲线所示)。重要行为体(如大国)形象的转变,或者说其他大量的行为体形象转变,能使其所在的国际体系的特征发生变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国际关系史上可以得到不少例证,几乎每一次历史转型期都与之契合,如欧洲大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体系转型——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形象的国家颠覆欧洲封建旧秩序,甚至形成对整个世界旧秩序的冲击;1917年俄国革命引发的系统效应;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和独立运动的高涨;东欧剧变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此类例证不一而足。这些都能反映国家形象得以重塑所带来的反馈力量(从杰维斯的“系统效应”来看,此为正反馈)。施动者(Agency)在这样的动态体系中的重要性和结构(Structure)一样重要,施动者是在另一方面彰显作用,即行为体不仅仅取决于行为,还受自身“信念”(Beliefs)的影响。国家的历史经历及国际社会化实践,使其习得有关世界如何运作的“信念”,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应对二者的最好方式又如何?制定政策的国内精英们包含了人们不同的世界观和相关的政策偏好,有些政策变化可以用行为体间的动机分布来解释,恐惧、利益和荣誉能引发不同的对外政策走向和特殊偏好[12](p.564)。
冷战以后,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加剧,全球气候政治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大国需要妥善应对的中心议题,那么在面对气候变化这一非传统安全威胁时,国家的国际形象或许拥有重塑的空间,从而顺应可能的全球气候治理潮流。当然,在面对这种“新”议题(或重新反思那些本应处于问题领域中心的边缘议题)的时候,如前所述,大国的“形象→利益→行为”关系链或许也未必呈现线性联系,而是可能由于反馈的力量使得利益和形象都得以重塑,产生系统效应。那么我们在全球气候政治的背景下讨论大国的国际形象问题,或许正如杰维斯所指出的那样,“思想从来都不会停滞不前,价值观也会不断发展,而新的机遇和威胁也随之而来”[18](p.105)。
为便于展开论述和进行接下来的案例分析,我们不妨假设如下②:
假设一,气候政治正向积极参与者。国际形象与之呈正相关关系,即国际形象受益于气候变化政治中大国的贡献,因之大国责任形象良性护持或渐进溯升;
假设二,气候政治负向消极参与者。国际形象与之仍呈正相关关系,简言之,即国际形象回落甚至受损;
假设三,气候政治与国际形象呈负相关关系,从逻辑上和历史现实中至少可以证伪其中一种极端情况,即气候政治负向消极参与(如拒绝批准京都机制、退出国际气候谈判机制等)而国际形象反而上升这一极端情况难以出现。相反,我们不妨尝试探讨二者负相关关系的另一种可能悖论——气候政治正向积极参与,而国际形象上升并不明显。
三、案例分析
以下将以大国的气候政治参与行为作为实例来对国际形象建构做进一步的考察,着重展示其中的运行机制,同时,结合上文理论分析和假设推理中抽象出来一些初步的认识,以有助于我们在气候变化政治这一后现代情境中更好地理解大国国际形象问题。我们将主要使用美国、俄罗斯和中国这三个案例,以尽量避免所谓“单一案例”可能遭遇的解释力不足,并且集中关注与行为、利益、形象有关的内容,从而尝试分析大国国际形象在气候政治中的建构。
(一)美国:“第二次机遇”?
美国对全球气候政治的参与可谓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被动到不得不逐渐转向主动参与的历程。早在20世纪70年代,环境问题及相关应对之策悄然兴起于美国国内,从美国的国际形象上来看,或许“美国人比其他国家的国民消耗了更多的资源,又排放了更多的污染和废弃物。同时由于美国是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强国,那么让其参与全球环境保护则是理所应当的”[19](p.9)。这种所谓对美国形象上的认知,促进了美国公共环境意识的觉醒,1970年4月22日首个国际“地球日”加强了环境主义的影响,迫使当时的尼克松政府成立了国家环境保护署(EPA),从行动上为此后美国参与国际气候政治创造了发展条件。
然而,美国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政治参与,从里根到老布什政府时期表现出来的行动却较为消极被动,一度成为全球气候问题合作的严重阻力。在里根政府时期,诸如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环境问题属“低级政治”议题范畴,为当时的美国所漠视,采取的行动较为消极,较多地依赖市场力量,通过私营部门涉足环境领域而减少联邦政府对于环境问题的管制,期间关于环境议题的对外援助少之又少,气候政策方面几无建树[20](p.15)。1992年10月15日,美国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且随后制定了能源政策法,然而有关温室气体减排的国家行动方案并未实际履行,及至2000年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增长了14.3%,远超其既定的维持1990年排放水平之标准[21]。显然,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气候政治参与呈负向消极参与。
克林顿政府时期,开始加强对外环境保护援助,拓展美国国家安全,将包含气候变化的环境问题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1993年4月,克林顿承诺把2000年温室气体排放减到1990年水平,以体现“美国对促进全球和平与繁荣负有领导责任”[22]。同年6月,成立“可持续发展问题总体委员会”,以讨论有关全球环境的对外资金、技术援助等,并向41国提供用于稳定人口的援助费用达4.6亿美元[23]。1996年,美国国家气候变化委员会对前一年发布的IPCC第二次研究报告表示认同。1997年2月13日,美国《经济学家关于气候变化的声明》发表,认为需要采取防范措施应对具有多方面危险性的全球气候变化[24]。值得一提的是,克林顿政府从1995年到2000年间前后共5次参加UNFCCC的缔约方大会,相比老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气候变化政治的参与更为活跃,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日内瓦部长宣言》从而为《京都议定书》的出台奠定了基础,推动了国际气候谈判的进一步开展。当然,在有关美国能源、制造业及其他相关工业部门对温室气体减排表现出较大的敏感性时,美国一般不愿给出明确的承诺或态度,从而为其战略利益谋划留有余地。
2001年,小布什政府一改之前美国政府对气候变化政治或犹豫或有所保留的态度,而在国际气候政治参与方面表现出了强硬的抵制态度,其环境政策甚至出现大倒退,最强烈的行为反应莫过于公然退出《京都议定书》,并且指责议定书是“根本错误的”。美国的“拖后腿”行径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从国际气候政治参与的层面来看,美国的国际气候政策陷入停滞状态,其国际形象急转直下,单边主义和一超独大的傲慢姿态备受指责。
2008年,奥巴马胜选总统,美国政府重新加强国际环境方面的双边、多边合作。如在双边合作上重视与中国的环境合作,典型的行为表现在和中国共同签署《关于中美两国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推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能源政策对话、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利用、中美和平利用核技术等双边机制的发展[25];在多边合作上,参与UNFCCC、G8峰会,并主导“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论坛”。同时,还利用亚太经合组织这样的平台来宣告自身的气候政策,利用北约组织强化能源安全目标,以期影响国际气候问题走向并掌握气候政治领域的话语权,尽可能地展示美国的软实力,运用巧实力,努力重塑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的领导者形象。
通过对美国的气候政策进行历史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发现美国的国际形象基本上与其气候政治参与呈正相关关系,从而也基本符合上文的假设一和假设二。即美国的气候政治参与行为,经由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里根和老布什政府时期的消极参与,到90年代中期克林顿政府若有声色、有所保留地响应,乃至新世纪初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强硬抵制和倒退,再到后金融危机时期奥巴马政府的“革新”,这之间美国的国际形象也有着十分微妙的正相关联系。单从“形象/身份→利益→行为”关系链的单向建构而言,不难解释一定历史时期的美国气候政策“行为”,但如果我们再思考这其中的反馈,可能进一步证实我们的假设和推论(不排除系统效应,比如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双重互动博弈,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都可能带有系统效应,也会影响到气候政治领域的大国行为和国际形象)。在这里,我们不妨联想布热津斯基的归因理论,所谓的“第二次机遇”,正是在对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大国际行为进行地缘政治的、历史的、深刻的反思后,从而重塑美国国际形象的战略考虑[26]。只是,不知其运筹帷幄间是否真的适得其主,与1997年同样出自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The Grand Chessboard)比起来,“第二次机遇”更像是给美国“救世主”又一次自我救赎③。比照其气候政治的参与历程,从老布什、克林顿,再到小布什政府,美国的国际行为反馈于形象,恰好耐人寻味地似可对号入座于“拙劣”、“无能”、“蹩脚/灾难性的领导”,到了奥巴马政府“重振旗鼓”,才似乎有了些许抓住“第二次机遇”的行动迹象,从而重塑美国的安全战略利益,重视气候变化议题,实现“世界领袖”形象再建构。
(二)俄罗斯:“游刃有余”?
2008年,俄罗斯作为全球第四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其排放量占全球的5.67%[27]。俄罗斯拥有足够广袤的森林覆盖国土,在影响气候变化方面蕴藏巨大潜力,就气候变化的脆弱性而言,俄排在遥远的第81位,相比近邻白俄罗斯(第28位)、哈萨克斯坦(第50位)、乌克兰(第52位),俄罗斯的情况似乎乐观得多[28]。对俄罗斯来说,与大部分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气候变化所能带来的,竟有不少明显的国家优势。比如说气温升高能使俄罗斯的冬天变得温暖从而可以减少冬季供暖时长而给国家节约大量能源;由于气候暖化,北冰洋地区的丰富能源开采前景将更加明朗起来,开发该地区资源的行动更为容易;海上国际航道交通的顺达也将使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影响加大,有利于其拓展国际形象。即便如此,至少有三大目标常用来解释俄罗斯的气候政治参与:其一,为改善俄罗斯的国际形象;其二,为入世谈判而加强与欧盟的联系;其三,京都议定书机制下的经济动机[29]。这里我们主要关注俄第一大目标即改善国际形象。当美国退出后,俄罗斯批准京都议定书的行为就显得尤为关键,甚至成了欧洲领导人议事日程所关注的重心,时任总统普京将对于京都机制的认可当作重塑俄罗斯国际形象的工具,以使俄罗斯成为挽救京都机制的“救世主”,表明俄与“欧洲政治”或“西方价值观”的一致[30]。
2011年12月的德班会议,俄政府强调其在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将不会承担任何数量上的义务,这与它在2010年坎昆会议中的陈述并无二致。俄罗斯强调国际气候制度须在“全面、综合”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即“包含所有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早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之前,俄总理普京就表示俄罗斯对气候变化谈判协议的参与和支持取决于其他主要工业国家须做出相应的承诺并能提出量化的减排目标,而且,还要将俄罗斯广阔森林具有巨大的碳吸收力这一因素考虑在内。
可见,俄罗斯对于气候变化政治的参与,是探求其特殊的国家利益进而重塑俄罗斯“超强”国家地位的工具性写照。俄罗斯参与国际气候政治似乎总是显得“游刃有余”,除了与其资源禀赋和历史遗产具有一定相关性之外,它对国际形象的追求与上文讨论的美国具有极其相似之处,即可以说都从国际地位及国际威望上看待和塑造所谓的国际形象,在这两个国家当中,国际形象的建构几乎可以混同于权力(尤其软权力的)优势、威望、相对地位等方面的谋划。
(三)中国:崛起大国的负责任参与
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政治的历程,与中国外交的整体步伐如影随形。正如我国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存在立场上的演变,经历了“被动却积极参与”(1990~1994)、谨慎保守参与(1995~2001)、活跃开放参与(2002年至今)三大发展阶段,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外交日趋成熟的发展进程[31]。
一般从全球公共问题的理论逻辑上来看,对气候变化的参与属于公共问题的范畴,难免遭遇“集体行动的难题”。那么,如上文美国和俄罗斯的案例所揭示的,一国对气候政治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选择性激励的影响,而不仅仅是道德伦理上的约束。国际形象一定程度上也属于选择性激励,显然它是一种国际社会意义上的激励。因而,从国际形象的护持而言,中国在气候政治方面总体上是正向参与的,但对于自身参与国际气候政治的积极行动而最终反馈于国际形象的再塑造进程,也不能盲目乐观。早期的气候政治参与中,中国尤其看重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护持,防止出现气候变化议题领域的“中国威胁论”[32]。2002年8月,中国批准《京都议定书》,联合国即表示这“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一个良好榜样”。然而,有不少发达国家非但不主动积极参与气候政治,反而还指责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大量排放温室气体、不承诺减排义务、威胁人类发展等。于是他们声称为了“把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要以中国等新兴大国实施大量减排为先决条件[33]。如此看来,在上文三种假设当中我们所担心的悖论出现了,气候政治与大国国际形象呈负相关关系,或至少气候政治正向积极参与,而国际形象的护持乃至上升难言乐观。
即使在气候变化这样的非传统安全议题上,大国参与行为面临的困难和可能的机遇一样不少,甚至当前的困境局面有时远多于利益和谐的乌托邦远景,我们也不能因此对正向积极参与国际气候政治以服务国家总体利益目标从而良性塑造大国国际形象的努力持过分悲观的态度。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负责任,意味着中国在国际关系与地区事务中承载着广泛的利益诉求,既有必要为国际社会提供一定的公共产品,又能够妥善应对国际政治中的复合安全挑战。负责任大国作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一种形象标识或身份认同,符合关系性思维。在这种思维逻辑里,“国际社会中的崛起大国是进程中的行为体或关系中的行为体,与他者以非冲突的方式互动;过程中的形象意味着源于动态关系的过程力量建构和重构行为体的身份”[34]。当然,这种负责任大国国际形象的建构,是国家崛起与国际合作以及参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不懈努力的写照,过程本身需要中国长期艰难的探索,其中难免遭遇不少挫折和困难。形象的护持效果或许有时并不明显,产出效应可能并不显著,但为了推动国家崛起的历史进程而继续积极正向参与国际气候政治,这一过程对中国和不少发展中国家而言,本身就存在路径依赖。从关系过程上来看,中国接受并深深内化了国际气候制度,但这一制度不能完全是西方模式的翻版,主体间性和互容性将日益替代西方话语霸权式的单向思维[35]。也许正是从这种动态发展和社会进化的意义上来看,我们对于包含气候政治在内的国际事务广泛参与,才可能是具有应然意义的。
四、结论
从形象的定义入手,我们探讨了国际形象的内涵,其包含了国际相对地位/身份、国际威望、国际声誉、国际荣誉等源于他者的认知范畴,其中身份认知尤为重要。由于存在主体间认知差异,国际形象的界定较为模糊和随意,过于关注或高估其中的相对地位也可能带来一定的危机。大国的国际形象反映了该国的战略动机,决定其利益关切,从而影响其行为。然而,形象→利益→行为的关系链条并非简单的线性联系,反馈存在于其中各个环节,产生系统效应,大国的国际形象因之仍有重塑的空间。
通过就美国、俄罗斯、中国这三个大国对全球气候政治参与的案例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气候政治参与行为与大国国际形象之间既存在正相关关系(正向积极参与则国际形象建构为良性护持或上升,负向消极参与则国际形象回落甚至受损),又存在可能的负相关关系(正向积极参与却面临国际形象建构的困境与悖论)。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为建构负责任大国身份或提升国际形象,总体上仍应正向积极参与国际气候政治进程,进一步为国家的崛起创造软条件。
可能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在于本文对国际形象的界定与探讨,主要关注其身份性与国家利益、国家行为之间的逻辑关联,以及大国行为对其国际形象的反馈效应。因此,这种分析框架仍然是初步的,由于诠释和论证的需要而抽象化的那些现象学思考,或许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案例选择与比较方面,本文对美国、俄罗斯、中国的气候政治参与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受制于分析框架的集中讨论,所作相关比较仍较为初步。尤其是涉及国际政治行为的反射评价,国际形象的上升或回落本身可能还受制于其他系统要素,比如大国的战略效果、国内政治回应等,这些都可能影响到该国国际形象的建构进程,对于新兴大国而言,甚至直接影响其崛起进路。事实上,如本文所提到的中国案例“悖论”所引发的思考,在全球气候政治治理中,亦属不难预知。换言之,新兴大国的气候政治参与,即使正向积极参与,其反馈也并不一定总能积聚到正能量(Positive Energy)(或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亦不难理解俄罗斯的气候政治现实主义)。长远观之,出于气候问题的未来政治关切,以及崛起中的大国战略考量,中国仍应继续正向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政治进程,相信“得道多助”,并努力参与国际气候建制,谋取必要的低碳生存和发展空间。同时,也为面对将来更趋复杂多变的国际气候政治博弈而积累必要的实践经验。
(本文的核心内容曾在2012年10月13~14日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五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上宣读。感谢清华大学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张严冰、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主任檀有志老师,以及察哈尔学会秘书长柯银斌老师的点评。)
注释:
①相关定义可参阅[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美]托马斯·谢林:《军备及其影响》(毛瑞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Charles Kegley and Eugene Wittkopf,American Foreign Policy:Pattern and Progress,New York:St.Matin’s Press,1996;Jonathan Mercer,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②以下假设都基于图1曲线所示的逻辑,即大国的气候政治参与行为可以重塑其利益,进而由利益的重塑影响其国际形象的建构。
③《第二次机遇》付梓之际,奥巴马政府还未上台,但实践表明,布热津斯基的战略思想对美国领导者影响深远,尤其对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制定起到推波助澜之功效。参见布氏2012新著《战略憧憬:美国与全球力量的危机》(Zbigniew Brzezinski,Strategic Vision: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New York:Basic Books,2012)。
参考文献:
[1]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2]Philip Kotler.Marketing Management,Analysis,Planning,Implementation and Control[M].UpperSaddle River,NJ: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Inc.,1997.
[3]管文虎.国家的国际形象浅析[J].当代世界,2006,(6).
[4]郭树勇.论大国成长中的国际形象[J].国际论坛,2005,(6).
[5]门洪华.压力、认识与国际形象——关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战略的历史解释[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4).
[6]尹占文,邓淑华.战略文化、国家行为与国际形象——对中国国际形象变迁的考察[J].社会科学研究,2009,(4).
[7]Charles.W.Freeman.Arts of Power:Statecraft and Diplomacy [M].Washington,D.C.:U.S.Institute of Peace Press,1997.
[8]Kenneth Boulding.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J].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959,(3).
[9]Amitai Etzioni.International Prestige,Competition and Peaceful Coexistence[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62,(3).
[10]Peter Lassman,Ronald Speirs.Weber:Political Writing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11]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M].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12]Richard Ned Lebow.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13]摩根索.国家间政治[M].徐昕,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4]Anthony Lang.Pol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M].Connecticut: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2004.
[15]Hans Morgenthau.Scientific Man Vs.Power Politic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6.
[16]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17]J.K.Fairbank,S.Y.Teng.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J].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41,(6).
[18]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J].World Politics,1978,(2).
[19]Gary Bryner.From Promises to Performance:Achieving Global Environment Goals[M].New York:W.W.Norton,1997.
[20]Norman Vig.Michael Kraft.Environment Policy in the 1990s[M].Washington 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1994.
[21]U.S.EPA.Inventory of U.S.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Sinks:1990-2004[EB/OL].http://www.epa.gov/climatechange/Downloads/ghgemissions/06-Complete-Report.pdf,2012-09-28.
[22]Clinton Lays out Environmental Program[EB/OL].http://www.loe.org/shows/shows.htm?programID=93-P13-00017,2012-09-28.
[23]楼庆红.美国环境外交的三个发展阶段[J].社会科学,1997,(10).
[24]Economist’s Statement on Climate Change[EB/OL].http://dieoff.org/page105.htm,2012-09-28.
[25]U.S.-China Energy Cooperation[EB/OL].http://www.pi.energy.gov/usa_china_energy_cooperation.htm,2012-09-28.
[26]Zbigniew Brzezinski.Second Chance[M].New York:Basic Books,2007.
[27]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Carbon dioxide emissions(CO2),Thousand Metric Tones of CO2,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Indicators[EB/OL].www.mdgs.un.org,2012-09-29.
[28]Global Adaptation Institute.Global Adaptation Index[EB/OL].www.index.gain.org,2012-09-28.
[29]Andrzej Turkowski.Russia’s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cy [J].Polski Insiytut Spraw Miedzynarodowych (PISM),Policy Paper,2012,(27).
[30]Laura Henry,Lisa Mclntosh Sundstorm.Russia and the Kyoto Protocol:Seeking an Alignment of Interests and Image [J].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2007,(4).
[31]严双伍,肖兰兰.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演变[J].当代亚太,2010,(1).
[32]Hyung-Kwon Jeon,Seong-Suk.From International Linkages to Internal Divisions in China [J].Asian Survey,2006,(6).
[33]杨洁勉.世界气候外交和中国的应对[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9.
[34]Qin Yaqing.Relationality and Processual Construction[J].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09,(4).
[35]秦亚青.作为关系过程的国际社会——制度、身份与中国和平崛起[J].国际政治科学,2010,(4).
[责任编辑:刘琼莲]